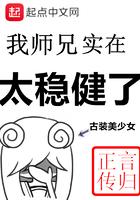奇书网>阳明学派是凭啥建立的 > 三结语(第1页)
三结语(第1页)
三、结语
本章主要透过考查晚明江右深具代表和影响力的理学家——王时槐、刘元卿——的言论与行为,讨论晚明江右学者的地域认同,以及他们诠释、建构传统的做法;晚明江右阳明讲学的特殊风格。以上两部分的讨论均着重强调在“晚明”这个特殊时间分期中,江南与江右文化风俗,以及理学内部江右与江左学派之间激**对话的过程。亦即,从文化竞争与自我认同的角度,探讨晚明江右阳明学在当时整体学界中的位置与发言。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说明当晚明江南因经济和政治实力,成为全国文化流行的中心时,江右士人感受到不断被边缘化的危机,却又似乎完全使不上力以逆转这种下滑的趋势。然而在这种危机感的驱动下,他们必须重新为自己寻找定位、凝聚认同。王时槐、刘元卿等著名的江右讲学者,一方面投入地方志的编纂工作,透过对吉安文化传统的诠释,他们发现了,质醇的民风、忠臣气节、阳明理学是吉安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也是他们最足以抗拒江左颓靡文化入侵的资产。另一方面,他们更是竭力地投入倡导地方讲会活动,以行动和学术思想,来传承并开创属于江右淳正的学术风貌。他们重复诉说着前辈们齐聚青原的盛况、仿效着过去月复一月或季复一季的讲会活动,透过言语、文字和行动来诠释传统,也因此发扬传统。就某个意义而言,16世纪40—50年代江右邹守益、聂豹、罗洪先等学者讲学的事件,实在是通过晚明学者们的记忆召唤与书写,才更清晰地显出其重要的历史面貌。
第二部分则从三点来说明晚明江右讲学的重要风格:长期静修以明性的工夫进程、重视礼法与肯认名实关系、静肃的讲会氛围。这三点分别呼应着他们对晚明江左学风的批判:即所谓“崇妙悟而略躬行、崇虚寂而蔑礼法、多虚谈而鲜实行。”江右学者在工夫实践方面,是以一种长期向内静修的方式为基调,这既是对王畿和泰州学者“自自然然”“无工夫之工夫”论的一种纠正,也是他们确实实践后所领悟的心得。虽然这种静修的倾向不免招致近禅的讥评,不过因为江右学者对礼法规范、品格操守的坚持,不仅普遍获得士大夫的赞赏,也使他们能免于受到过激的批评。而呼应着对王畿和泰州之教导致“败坏礼法纲纪”的批判,江右学者则十分强调礼法规范的重要性,并且重申名实之间的关联,认为名节是道的樊篱,不容任何人以“不好名”“断名根”为口实而混乱道德表述。最后,我们则从晚明江右的一些讲会会规中,看到一种格外强调静肃自修、压抑言说、减少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特色,这种强调也改变了早期阳明讲会所标榜的“互相规过”的直谅作风。此种静肃的风格,呼应着他们对当时江左学风“多虚谈而少实行”的批判,但却非只在表面行径上欲求区分或改革的做法而已,更与学者们之工夫实践与思想内涵紧密相关,是在当时学风刺激下,反思与实践的心得。
[1]JohnDardess,AMiy,Ch。8。
[2]刘元卿,《诸儒学案》,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周汝登,《圣学宗传》,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孙奇逢,《理学宗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3]例如,邹元标:“常窃疑海以内播迁几三百人,岂无申只手辟巨眼,为吾道一吐气者。”即可见学道人数并不多,载邹元标,《答胡趋儆侍御》,见《邹子愿学集》,卷2,63b~64a页。这种现象和感想也会因地而异,例如,苏松地区,文人文化显然胜于理学文化,普遍而言,阳明学并不兴盛,江右地区则理学较兴盛。参见宮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眾——明代史の素描试み——》;JohnMeskill,GeerestsaheYaa,AnnArbor:AssoforAsianstudies,1994,pp。33~70。
[4]我未能找到其名。
[5]杨东明,《山居功课》,卷6,72b~73b页。
[6]对于士人地域认同的问题已有许多重要的讨论,特别是RobertHartwell和RobertHymes指出从北宋到南宋之际,士人阶层的社会参与有一重要的转向,即从全国性事务转向在地方社会中经营,其对地方的建设与认同亦转强。本文所讨论的明末江右士人的地方参与,虽然看似这个趋势的延续,但毕竟时间已到16世纪末的晚明,从南宋到晚明到底经过怎样曲折的变化?这种对地方社会的经营与认同是否在明初中央集权体制下曾被打断,晚明再起?对于这些问题,作者未能深研,无法回答。PeterBol对金华地区的研究,同样指出晚明金华士人有颇强的地域认同,且不是从南宋延续发展到晚明,明初朝廷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较强,地域性的士人活动与意识亦相对受到压抑。RobertHartwell,“Demographic,PolitidSosformationofa,750—1550,”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42。2(1982),pp。365~442;RobertHymes,StatesmeheEliteofFu-g-Hsi,inNorthernandS(Cambridge:CambridgeUyPress,1986)。包弼德(PeterBol),《地方传统的重建——以明代的金华府为例(1480—1758)》,收入李伯重、周生春编,《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960—1850)》,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247~286页。
[7]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三、第四、第五章。
[8]RidlerandJoekin,“Tradition,GenuineorSpurious,”JournalofAmeriFolklore97。385(1984),pp。273~290。
[9]EvelynS。Rawski,“EidSodationsofLateImperialCulture,”inDavidJohhan,EvelynS。Rawskieds。,PopularLateImperiala,Berkeley:UyofiaPress,1985,pp。3~33;陈学文,《明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发展》,见《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台北:稻禾出版社,1991年,87~97页;JohnMeskill,GeerestsaheYaa,pp。1~32。关于明代白银输入中国的估计量,见RiGlahn,FountainofFortune,Berkeley:Uyofia,1996,Ch。4;关于晚明江南消费文化、物质文化和流行等,见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见《中研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137~159页;林丽月,《晚明“崇奢”思想隅论》,《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1991年),215~234页;《衣裳与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见《新史学》,10卷3期(1999年),111~157页;as,SuperfluousThings;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见《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37~83页;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见《新史学》,10卷3期(1999年),55~109页;毛文芳,《晚明闲赏美学》,台北:学生书局,2000年等。
[10]BenjaminA。Elman,ACulturalHistoryofCivilExaminationsinLateImperiala,pp。256~260。
[11]BenjaminA。Elman,ACulturalHistoryofCivilExaminationsinLateImperiala,pp。256~260。缪进鸿和沈登苗的研究也显示,从宋、元、明到清代,江西的学术文化地位明显滑落的情形。缪进鸿,《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见《教育研究》(1991年),10~26页;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见《中国文化研究》,26期(1999年),59~66页。
[12]Ping-tiHo,TheLadderofSuImperiala,p。227。
[13]BenjaminA。Elman,ACulturalHistoryofCivilExaminationsinLateImperiala,pp。256~260。
[14]王时槐,《文昌塔记》,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3,27b~30b页。
[15]罗玘,《送苏君江西提学序》,见《圭峰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卷5,26a~27b页。亦见JohnDardess,AMiy,pp。168~169。
[16]王时槐,《文昌塔记》,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3,27b~30b页。
[17]王时槐,《文昌塔记》,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3,27b~30b页。
[18]BenjaminA。Elman,ACulturalHistoryofCivilExaminationsinLateImperiala,pp。258~259。
[19]关于西原惜阴会,见下文。
[20]王时槐,《西原会规十七条》,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6,19a~19b页。
[21]王时槐,《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4,18b~19a页。
[22]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眾——明代史の素描试み——》。
[23]JohnMeskill,GeerestsaheYaa,pp。33~70;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
[24]除了俭朴仍为一般人所肯定的美德外,此也关乎士大夫面对士商身份混淆以及许多僭越风俗流行时,为维护社会秩序及保护自己地位的考虑,参见林丽月,《晚明“崇奢”思想隅论》,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
[25]包弼德(PeterBol),《地方传统的重建——以明代的金华府为例(1480—1758)》。
[26]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73~92页。
[27]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36年,10~11页。
[28]李文耀,《重修束鹿县志序》,见《乾隆束鹿县志》,李文耀、张钟秀纂,民国二十六年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卷1,2a页(341页)。
[29]薛虹,《中国方志学概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115、118页。
[30]见《吉安府志》,明万历间刻本,页首。
[31]刘元卿,《福乘藏稿序》,见《刘聘君全集》,卷4,7a~8a页。
[32]《吉安府志》,明万历间刻本,卷11,1a~1b页(170页)。
[33]《吉安府志》,明万历间刻本,卷18,1a页(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