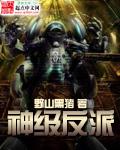奇书网>阳明学派是凭啥建立的 > 二晚明江右阳明讲学的特殊风格(第1页)
二晚明江右阳明讲学的特殊风格(第1页)
二、晚明江右阳明讲学的特殊风格
既然江右与江左两地的文化存在着不同的面貌,到底江右阳明讲学的特殊风格为何?学者们所强调的讲学重点,与当时江左讲学风尚间存在怎样的关系?本节主要想讨论这些问题。正如上节所述,讨论晚明江右士人的地域认同以及他们对传统的诠释时,必须考虑当时江左文化的冲击,同样的,要谈晚明江右阳明学风,也必须将之置放在与越中学派和泰州学派相对立和对话的角度下思考。
从聂豹、罗洪先开始,江右理学家就不断地对阳明学派内部不同的良知诠释与讲学风格进行反省,聂豹和罗洪先主要针对的是浙中阳明学领袖王畿的学说,到了晚明,批判的矛头更指向一股所谓“崇妙悟而略躬行、崇虚寂而蔑礼法、多虚谈而鲜实行”的学术风尚,主要的对象就是深受禅学影响的浙中讲学,以及加入李贽因素后的泰州讲学。当然针对王畿和泰州等讲学的批判,并不仅限于江右学者,许多江南士人也发出严重批判,例如,浙中的黄绾、张元忭、王叔果(1516—1588)都有严正批评,[41]显示江左学风本身的多元歧义性,但下文我们只着墨于江右讲学者的批判。
(一)江右学者的批判
让我们先来看,16世纪40-50年代江右学者批判的历史脉络,当时最重要的辩论是环绕着王畿“现成良知”论展开的。王畿的“现成良知”强调良知的圆满具足、不假修为,因此也是一切工夫的根源所在,从人能(应)把握此完美良知的角度看,其他任何的工夫和修为均是次要的。王畿这种看法并非不重视工夫,只是反对执着任何特定程序的工夫模式,强调随时随地、动静一如的工夫观。这种看法引发许多争议,其中以江右的聂豹和罗洪先的批判最具代表性。
聂豹以为王畿学说的主要错误在于“以知觉为良知”,将情识冒认作良知,所主张的“以不学不虑为工夫”也将造成重大流弊。他指出:“浅陋者恣情玩意,拘迫者病己而稿苗,入高虚者遗弃简旷,以耘为无益而舍之。是三人者,猖狂荒谬,其受病不同,而失之于外一也。”[42]亦即认为所造成的弊端,虽因个人资质个性有所不同,但归根的病源则是,误认已发的知觉为良知本体,而忽略真正涵养内在的良知本体,所谓“失之于外”。为了矫王畿“现成良知”之流弊,也因为得自他长期自修工夫的验证和把握,聂豹大约在1548年,提出他的归寂说,[43]他的主要观点是:“良知本寂,感于物而后有知,知其发也,不可遂以知发为良知而忘其发之所自也。”意指良知是不睹不闻、廓然大公的寂体,是未发之中,而不是感物后所产生的知觉。基于此,他认为学问之道在于主乎内之寂然者,就是归复于本寂的良知本体,唯有此才能达到感无不通、外无不该、动无不制、天下之能事毕的境界,绝不是任随良知的发用而行。[44]
聂豹明显区分未发与已发,并不契于王阳明所主张动静一如、未发已发不二分的看法,因此其说一出,其他江右阳明学者们如邹守益、欧阳德、黄弘纲、陈九川等人都出面反驳,[45]不过此说却深获罗洪先的共鸣。罗洪先同样是对于王畿学说进行深刻的反省之后,且几度迂回才终于提出他的批判。罗洪先早年相当佩服王畿之学,但后来两人在学问上渐行渐远,罗洪先不满意王畿的讲学风格,也不满意他现成良知的学说,他认为王畿学说的弊病在于:承领本体太易、欠缺静定工夫。亦即认为王畿太过相信心体的发用,源于相信“以良知致良知”而主张“无工夫可用”的工夫论,更是引发学术流弊的关键。罗洪先认为这种工夫根本与儒者“兢兢业业”“必有事焉”的教导不契,不但无法指引学者正确的为学取径,更会使人奔放驰逐、茫**一生、毫无所成,势必造成**肆的学风。[46]
虽然聂豹和罗洪先归寂主静的倾向起初在江右有些孤单,不过,刘文敏晚年似乎同意了聂豹的看法。[47]牟宗三也认为江右之学从刘文敏的“以虚为宗”、刘邦采的“悟性修命”,到王时槐的“以透性为宗、研几为要”,是一连串走向以道体性命来范域良知的趋势,就是越来越接近聂豹、罗洪先等人,从阳明学歧出的取径,也因此越来越不能与“现成良知”所主张“良知本有、可随时呈露”的宗旨相契,因此他认为基本上江右王学是一段逐渐违离王阳明学说精神的学术史。[48]在此我们不必像牟宗三一样进入何为阳明学说正宗传承的价值判断,而是要指明:从聂豹、罗洪先以降的江右讲学者,批判、排拒王畿所影响的浙中学风,及与王畿学说风貌相近的泰州学派的态度,确实有越来越明显和扩大的趋向,而相应于这种批判和抗拒的趋势,则是聂豹和罗洪先主静归寂的主张,在江右获得更多的认同。邹元标便指出,王时槐十分尊崇罗洪先静定之学,言必曰“文恭、文恭”,江右阳明学遂得传衍。[49]浙中和泰州两学派,似乎总能让江右学者产生某种警惕自励的作用,当然也关键性地影响着晚明江右学者对端正学风的看法和表现。下面让我们来到晚明的脉络,继续看江右学者对当时江左学风的批评。
晚明浙中理学的一大特色是深染禅风,不仅王畿之学难免于近禅之讥,他在浙东的传承,更是越来越受禅学的影响,黄宗羲对此描述道:“当是时,浙河东之学,新建一传而为王龙溪畿,再传而为周海门汝登、陶文简,则湛然澄之禅入之。三传而为陶石梁奭龄,辅之以姚江之沈国谟、管宗圣、史孝咸,而密云悟之禅又入之。会稽诸生王朝式者,又以捭阖之术,鼓动以行其教。证人之会,石梁与先生分席而讲,而又为会于白马山,杂以因果、僻经、妄说,而新建之传扫地矣。”[50]根据黄宗羲,浙中阳明学从王畿、周汝登和陶望龄,传到陶奭龄等人,已深受禅学影响,因此刘宗周欲与此学风划分界限、并矫正之。[51]尽管晚明文人和三教学者中,多有三教交涉融合的倾向,学术界也确实有较多元而宽容的态度,但当时欲端正儒学、排拒异端的儒者大有人在。而且在辟异端的立场下发言,声音更响亮而严正。当然批判者并不只限于江右学者,著名的东林学者和许多浙中、江南的学者也发出严厉的批评,只是江右因地域的差距及学术特色,其批判更容易与地域传统相连接,也更容易以江右学术之名目而发。
至于对晚明泰州学派的批判,我们知道泰州学派在学说精神风貌上与王畿颇多相契之处。一般而言,江右学者对于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能够以布衣之身致力于孔门圣学,对其为学的决心与热诚,都相当称许;对于泰州学派另一位重要学者罗汝芳的高卓胸襟与风范,及其学问的圆融透彻,也都赞誉有加。不过,他们对于泰州的学风和教法,就如同对王畿的教法一样,则多持保留意见。例如,王时槐说:“近溪自是高贤,但立教贵有准绳,不可不慎,如近溪之说亦在善,学者慎之,乃无流弊耳。”[52]王时槐在《西原会规》中说道:
近世学者渐袭虚见、隳实行,有足虑者。又海内高明之士有以乐为教者,一切破除礼法,于言动威仪全不检束,以此为天真自然。其流之弊,遂使后辈庸劣者,纵欲败度;憸狠者,干纪犯宪。如是者盖不少矣。赖吾郡诸先觉力排其说,故昔年郡中有为此狂谈者,能鼓动异省,而吾郡士人竟未受惑,此先觉之功,而吾侪所当恪守也。[53]
此处“以乐为教者”指泰州的王艮,王艮的《乐学歌》对于心体本乐、学是乐的道理有特别的阐发,其学也强调“天真自然”。[54]因此此段文字是针对泰州教法而发的批判,批判的重点仍在,其可能导致狂放、纵欲的危险性。
另外,当我们讨论晚明一般对泰州讲学的批判时,也必须考虑李贽因素所造成的发酵作用。李贽坎坷的一生、深刻矛盾的宗教情怀、激烈的批判风格、骇人听闻的议论、加上他学说中隐含对一般是非价值判断及人伦规范的质疑,使他成为当时学术界著名的异端分子。[55]他和耿定向的论辩争执,主要关键点乃在人伦礼法规范与信任自我心性间的紧张关系,[56]基本上延续了王畿与其批判者之间的张力,或甚至可以说反映了阳明学与程朱学对话的精神,此本不是可以轻易判断是非对错的。然而,整个事件在当时显然加深了李贽异端狂妄的形象,当时针对李贽的批判完全集中在其“反礼教”和“放纵欲望”的形象上做文章。而李贽对王畿和罗汝芳的倾慕,以及他对“现成良知”论的发挥,也使得在观察晚明学界一片反对“无善无恶”的声浪时,都必须考虑李贽的因素。沟口雄三就指出顾宪成和冯从吾的反无善无恶说,基本上都是针对掺杂了“李卓吾要素”的无善无恶之说,亦即针对李贽肯定情欲的言论而发。[57]
至于泰州学风对江右的影响问题,我们知道,泰州学者中多有江西人,例如,何心隐是永丰人,早期虽在本乡倡族人建聚和堂、创义田、储公廪,但1561年之后何心隐逃离永丰,历游大江南北,并没有再回到吉安,其学说对吉安一地影响有限。罗汝芳是建昌府南城县人,其讲学也确实深入江西,[58]但在16世纪80年代以前,其学对吉安府的影响并不算大。根据我对吉安府阳明讲会活动的考察,确实得到和王时槐此处所言相当一致的看法:吉安府在晚明前期,尚能够相当程度地抗拒泰州学风的影响。不过从王时槐之言,我们可清楚看出,他已备感江左风尚逐渐入侵的威胁,他说江左华靡、轻巧、放达之风,已足以使吉安高贤怅惜惶恐,故他呼吁江右士人要共同起来,继承江右士人传统,才能有效遏阻江左学风入侵。[59]
尽管江右学者严厉地批判、刻意地打压江左学风,但强势文化的侵入和影响,毕竟有不可拦阻的穿透力量。当17世纪初期,尤其是王时槐去世(1605)之后,李贽、泰州学派和佛学在江右流行的情形更加明显,刘元卿就直斥李贽是败坏江右风俗的大罪人:“敝郡庐陵泰和之间,倏化为夷俗,至有明斥孔子为钝根,谓五伦皆假合,推此风不至趋于乱不止,此其端皆起于卓吾诸人,而其流弊遂至于此。”[60]然而从这段话,以及他所说:“迩日禅锋炽燃横被,江右谈者辄以了不可得为妙义”;“吉州学者寥寥,自王塘翁物故,如群蜂失主,莫知所归,高谈者,穷无何之乡,冥栖者,入黑漆之筒,使中庸一路遂成榛荆。”[61]我们则可知,17世纪初江左风气对江右的强大感染力,也可以感受到在王时槐去世后,刘元卿所承受的压力。面对江左文化的强大威力,他也只能再次召唤江右传统以资对抗。
(二)江右讲学风格
本节将从三方面来讨论在抗拒江左学风的特殊历史情境下,晚明江右阳明讲学到底呈现如何特殊的风格:一、针对重悟轻修、过度相信自己感官情绪的弊端,江右讲学者致力于长期静修明性的工夫;二、针对重内轻外、**越礼法、混淆名实的弊端,江右讲学者强调礼法等社会规范的重要,并再度肯认名与实间的关联;三、针对虚谭不实的弊端,江右讲会特别营造一股静肃潜修的氛围。
(1)长期静修以明性的工夫进程
前文已谈到,江右学者的批评主要是针对王畿“现成良知”理论所造成的影响而发。“现成良知”论因为对于良知本体有全然的信任,一切以良知自然呈露为依归,强调顺着本心良知去体悟、去做工夫,即罗洪先所批评“无工夫可用”的工夫。泰州学派与此有相当契合之处,同样强调圣人之学应顺应良知之自然呈露,是自自然然、不费纤毫之力的,也同样反对一切以人为费力之固定工夫程序的追求。这种工夫论倾向经常被视为是“崇妙悟而略躬行”,为开启懈怠荒**不拘学风的关键,因此饱受批评。
相应于这种批判的态度,聂豹和罗洪先都同时采取以静修的工夫回归性体的为学取径,来从事圣学,他们也确实都经由这样的工夫进程,体悟真道并确立己学。聂豹在狱中长期静坐而见光明心体,成为奠定他归寂学说的关键;[62]罗洪先1546年辟石莲洞后,多洞居静修,“默坐半榻间,不出户者三年”,1555年更废书块坐三月,恍然大觉,从此才真正确立其“收摄保聚”之学。[63]这种透过长期静修以回归性体的工夫取径,也逐渐成为江右理学的基调。从许多理学家的传记,我们可以见到这种普遍的趋势。例如,刘文敏以八十岁之高龄,仍陟三峰之巅,静坐百余日;[64]王时槐五十岁罢官后,“屏绝外务,反躬密体,如是三年,有见于空寂之体。又十年,渐悟生生真机,无有停息,不从念虑起灭。”[65]就连并不全然契合罗洪先主静教法的胡直,其奠定自学的重要基础,仍在长期的静修工夫。[66]根据方志所记,赵弼、杨以伦、刘霖、聂有善等学者亦然,可见这种静修工夫的普遍。[67]另外,我们从学者们交换书信中讨论“静时或有一团黑境,或胡涂无分晓,或全无着落”的景况,[68]也可窥见江右士人对这种修养工夫的进深程度。
这种长期静修的工夫路径,固然可以追溯到宋儒的影响,学者们已指出罗洪先师事李中,而李中之学可上溯宋儒,且其学明显受到周敦颐主静无欲,与李侗“观喜怒哀乐未发气象”的影响;而聂豹的学说也受到周敦颐、陈献章学术的影响。[69]尽管历史文化资源与影响因素确实存在,但我们在考虑宋儒学术对明学者的影响时,也应该考虑晚明当时的特殊因素,尤其我们知道,聂豹和罗洪先两人,都十分欣赏王阳明的学术,也长期在阳明学派中交游学习,他们并不容易轻易跳过当时阳明学的学术氛围,而上接宋儒传统的,他们亦非完全不能体会王畿等人求学和传道的理念,或只是轻易地为反对王畿而提出另一套学问。相反的,他们是在相当迂回的对话和反省过程中,且奠立在自己亲身实践的心得上,才逐渐确立这种静修的工夫路径。因此,我们与其视他们为前代学术遗产的被动接受者,毋宁视他们为在可能的历史资源和情境下的主动行动者、实践者。当时王畿学说所带出的影响,与他们自己的反思与理想,恐怕是引导他们学说和工夫取径更重要的因素。
其实江右学者明显向内静修的工夫路径,也很容易被诋毁为喜静恶动、枯坐顽空、近于禅定。从王时槐说:“今人不知学,但见向里寻求,稍稍习静者,便诋以为禅。”便可见这种批评的普遍。[75]我们知道从宋代的周敦颐、陆九渊、杨简,到明代的陈献章、王阳明均曾被诋为禅,人们对于聂豹和罗洪先亦不免有虚寂之疑。尽管如此,且同样在辟佛的前提下,江右学者仍然肯定静修的工夫之于涵养心体的重要性,尤其强调其对于初学者的重要。以王时槐为例,他一面反驳批评者本身不知学,一面提倡重视闭关静修的“研几”之学。[76]他虽不坚持静坐是唯一的工夫,却极力强调“静”的重要:“夫学当无间于动静,然始焉立基,终焉入微,必由静得。虽有志为学,不久静,恐以意气承当,以影响为究竟,于真体亲切处未能彻底,故贵静也。”[77]他相信在静坐中默识自心真面目,方可“邪障彻而灵光露”,达到在应事接物的人情事变中克尽伦分、动静皆宜的境界。[78]
综言之,江右阳明学从聂豹、罗洪先以降,到晚明众学者,在实践工夫上有明显强调长期静修回归性体的趋势,此种工夫取径也标识着江右重修的学风。此既关乎学者性格气质与自身体悟的心得,但也有着长期与江左学风对话的因素,并非仅被动地接受某些宋学遗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