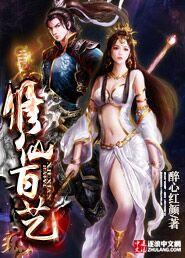奇书网>重生三国之貂蝉

重生三国之貂蝉
华筵惊梦,井口的冷还在。她拒绝再做谁的“完美补充”,转身做局:一纸“依例如此”,一声“铃”,一面“墙”,一盏“白灯”,把快变稳,把刀纳入秩序。她让“事实比脾气大”;她,借戟问心,与飞将隔墙对弈,让猛虎学会细嗅;董府家宴,她把暧昧改成流程,把随口允诺钉成公事。她的金手指不是天命,而是可验证的规则——。这是一部女强权谋/商战写实风的古设新写:没有花里胡哨的甜话,只有阳谋、证据、口碑与复利;也有互相成就的双强:他握刀,她持秤,彼此克制,彼此校准。若你也厌倦“情绪劳动”和“你懂事”的捧杀,来这本书:看她如何把风声钉在墙上,把黑锅写回原主,把名字从沉默里取回。 重生三国:貂蝉,一舞倾天下
《重生三国之貂蝉》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30章 财源滚滚杀机暗藏
,案上新添三样东西:一册《银流三问》草案、一张军需比价会的流程图、三封来自坊市同业公所的“捐助意向”。阿绣把帘子挑起半寸,让光进来,不让噪进来。两名女官把昨夜加班抄清的“回执汇总”摊开,三类问政——礼、兵、财——像三条并列的河,各自有源各自有岸。 “今天不打仗,理账。”我用簪脚在案上一点,“三件事:一,军需公开比价;二,民助账设‘冷却期’;三,银流上墙。记住一句话——钱也要有回执。” 这座城在问礼日之后,竟真的“活”了一截。百花楼的针码绣接单不断,回音斋的回执板天天换新,草木堂的粥香把一条街熏得安稳。商人嗅到秩序的味道——秩序意味着交易可预期,预期一稳,钱就肯出来走路。三封“捐助意向”便是钱走来的第一串脚印:米行的“义粟”、布行的“寒具”、票号的“抚恤银”。落款都...
《重生三国之貂蝉》最新章节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30章 财源滚滚杀机暗藏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29章 三日既满开箱问政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28章 反客为主饵钓鹰犬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27章 筑巢引凤鹰犬环伺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26章 金针暗绣百花之楼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25章 密室复盘草蛇灰线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24章 论功行赏匕现图穷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23章 受禅台前神鬼泣血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22章 禅台筑罢风雷欲起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21章 收网之时共谋朝堂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20章司徒说吕大义成囚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19章凤仪亭下戟挑龙鳞
《重生三国之貂蝉》章节列表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1章华筵惊梦凤目初开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2章死局三策一念择主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3章凤仪亭前一曲问心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4章丝帕之谜无声之饵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5章飞将试探隔墙对弈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6章猛虎细嗅棋盘暗流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7章借戟问心池畔双弈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8章余波未平暗流再起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9章董府家宴画戟为媒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10章静室密谈刀鞘之约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11章小试牛刀立竿见影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12章连环之计反客为主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13章锦囊倒授借壳生花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14章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15章祸起萧墙假凤虚凰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16章司徒献宝初见龙颜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17章一女二许无形之链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18章献蝉入宫风雷将作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19章凤仪亭下戟挑龙鳞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20章司徒说吕大义成囚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21章 收网之时共谋朝堂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22章 禅台筑罢风雷欲起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23章 受禅台前神鬼泣血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24章 论功行赏匕现图穷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25章 密室复盘草蛇灰线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26章 金针暗绣百花之楼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27章 筑巢引凤鹰犬环伺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28章 反客为主饵钓鹰犬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29章 三日既满开箱问政
- 第一卷金丝雀之笼第30章 财源滚滚杀机暗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