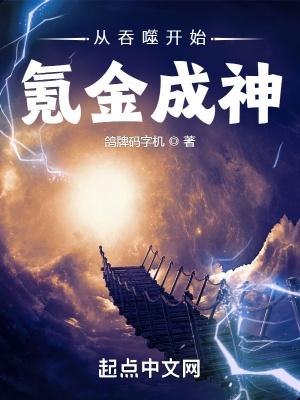奇书网>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 詩卷第十七02(第3页)
詩卷第十七02(第3页)
【纂疏】李氏曰:「愛民者,天之常道耳。今天使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言『為猶不遠』,又言『猶之未遠』,蓋反覆言之。自下文以至末章皆是大諫也。」嚴氏曰:「朱氏以此詩為切責僚友用事之人,而義歸於刺王,與上篇同味。詩意信然。」又曰:「一章至五章,皆切責僚友之辭。厲王邪辟,凡伯不欲斥王,而歸之於天。」疊山謝氏引先生《初解》曰:「人苟知聖人之法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此心若無聖人矣,則管管然無所依據,矯誣詐偽何所不至,其出言行事不以真實,而歸於誠道無怪也。」○愚謂厲王無道,召穆、凡伯以親賢之故,宜極言而力救之,以盡其意。顧乃不直致其諫,而姑責同僚以使之聞之者,豈非亦以其監謗之故,不欲嬰其鋒以陷於罪,而甚吾君之惡也耶?吁!二公忠愛之懷,於此益可見矣。
天之方難叶泥涓反,無然憲憲叶虚言反。天之方蹶俱衛反,無然泄泄以世反。辭之輯音集,叶徂合反矣,民之洽矣。辭之懌叶弋灼反矣,民之莫矣。
賦也。憲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蓋弛緩之意。《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輯,和。洽,合。懌,悦。莫,定也。辭輯而懌,則言必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也。
【纂疏】疊山謝氏曰:「孔子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子產有辭,四國賴之。鄭,小國也,介於齊、楚、秦、晉四強國之間,能保其社稷者,惟有辭命足以動人耳。俾諶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鄭之辭命豈有不善者乎?厲王之無道極矣,出其言,善民未有不應之者,信乎辭之不可以已也。」嚴氏曰:「此詩首章責同僚出話不然,為猶不遠。故二章因戒之,以言論之間,宜相和協,庶可措民于安然。愚而自用者,終不能舍己從人。故三章言『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四章言『匪我言耄,爾用憂謔』,乃大言虚誕,諛言阿附,善人見其如此,不肯復言矣。故五章言『無為夸毗,善人載尸』也。五章皆說僚友議論不相協,猶《小旻》詩六章,其前五章皆說謀猶之不臧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許驕反。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叶思邀反。先民有言,詢于芻初俱反蕘如謡反。
賦也。異事,不同職也。同僚,同為王臣也。《春秋傳》曰:「同官為僚。」即,就也。囂囂,自得不肯受言之貌。服,事也。猶曰我所言者,乃今之急事也。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古人尚詢及芻蕘,況其僚友乎?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虚虐反。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其畧反。匪我言耄莫報反,叶毛博反,爾用憂謔。多將熇熇叶許各反,不可救藥。
賦也。謔,戯侮也。老夫,詩人自稱。灌灌,款款也。蹻蹻,驕貌。耄,老而昏也。熇熇,熾盛也。○蘇氏曰:「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汝以憂為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為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纂疏】濮氏曰:「天方降禍,不可如此戲謔。」鄭氏曰:「老夫,凡伯自謂。」嚴氏曰:「小子,承上章同僚之文,指用事之人。」李氏曰:「蹻蹻,舉足高蹻意。」疊山謝氏曰:「不可救藥,如所謂死病無良醫也。」
天之方懠才細反,叶箋西反,無為夸苦花反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許伊反,則莫我敢葵。喪息浪反亂蔑資叶箋西反,曾莫惠我師叶霜夷反。
賦也。懠,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尸則不言不為,飲食而已者也。殿屎,呻吟也。葵,揆也。蔑,猶滅也。資,與咨同,嗟嘆聲也。惠,順。師,衆也。○戒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為也。又言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於散亂滅亡,而卒無能惠我師者也。
【纂疏】疊山謝氏曰:「『威儀卒迷』,《書》曰『夫人自亂于威儀』是也。」濮氏曰:「威儀盡亂,侮老慢賢,善人則如尸而不復言語矣。」嚴氏曰:「無以為資,言其無生生之計,曾莫有施惠我衆民者,皆責之辭。」似通。
天之牖民,如壎許元反如篪音池,如璋如圭,如取如擕。擕無曰益,牖民孔易以豉反,叶夷益反。民之多辟匹亦反,下同,無自立辟。
賦也。牖,開明也。猶言天啓其心也。壎唱而篪和,璋判而圭合,取求擕得而無所費,皆言易也。辟,邪也。○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邪?
【纂疏】《說文》:「在屋曰囱音窻,在牆曰牖。」毛氏曰:「土曰壎,竹曰篪。」孔氏曰:「半珪為璋,合二璋則為珪。」毛氏曰:「『如壎如篪』,言相和也。『如珪如璋』,言相合也。」嚴氏曰:「六章至八章,皆責僚友,而因以誨王也。」
价音介人維藩叶分邅反,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叶胡田反。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叶胡罪、胡威二反,無獨斯畏叶紆會、於非二反。
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師,衆。垣,墻也。大邦,强國也。屏,樹也,所以為蔽也。大宗,强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
【纂疏】李氏曰:「『价人』,或以為大人,或以為善人,或以為掌軍事者,無所經見,姑兼存之。『宗子維城』,言同姓之宗子,亦當以德懷之。左氏曰:『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曹氏曰:「藩、垣、屏、翰備,宮室可以安矣。若夫城則周乎其外而為之固守,宗子之譬也。國之枝葉休戚同之,藩、垣、屏、翰,恃之以為固,故大封同姓以為磐石之宗,此周之所以宗強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用朱反,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叶謨郎反,及爾出王音往,叶如字。昊天曰旦叶得絹反,及爾游衍叶怡戰反。
賦也。渝,變也。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衍,寬縱之意。○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懠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不之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兹者乎?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附錄】時舉問:「『天體物而不遺』,是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不在』,是指人而言否?」曰:「『體事而無不在』,是指心而言也。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耳。」時舉。旦與明只一意。這箇豈是人自如此?皆有來處,纔有些放肆,則他便知。所以曰:「日監在茲。」又曰:「『敬天之怒』至『無敢馳驅』。」道夫問:「『渝』字如何?」曰:「變也,如『迅雷風烈必變』之變。」道夫。道夫又問:「昨所論『昊天曰明』云云[48],此意莫只是言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曰:「公說『天體物而不遺』,既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今所以理會不透,只是以天與仁為有二也。今須將聖賢言仁處,就自家身上思量,久之自見。」同上。
【纂疏】嚴氏曰:「『戲豫』即《無逸》所謂『耽樂』,『驅馳』即《無逸》所謂『游田』。」鄭氏曰:「及,與。遊,行。衍,溢[49]。昊天在上,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遊溢相從[50],可不謹乎[51]?」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1]「履」原作「里」,據朱熹《詩集傳》卷十七改。
[2]「何如」原作「如何」,據《朱子語類》卷八十一改。
[3]「孔子之言」四字,《朱子語類》卷八十一無。
[4]「嚴氏曰」云云,未見於嚴粲《詩緝》,實乃《毛詩正義》孔疏文。按孔疏對姜嫄身份之說法,與《詩緝》有明顯差異。
[5]「履」原作「里」,據朱熹《詩集傳》卷十七改。
[6]「祥」原作「詳」,據朱熹《詩集傳》卷十七改。
[7]「封」上,《周禮注疏》卷八有「犯之者」三字。
[8]「亦」,謝枋得《詩傳注疏》卷下作「以」。
[9]「叙」原作「序」,據《朱子語類》卷八十一改,下同。
[10]「禮」原作「里」,據朱熹《詩集傳》卷十七改。
[11]「謂」字原無,據李樗、黄櫄《毛詩集解》卷二十四補。
[12]「翦」原作「剪」,據朱熹《詩集傳》卷十七改。
[13]「漆」上,《毛詩正義》卷十七之二有「不言畫,則」四字。
[14]「《荀子》云」,《毛詩正義》卷十七之二作「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按「天子」至「黑弓」,亦見於《荀子·大略》,文字略有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