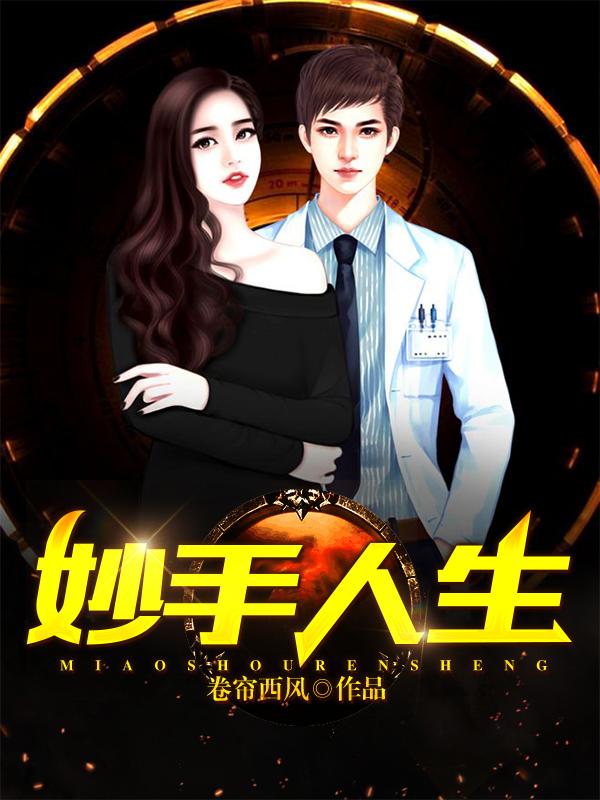奇书网>白寿彝史学论著奖 > 通识和器局(第2页)
通识和器局(第2页)
第二,前一个办法很容易引导我们的历史工作陷入大汉族主义的偏向。因为在这个办法处理下的地理条件,很容易限制了本国史的内容,要使它成为单独的汉族的历史或汉族统治者的历史,要在“汉族”或“汉族统治者”和“中国”之间画上等号。后一个办法采用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它可能使本国史有丰富的内容,可能使本国史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可能使本国史告诉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的历史的由来。
第三,前一个办法可能引导我们把本国史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孤立地看,不能把历史和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后一个办法,恰巧相反,是要求我们从了解现在社会生活的意义上去研究历史的。
从这三点来说,用皇朝疆域的观点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错误的办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正确的办法。我们应该消灭前一个办法。我们应该建立后一个办法。[10]
白先生关于对历史上中国国土问题的处理意见,既考虑到历史上的发展形势,也考虑到新中国的现实状况,是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从而克服了对于国土问题的片面性认识,同时也正确地回答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他的这一见解,被许多同行所认同,对于新中国的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90年,白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就“统一多民族国家”,讲了3个问题:“一个是统一规模的发展,一个是统一意识的传统,一个是‘一’和‘多’的关系。”[11]其核心思想,仍然是“统一”和“多民族”的问题。可见,在40年中,他的民族观是始终围绕着这一条主线一以贯之的。
白先生关于民族史的见解以及如何进行民族史研究,有许多精辟的论点和重要的设想,这些论点和设想,在民族史研究领域产生了突出的积极影响。
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白先生的3篇文章,一篇是《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的讲话》(1981年),一篇是《说民族史——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召开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还有一篇是《关于民族史的工作——在中国民族史学会上的讲话》(1988年)。在这几篇相互关联的文章中,白先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
首先,是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针对学术界久已存在的友好合作、互相打仗这两种对立的说法,白先生指出:
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在民族关系史上,我看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这一点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当然,历史发展是波浪式地前进、螺旋式地前进,有重复、有倒退,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总会有曲折、有反复,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总的讲,我们各民族的共同活动,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种情况,在某些地方可能是有意识的,在另一些地方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它都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份贡献。可能有的民族贡献多一些,有的民族贡献少一些,有的更重要一些,有的不太重要。这大概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的。[12]
白先生的上述论断,深入浅出地回答了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的问题。此论一出,原来的争论双方都表示认同,很少再有类似的争论了。从这里我们得到这样的启示:看待复杂的历史问题,既要从具体环节考察,更要从整体上和发展趋势上考察;既要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又要看到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及其辩证演进的前景。
其次,是关于主体民族问题。白先生出身于回族,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能够从历史事实、从全民族的利益上来看待民族史问题。这里说的“主体民族”是他的民族史观的又一个重要论点。他认为:
汉族是中国历史上的主体民族,这个提法对不对?我说对。为什么?因为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无论在哪个时期,都是人数最多、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在某些方面,汉族可能不如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超过了汉族。但总的讲,汉族水平是比较高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始终成为我们国家的稳定力量。没有这个民族不行。……中国历史几千年连续不断,在世界史上是少有的。这个功劳,汉族应居第一位。如果没有汉族,少数民族做不到这一点。当然,我们说汉族是主体民族,并不是说少数民族无关紧要,并不是说这个老大哥可以欺侮兄弟、压迫兄弟。绝不是这样。我们说尊重汉族的历史,这跟大汉族主义是两回事。汉族成为主体民族,可能成为大汉族主义思想滋长因素之一;但不等于说,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就一定要产生大汉族主义。[13]
白先生进一步分析说: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稳定力量,并不因为元代是蒙古贵族的统治、清代是满洲贵族的统治而有所削弱或受到排挤。元代和清代的统治,尽管是少数民族的贵族当权,但必须得到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没有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蒙古贵族、满洲贵族的统治也不可能稳定。这个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14]
白先生所论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发展白先生的上述论点,从元朝、清朝统治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历史文化认同方面做进一步的说明。应当强调的是,这方面的历史资料的发掘和阐说,尚有很大的空间。作为白先生的门人,我们有责任去努力从事这一工作,使白先生的学术观点进一步发扬光大。
再次,是关于少数民族对边疆的开发和捍卫问题。白先生的民族史观和民族史研究,总是从“多民族”的视角出发,其中蕴含着深刻的辩证观点和全局意识。他在讲到研究和撰写“多民族的统一”的历史时,强调指出:
我们要写多民族的统一,写各民族同汉族在相互关系上的发展。各族有各族的特点,但也离不开“共同性”。第一点是对边疆的开发,少数民族出了很大的力量。没有他们,边疆开发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他们在边疆地区繁衍、生息、生产劳动,不断开拓,经历了多少个世纪。旧的史书,把少数民族同汉民族的关系,写成了是少数民族不断文明化的过程,这是不对的,正是少数民族开发了那个地方。第二点是要大写我们少数民族如何捍卫我们的边疆。这两方面的材料可多可少,但内容很要紧。没有这两点,就没有今天的中国。[15]
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少数民族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对边疆的开发和捍卫,可以说是最重要、最伟大的贡献。“没有这两点,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这样一个深刻的结论,是真正把少数民族的地位放到历史的高度和现实的价值加以估量和评价。对于这一结论,当今的史学工作者,仍有深入理解、深入研究的必要。
最后,白先生还谈到了研究和撰写民族史的以下问题。
——关于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工作和理论指导问题。白先生指出,不应把资料的收集、整理看作是简单的工作。他说:正史中的资料、正史以外的资料、地下出土的资料,以及外国传教士和外交官的资料、外国政府公布的档案资料等,都应当关注。他认为:“这些年,我们的资料工作做得不少,但重视得还不够,还不能摆在应有的地位上去看待。有些单位把资料工作一律看成是简单的工作,这是不对的。资料工作中,有比较简单的,有相当复杂的,有时比写论文还要难。”[16]这些话,把资料的大致范围及其重要性都讲到了。
同时,白先生又强调了理论指导的重要性。他既有原则又有分析地指出:
又一件事,是理论方面的。我们的民族史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不可动摇的。说是指导,是指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上的指导。我们要在指导下工作,要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史里,有不少理论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有待于深入的发掘。我们对一些已经提出来的问题,已经习以为常的看法,还是可以重新提出来进行再认识的。[17]
从这里可以看出,白先生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民族史的结合,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民族史研究的正确方法。这是白先生始终不渝的治史宗旨,即以唯物史观同具体的研究对象结合起来,从中提出理论性的认识,用以得出合理的历史结论,并丰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白先生还进一步解释重视理论在学术发展上的意义,他说:
理论更高的成就,在于能有更多方面的联系,能解释更多的矛盾。因此,我们也就必须有更广阔的视野。我们民族史工作者,各有自己的专史、专题,但不能作茧自缚,要把上下古今、左邻右舍尽可能地收入眼下。我们必须注意,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至少需要懂得一些其他有关的民族的历史,懂得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同志们,我们的工作是必须付出艰苦劳动的工作。但同时,我们是在进行推动历史前进的工作,意义是很深刻的。[18]
白先生从自己的治学经验中总结出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我们这些晚辈和中青年史学工作者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思想遗产。重温他的这些话,感到格外亲切、格外有分量。
——关于民族史的撰写形式问题。白先生在中国史学史方面的造诣,使他能从中国历史编撰的优良传统来看待史书编撰问题。关于民族史的撰写形式,他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
民族史的写法不要千篇一律。不一定都写成社会发展史的形式,体裁可以有多种。否则很多东西不易写进去,要不拘形式。按照各民族的材料,采取适当的形式,不要写得太呆板。
不要只引用经典著作。经典著作的结论,不能代替历史。历史是具体的。比如说,某个民族是哪一年形成的,不好说。这都有个长期的过程。写书的时候,也可以使用传说。汉族的历史就有很多传说嘛。写明它是历史传说就是了。有的传说可能失真,但不能说完全无真实性。它总有个历史的影子嘛。提供材料、讨论,需要人多一些,但写书时无须太多人。人多了不好办,改也不好改,总得有拿主意的人。学术问题不能投票,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写成的书稿要保证有一定的水平。[19]
理论、形式、历史、传说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都是历史编纂中要碰到、要正确处置的问题,白先生也都讲到了。可以看出,他在民族史研究方面,从一般性原则到如何着手去做,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些是他亲身的经验,有些是他的设想,都值得后人珍惜。
除了在理论、方法论的遗产方面,白先生主编的《回族人物志》[20]和《中国回回民族史》[21]也反映了他在民族史撰述上的主要成就。
三、史学史理论与史学史撰述
白先生自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从事中国史学史教学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工作,并创办了内部刊物《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即今《史学史研究》季刊)。
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认识和研究,同样显示出他的通识和器局,从而得到这一研究领域的同行的尊敬。他在这一研究领域所表现出来的通识和器局,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对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认识和阐述。中国史学在目录学方面有丰富的遗产,而在20世纪上半叶又有多种史部目录解题或要籍介绍的专书问世。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怎样从史部目录学和要籍介绍的形式中走出来,从而成为史学史这门专业学问的发展史?20世纪前期,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做了初步的尝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刘节在教学中也做了可贵的努力,这见于他的学生们所整理的讲稿《中国史学史稿》。白先生认为,要把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推进到新的高度,首先必须明确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任务。他在1964年发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主要是“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以及努力做到理论和资料的结合。他指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阐明规律(包括思想发展的规律和一些技术上的规律)是可以做到的。而总结成果主要是下功夫研究史学上的一些代表作。这两点,只有在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详细占有资料的情况下才能做到[22]。
《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是一篇理论文章,如果我们联想到白先生此前发表的《谈史学遗产》一文,以及他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30部代表作的有关见解,就可以理解他所说的“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的丰富内涵。白先生在1961年撰写的《谈史学遗产》这篇长文中,提出应当重视七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史学基本观点的研究(含对历史观的研究、对历史观在史学中的地位的研究、对史学工作的作用的研究),二是关于史料学遗产的研究,三是关于历史编纂学遗产的研究,四是关于历史文学遗产的研究,五是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前人已有成果的研究,六是关于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研究,七是关于历史启蒙书遗产的研究[23]。其中,有些观点在他20世纪80年代所写的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中,又有了新的发展[24]。显然,如果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结合有关历史著作来研究中国史学史上的这些问题,我们就有可能不断认识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