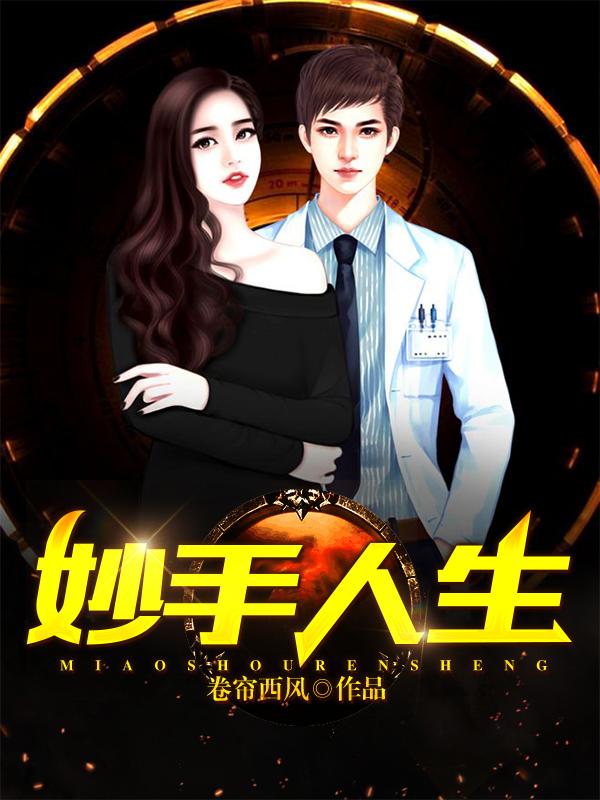奇书网>白寿彝史学论著奖 > 通识和器局(第1页)
通识和器局(第1页)
通识和器局
通识和器局[1]
——纪念白寿彝先生百年诞辰
引言
2009年2月19日,是白寿彝先生100周年诞辰的纪念日。很早就想到要写一点纪念文字,以表达自己对老师的缅怀之情。可是提起笔来,总觉得要写的东西很多很多,真不知从何处着笔。想了很久,我想用这样四个字来概括白先生的学术特点和治学宗旨,或许更能反映我对自己老师为学风格的理解。这就是:“通识”和“器局”。
从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2],到郑樵倡导“会通之义”[3],再到章学诚总结出来的“通史家风”[4],以及龚自珍所说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5],都包含了知识的渊博、器量的宏大和见识的深刻,可以看作是历史上的史学家的“通识”和“器局”。
白先生学术的特点,正是继承、发展了史学上的通识和器局。对此,我以前有一点朦胧的认识,而现在比以前又多了一些理解和认识。1981年,白先生在《史学史研究》上连续发表了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的文章。我在阅读、学习中的那种激动和沉思交织在一起的心境,至今难忘。1981年年底,我写了一篇读后的认识《史学遗产和史学研究——读书后》,发表在《史学史研究》1982第1期上面。其中,第三部分讲的就是“专长之才和通识之才”的问题。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的四篇《答客问》,以论说理论问题开篇,引用和评论了一百八十种左右书刊,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而又采取问答体的形式,反映了作者本人也是努力在用德、学、识、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这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的一种‘身教’吧。”
20多年过去了,随着岁月的逝去,我对白先生著作的精髓也懂得多了一点。白先生的通识和器局,在他所研究的诸多领域,都更加鲜明地显现出来。
一、理论与通史
白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把它用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他从未中断这种努力,也从未改变这一方向。他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善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并把它同自己的研究对象结合起来,从而提出自己的见解。白先生写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的目次中,有这样几个标题:“历史理论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理论二:物质生产和物质生产者的历史”;“历史理论三:社会历史之辩证的发展及其规律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丰富的内容,白先生所强调的这几个基本原理,无疑是很重要的。诚如他所理解的那样:“历史理论,首先是史学领域的哲学问题,主要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上的地位问题,历史进程有无规律可循的问题。”[6]从思想史研究和历史研究来看,这几个问题,不仅是重要的,而且也是经常会引起这样那样争论的问题。白先生强调这几条原则,自有其针对性。
白先生善于把理论运用于指导他所从事的研究,不仅有明确的和坚定的信念,而且具有突出的实践性和艺术性。那种高屋建瓴的气势,真有**之感。举例来说,如他在《中国通史纲要》中撰写的《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实则是一篇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宏论。文中不仅明确地划分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各个阶段及其特点,而且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一见解的核心价值,是充分地考虑到了在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的变化。因为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这一主要矛盾的矛盾主要方面,其变化直接影响到对劳动力的占有形式和剥削形式的变化。具体说来,他把秦汉时期的世家地主、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门阀地主、五代宋元时期的品官地主和明清时期的官绅地主的出现,并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作为将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的标志之一的观点[7],已为不少学者所认同。
又如,白先生在主持制定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导论》卷时,曾确定要写出12个方面、346个问题的理论性著作,作为统率《中国通史》的开卷之作。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白先生要我撰写“家庭”一章。白先生说,在《中国通史》中,难得有机会在某一个地方专门来写中国历史上的家庭,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有必要在导论中对它的演变做一个概括的阐述。后因种种原因,《中国通史》的导论没有执行这一撰述计划,但白先生仍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构想。而目前我们所读到的《中国通史》的《导论》卷所包含的9个问题,还是十分突出地显示出它的主编的通识和器局。这9个问题是:
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
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
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
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
国家和法;
社会意识形态;
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
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
中国和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白先生在《导论》卷的题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他说:
本卷只讲述一些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不能对中国历史做理论上的全面分析。一九八一年六月,我们在《史学史研究》第二期上发表了导论的提纲,提出了中国历史的十二个方面,三百四十六个问题,涉及面相当广泛,但在短时期内不能对这些问题都进行研究,经过反复讨论,拟定了现在这样的内容。一九八一年的提纲,我们认为仍值得参考,现作为附录,附在本卷之后。[8]
这里说的“只讲述一些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他用“涉及面相当广泛”来表明12个方面、346个问题的价值,故作为《导论》卷的附录,这既可以反映编撰者的思路和工作进程,也可供将来的研究者参考。
还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即上述9个方面的问题,既不是讨论历史过程,也不是空发议论,而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阐述相关的理论认识。可以认为,这是比较系统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而做的理论论述,是唯物史观取得民族形式的一种途径。在唯物史观受到来自国内外的非难和挑战的时候,《中国通史》的《导论》卷的出版,一方面反映了主编白先生的通识和器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所指导下的学术群体的实事求是的、开放进取的学术心态。该书面世将近20年了,但仍然具有理论上的价值。
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出版,而中文版已印刷了30多次;他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誉,并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称颂,这同他在通史方面的通识和器局是密不可分的。
二、民族观与民族史研究
白寿彝先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白先生又是一位出身于少数民族的史学家。这两个因素,使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具有深刻的和创造性的理解。他的通识和器局,在这方面也反映得十分突出,为治民族史者所推崇、所尊敬。
白先生在《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的题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现有的和曾经有过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这一点认识……逐渐为我国史学工作者所普遍接受。这在史学思想上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它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我在多年断断续续的摸索中,对民族史有两点体会。它经历过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区域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以至当前社会主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统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又一点是,尽管在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的民族斗争,甚至于出现过民族战争,但从整个历史的发展看,我国民族之间总是越来越友好。友好并不排斥斗争的存在,斗争也不能阻挡友好关系的前进。[9]
上面这段话,大致可以表明白先生的民族观和民族史观。
显然,白先生的民族观的核心是:“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现有的和曾经有过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民族宗教论集》开篇就是关于“国家与民族”的论述。白先生的这一民族观,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已经初步形成了。他在1951年写的《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一文中指出:
为了说得更清楚,我们不妨说,对于本国史上祖国国土的处理,是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皇权统治范围的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或伸缩。又一个办法是,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研求自有历史以来,在这个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动。这两种不同的办法,显然表示着不同的思想倾向:
第一,前一个办法显然还受着传统的历史观点的支配,就是还受着皇朝历史观点的支配。尽管我们在本国史的工作中,主观上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并且事实上也已经站在人民的立场,但如果用这样的办法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那么,至少在这一点上,还没有从旧的非人民的,甚至是反人民的立场上得到解放。这和后一个办法是不同的,后一个办法是已经摆脱了旧的观点,完全从旧的立场上得到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