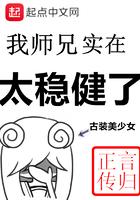奇书网>清末新史学 > 一发端新探(第1页)
一发端新探(第1页)
一、发端新探
1896年6月15日,清政府驻日本东京的公使馆里,出现了十三位长袍马褂、脑后垂辫的中国青年。这件事后来被视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转折点。[1]著名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前辈学者实藤惠秀先生在其开拓性著作中,首先把它定为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发端。此后几乎所有研究留日学生史的学者都接受这一看法或与之不谋而合。尽管有的著作将此事与清政府确定留日国策区别开来,并且分析了一些背景情况,但仍然承认其发端地位。[2]
然而,究竟以何时或什么标准定为留日学生发端更为妥帖,并非没有疑义。这一问题至少牵涉四个方面的关系,其一,它标志着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主要流向的逆转。在茫茫大海的古老航道上,过去是运载日本学问僧的帆船驶来大唐,现在却是中国学生搭乘邮轮开向扶桑。其二,它是中国人留学日本的正式发端,在近代中国留学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三,它显示了甲午战后中日关系的变化,表明在战争中失败的一方认识到向战胜国学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揭开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其四,它是近代中国向外国学习进程中的一个界标。派遣留日学生及其队伍的膨胀,使得中国人学习西方不仅主要转向以日本为媒介,而且越来越带有东方色彩,表现出开眼看世界视野的拓展。在确定留日学生运动发端时,应当从以上几方面通盘考察。实藤先生正是想指出这些意义,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引述了日本舆论界的有关评论。可惜所引《太阳》杂志的两篇文章,都是1899年后的作品,不能说明1896年这十三位中国青年出现于日本所引起的反响,以及这一事件的性质和意义。
这十三位青年是:唐宝锷、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翚、吕烈辉、吕烈煌、冯訚模、金维新、刘麟、韩筹南、李清澄、王某和赵某。清政府何以要派遣这些学生东渡?事情还要追溯到中国向日本派驻公使之始。
1877年,清政府任命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驻日公使,在东京设立公使馆。起初以为“中东本同文之国,使署中无须另立译官”[3],结果洋相出尽。一年后,何如璋便向总理衙门抱怨:“东学翻译最难其选,因日本文字颠倒,意义和舛,即求精熟其语言者亦自无多。”不得不“暂觅通事二名”,并要求驻横滨、神户、长崎等地领事“就地觅一通事,以供传宣奔走之用”[4]。这显然有损于堂堂大清国钦差的体面,不利于沟通内外之情。所以继任公使黎庶昌就以“使署理署需用东文翻译”为由,“奏请招致学生设馆肄业,以三年为期”[5],在使署西侧设立一所东文学堂,“专为学习翻译”,于1882年11月正式开馆。以后即沿为定制,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才一度中断。十余年来,成效甚微。后来的驻日公使裕庚评价道:
既专为学习翻译而设,不过学至翻译而止,入手之初,未尝计及深造。学堂既设在使署,去高等师范甚远,无所折衷,一教众咻,事事皆从简略。名师既不相就,学生则饱食而嬉,以致成材甚少。使臣虽日加督责,而众人视为具文。又所定章程奏明拔充学习翻译后照章褒奖,并可分派各口充当翻译,于是学生甫满三年,知此捷径,群思弃而之他。既到各口后,又复荒其本业,不加温习,一经传语,动辄贻笑,翻译东文,错谬多端。[6]
总之是一塌糊涂。尽管裕庚的话不乏官场中司空见惯的贬低前任恶习,以及在变法浪潮之下的自我吹嘘,多少还是反映了一些实情。
甲午战后,裕庚接任驻日公使,于1895年9月抵达东京,不久即着手恢复东文学堂。他与日本外务大臣兼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多次商议,认为在使馆内设立学堂不如将学生送到日本学校附读,较为切实。遂将此意报告总理衙门。次年4月,总署奏请批准了这一要求。裕庚遂派已预定为横滨领事的湖北补用知县吕贤笙前往上海、苏州一带招收学生,往返两月余。1896年6月15日,吕率领选定的十三位青年抵达东京。他们在使署寄居半月后,于6月30日入校学习。
按照中日双方达成的协定,这批学生的教育委托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负责,由他和裕庚共同在高等师范附近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校”,由本田增次郎任东文监督,町田弥平为东文教师,两人的束脩以及学校的全部费用由清驻日公使负担。开始这些学生连假名也不认识,以后课程逐渐增加,共分为两类,除星期日外,每天上午和晚上由教师教授或自习外交史、日本文法、日本尺牍、汉文、日文书写以及阅报等,下午则到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地理、初级高等物理、高等初级数学、历史、兵式体操。[7]
由上可知,这批学生的所谓“留学日本”,不过是在延续原来使馆东文学堂的基础上略加变通,即将以前专属于使馆的东文学堂改为同时还由日本文部省委托的高等师范负责部分教务;所学课程则从专攻日文扩大到一些基础科目;学堂也由使馆迁到高等师范附近的一座校舍。但是,这些并未改变东文学堂的性质。
首先,培养学生的目的没有变,仍是训练为使馆服务的翻译人才,因而官方继续称之为“东文学生”。直到1898年,清政府没有再派学生留日,裕庚也未提出这种要求。因为10名翻译已足以应付使馆业务需求,而清政府并没有将他们别作他用的意向。学习基础课程,最初不过与京师同文馆一样,仍是为了翻译上的需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特别是变法运动的兴起,才逐步扩大用途。
其次,学堂及学生的隶属关系没有变,学生并不是直接进入日本学校,而是单独设立了一个附读班,这样既便利了学生学习,又保证了使馆的权限。不仅全部的学生学费、教师薪水和学堂费用由使馆承担,[8]而且每隔一星期要将学生接回使署面加考验,“教师教导不力者,告知学校长更换;学生怠惰荒嬉者,由学校长转告使署撤回”。其中3人不久即因“纨绔性成,紊乱规则”,受到“登时撤令内渡”的处分。[9]甚至学生患病也由使馆接回调理,并负担一应车、饭费用。
东文学堂的复办及其变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甲午战争前后中国人对日观复杂变化的心路历程。甲午一战,清政府水陆两军在历来不为中国士大夫所正视的“倭寇”手下惨遭败绩。但是,统治集团的君臣们,包括以“求新”自我标榜的洋务派,都没有向自古就从中国引进文明的战争对手学习的勇气和胆识。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强盛,早已使清政府感到震动。特别是历届驻日公使,耳闻目睹那些日新月异的变化,都意识到日本将成为中国的一大威胁。首任公使何如璋即实际上承认明治维新是“时事之转移固自有其会”[10],继任黎庶昌也感到日本“近年事事讲求,海陆两军,扩张整饬,工商技艺,日异月新,物产又极富饶”,“其力量几与西洋次等之国相敌”[11]。然而,要放下大清皇朝钦差的架子向“倭夷”屈尊,实在是他们不敢也不愿想的事。
权力之争和策略考虑曾导致一部分洋务派官僚倾向于联合日本。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主张与英日结盟反对沙俄,形成一个松散的联日派。但他们更要维持居高临下的门面,自欺欺人地说日本是易于笼络的小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洋务派很难提出学习日本的政策。尽管他们出于洋务的需求,可以向日本派遣少数留学生。
敢于学习日本,是维新派的功绩。一些早期维新思想家在将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进行比较时,明确指出二者的优劣是非。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不仅公开把日本由变法而强盛的事实作为范例,而且在制定变法方略时,不同程度地参照借鉴了明治维新的模式与经验。不过,甲午战争前,就是在这批人的心目中,也还或隐或现地含着对“区区三岛”的轻蔑之意,因而在承认明治维新成就的同时,多少保留了几分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尊。
甲午战败的惨痛事实,打破了洋务运动30年,国防“深固不摇”的神话,人们不得不对东洋人刮目相看。但战败屈辱所激发出来的民族悲愤情绪和同仇敌忾心理,使人们一时还不能冷静下来思考问题。而三国干涉还辽成功所引起的远东局势新变化,又给沙皇的狰狞面目蒙上一层柔光。在统治集团中占上风的亲俄派固然奉沙皇为救星,就连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也来了个180度急转弯。刘坤一上书密陈联俄拒倭大计,正式承认自己过去的失误。他说:“或谓俄与中国接址最宽,将来必为害于中国。臣前此亦以为然,今则颇知其说之谬。”“以臣愚见,各国之患犹缓,惟日本之患为急。”因而建议:今后“凡与俄交涉之事,务须曲为维持;有时意见参差,亦须设法弥缝,不使起衅。中俄邦交永固,则倭与各国有所顾忌,不至视我蔑如,狡焉思启矣。”[12]
在朝野上下一片联俄拒倭的喧嚷声中,无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提出学习日本的口号。1895年张之洞奏议战后补救之策,建议派遣留学生,也仅以欧美为念,没有提到日本。裕庚后来自称到东之始,即以为“翻译不过学业之一途”,俨然已有“振兴人才为本原计”[13]的设想,未必属实。他讲这番话时正值变法运动**,意在邀功,并非真有维新宿志。裕庚任期两年内东文学生人数只减不增,就是对他本人最有力的驳斥。
由此可见,1896年戢元丞等人东渡,既不是甲午战争刺激的结果,也不是中国人认识到向日本学习的必要性,因而鼓动留学日本的产物。甲午战争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的确大大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变革决心。但历史毕竟是具体而复杂的,如果把战后的一切变化都与此直接联系起来,看不到在警醒与学习敌手之间还有一个转变过程,而且其难度不亚于鸦片战后士大夫经历的磨炼,则不免失之简单笼统。
那么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发端定于何时为宜呢?
从中国方面看,产生派遣留日学生的动议比较晚,而日本方面则早就有此打算,特别是日本军政界中一批对华野心不断膨胀的人,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之日起,就积极策划利用互派留学生来培植亲己势力。“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根据奉使北京的实际经验,深感对华问题不能付之等闲。迨西南战役以后,一八七七年十二月,趁中国首任公使何如璋、副公使张斯桂等抵达东京的时机,为两国间彼此交换留学生及善邻亲睦起见,特纠集少数有志之士,创设振亚社,不时集会。”[14]1880年3月,这批人组成了兴亚会,特邀何如璋到会祝词,并开办中国语学校,教授日本青年。1898年,该会将横滨大同学校总教习徐勤以及自费前往日本留学的维新派骨干罗普吸收入会。[15]以后兴亚会并入东亚同文会,后者成为日本最积极干预中国留学生事务的组织,先后在东京和中国的上海、南京等地开设同文书院。1902年又利用成城学校入学事件企图取得保送自费生进入日本军校的垄断权。不过,兴亚会提出的互派留学生的计划,由于中国方面持有戒心,长期未能付诸实现。
关于留日学生的概念,并无严格界定,其中不仅有从中国本土去的青年,也包括旅日华侨商民的子弟。有些专为后一类人开设的学校,如神户的同文、横滨的大同学校,后来也吸收国内来的学生。而第一所华侨子弟学校横滨中华学堂,早在1885年即已创立。[16]不过,按照惯例,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将这些学校的学生算作留学生,一是就读于此的华侨子弟进入日本学校,一是国内前来求学的青年。[17]这一约定俗成的概念同样适用于使馆东文学生,如唐宝锷、胡宗瀛在留学生题名录上签署的留东日期,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进入早稻田大学和青山农学校,[18]而不是1896年6月进入附读班,可见他们本人也没有把1896年东渡视为自己留学生涯的正式开端。
我国最早名副其实前往日本留学的是广东顺德人罗普。罗字孝高,是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嫡传弟子。1897年,他只身漂洋过海来到日本,次年初“由日本当道举入”早稻田专门学校学习法科,“讲习万国律例之学”[19]。据与他同屋居住的日本友人田野桔次说:“当时东京留学生亦未有一人也。”[20]冯自由《革命逸史》称罗是中国学生进入早稻田专门学校的“第一人”[21],其实他也是近代中国留学日本的第一人,起码是首批留日学生的代表者。
与之同时,还有一些民间人士前往日本求学。如1898年1月汪康年到日本考察报务之际,就在大阪见到正在山本宪的家塾中学习日语的汪有龄、嵇侃两位留学生。[22]当然,他们的行动仍属个别现象,但反映了当时中国人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意向,预示了一种呼之欲出的新趋势,表明中国人留学日本是维新浪潮推动的产物。罗普赴日是否得到康有为的赞助支持,不得而知。不过,维新派的《知新报》将此事列入“创新要事”,予以综合报道,称赞其“慨然有志”[23],表明了这一派人的态度。
甲午战后,维新人士以战争胜负的鲜明对比为据,大声疾呼变法图强,指出日本强盛的原因之一,在于“遣宗室大臣游历各国,又遣英俊子弟诣彼读书”[24]。日军所以屡胜,是因为“将士出于学校,练习有素”[25]。梁启超还上书张之洞,认为“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而日本学校以政治为最重”;中国对西学则“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26],建议效法日本,改革体制课程。一面鼓吹留学的必要与重要,一面比较中日的优劣,自然有助于造成学习日本的舆论氛围。
中国有可能派遣留日学生,也由于战后中日关系的紧张状态有所松驰。1897年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沙俄趁火打劫,紧跟着占领了旅大。这种**裸的侵略行径,给那些曾对沙俄抱有幻想的人当头一棒,朝野上下齐声痛斥沙俄背信弃义,亲俄空气一扫而光。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旧调重弹,提出“以兼联英日为要策”[27]。维新派对此积极呼应。胶州湾事件后,日本参谋本部派人来华请助联英拒德,“时经割台后未知日情,朝士亦多猜疑日本,恭邸更主倚俄,乃却日本之请”。康有为走告翁同龢:“明日本之可信,且与日使议请将偿款再摊十年,并减息,日使矢野君极有意。”又为御史杨深秀、陈其璋等草疏请联英日,并作联英日策,遍告朝士。经此事后,“朝士渐知英日之可信,而知俄之叵测,自此群议咸知联英日矣”[28]。康有为趁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直截了当地建议光绪奉日本为楷模,变法图强。汪康年等人也前往日本,试图联合中日民间势力以救危亡。这一努力得到以江浙为中心的开明士绅的广泛支持。这样,中国派遣留日学生的主客观条件开始形成。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借机施展外交和文化手段。1897年底,日本参谋本部军官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等先后来华,在武昌与张之洞、江汉关道以及洋务委员等晤谈,转达参谋部川上操六大将之意,诡称:“前年之战彼此俱误,今日西洋白人日强,中东日危,中东系同种同文同教之国,深愿与中国联络。”请中国派人到日本“入武备及各种学堂,地近费省,该国必优待切教”。清廷担心引起其他列强的进一步要求,谕令张之洞“断勿轻许”[29]。但张之洞不肯作罢,一面再次奏陈:“惟彼言深悔前年不应与中国战争,今愿遣我人赴东入各种学堂云云,洞甚嘉许之。”[30]一面决定让郑孝胥等3人于次年春选派学生“赴东洋入武备农工各学堂”[31]。
1898年,维新运动声浪日高,日方活动也更加积极。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于5月间函告总理衙门:日本政府“拟向中国倍敦友谊,藉悉中国需才孔亟,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该国自应支其经费”。接着又亲赴总署面陈:“中国如派肄业学生陆续前往日本学堂学习,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