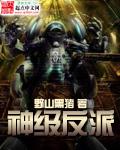奇书网>王阳明良知四首 > 五小结(第1页)
五小结(第1页)
五、小结
比较王华与阳明的会社性质,可以发现在王华那个时期的会社活动内容,一方面逐渐脱离程朱思想的牢笼,从对传统经典的探讨,开始有一些不同的学术意见出现。这些意见也间接地影响到阳明,使其在反省传统学术思想时,能够比当时一般的士人更没有思想的羁绊,而独立地思考儒家思想中的关键概念。另一方面,由于会社内容不仅仅于讨论学术议题,对于所谓一个人“德业”的关注,也是当时相当重要的议题。而这种要求“道德”的声音,在往后阳明所参与的会社活动中,却几乎未见类似的内容。这显示出阳明所处的学术风气,大体上走向诗文辞章之学,而对于儒家传统所极力表彰的君子“德性”,却流于口耳之学。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当士大夫们遇到利益攸关之时,自然也就不可能对“道德价值”有所坚持了。从正德元年“诛八虎”事件中,乃至于往后朝局的发展,都无不验证这样的社会现象:没有“道德”观念,也就没有是非的存在。因此,离京师千里之远龙场的阳明,站在一个“小人得志”与“君子道消”的环境之外,思索该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是“君子”,而非“小人”?
阳明认为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每个人的“私欲”上,是大大夫官员们因为无法克除私欲,才导致“丁卯之祸”。而阳明认为当时学界所认知的外在的道德规范事实上只能喝止私欲的蔓延,并无法根本地祛除私欲;而宋儒静坐的方法也只能达到一时的洒脱境界,仍会有私欲再度丛生的问题。最后,经由“舜”这个圣人的所作所为的启发,促使阳明体认到圣人与人都具有“明德”,只不过差别在于圣人时时去其私欲而能自明其明德,但一般人则无法时时祛除私欲,导致“明德”被遮蔽。而一个被遮蔽明德的人就是小人,所以,要成为君子的关键就在于祛除私欲。而阳明从朱子的思想出发,通过对其读书法中“格物致知”概念的重新理解,体认到所谓“心即理”的说法。他认为只要能够保持那“不为物欲侵扰的心”,即能以此“心”,来应接事物,所以功夫应该在如何去除私欲的方面做。而从事后他对“格物致知”的说法,可以知道“格物”是“去其心之不正”。所以,所谓“自明明德”是与“去其心之不正”同时发生的,一旦能去其心之不正,即能自明明德,也就是所谓“知行合一”的功夫。阳明认为通过这个功夫论,即能成为“君子”,也就可以经纶天下。
[1](明)李梦阳:《熊士选诗序》,见《空同集》(文渊阁四库全书·集1262)(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五十二,页475d—476a。
[2](明)黄景昉:《国史唯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成化弘治》,卷四,页112。
[3](明)罗玘:“公越人也,少有重名,勾吴以西,湖湘以东,使日月争迎聘致,以公至卜宠辱焉!及起而魁天下,朝之大夫士与天下之人以‘何如人’望公哉!”见《送冢宰王公归余姚序》,《圭峰集》(文渊阁四库全书·集1259)(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十,页142b。
[4](明)黄瑜:“明年乙未(1475),谢公(迁)状元及第,公(宁良,字元善)闻之,以书来贺曰:‘先生与谢君齐名于时,今谢君及第,此亦汇进之兆也。良不佞,敢为先生贺。’”见《双槐岁钞》(北京,中华书局,1999),《瑞梦堂》,卷九,页180。
[5](清)张吉安修、朱文藻等纂:《余杭县志》:“王华,字海日,余姚人,教授余杭十余年,后状元及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寓贤》,卷二十八,页419c。又《道光婺志粹》记云:“华,字德辉,余姚人,仕至吏部尚书,守仁父也……先生微时,为塾师于东阳叶家,有小桃源诗诸作,后以访旧至,为昭仁许氏作《四傅堂记》。”见(清)卢标:《道光婺志粹》(上海,中国书店,1993),《寓贤志》,卷九,页630c。
[6](明)樊维城、胡震亨等纂修:《海盐县图经》:“王守仁幼从海日公授徒资圣寺。”(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方域·寺观》,卷三,页256。阳明于此有佚诗《寓资圣僧房》,见(明)刘应钶修、沈尧中等纂:《嘉兴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艺文·海盐县》,卷二十九,页1959—1960。又(清)吴翯皋等修、程森纂:《德清县志》:“锦香亭,在大麻村向阳里。明王守仁读书处,其父华尝馆于此,后人筑亭其上。”(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杂志·堂宅园亭故址》,卷十三,页811。
[8](明)赵宽:《白驹联句引》,见《半江赵先生文集》,卷十二,页316d—317a。
[9](清)张夏云:“愚按:一斋长子性与王阳明父海日翁同成化辛丑进士,联居京师。阳明年十七入闽,过广信,奉其父命从一斋问学。一斋以心传告之。次子忱官司训,十年不下楼居,盖皆淳质君子也。然罗整庵尝言一斋以作止为道,因取禅家搬柴运水,则其流传之失似亦一斋早示之隙矣!又尝见庄定山寄一斋诗云:‘江门风月诗,连塘水花趣。安得二先生,倾倒鹅湖寺。’又云:‘朱学本不烦,陆学亦非简。先生一笑中,皓月千峰晚。’盖定山与白沙同道,欲通之于一斋也。夫一斋既已作陈之合,安得不开王之先耶!明儒学脉之歧实开于此。”见《雒闽源流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123)(台南,庄严文化,1996),《娄谅》,卷四,页70d—71a。
[10](明)娄性:《皇明政要》(中国野史集成·续编·10)(成都,巴蜀书社,2000),末卷,页878a—878b;(清)黄宗羲:《教谕娄一斋先生谅》记云:“先生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助勿忘为居敬要指。”见《明儒学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崇仁学案二”,卷二,页38。
[11](明)何良俊云:“我朝留心经术者,有杨文懿(守陈)、程篁墩(敏政)、蔡虚斋(清)、章介庵(袞)诸人。”见《四友斋丛说》(北京,中华书局,1997),《经三》,卷三,页24。又杨守陈在当时以《易》学名家,《县志》云:“杨霖,字时望……初霖闻四明杨守陈邃于《易》学,负笈数百里师之。”见(清)江峰青修、顾福仁等纂:《嘉善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宦业》,卷十九,页357c。
[12](明)王懙《吏部侍郎赠礼部尚书谥文懿杨公神道碑铭》云:“大父棲芸先生,潜心理学,远宗杨慈湖(简)、黄东发(震)诸公,卓然为时名儒……至其家庭授受而用以取科第,则专门《易》学。盖公既得之棲芸而遂以传之弟,若子公弟(守随、守阯)三人并举进士。”见(清)黄宗羲编:《明文海》(文渊阁四库全书·1458)(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四百五十,页501b—503c。
[13](明)杨守陈:《杨文懿公文集》(丛书集成续编·186)(台北,新文丰,1989),卷二十一,页238a。
[14](明)杨守陈《国子卢君楷墓表》云:“成化七年(1471),国子监典簿以侵馔钱抵罪事连前祭酒礼部侍郎邢公让,祭酒陈公鉴、司业张公业俱坐除名为民。盖邢尝以馔钱葺监舍,实未始侵入巳,张素不预,陈始至未察也,而三人之素所不悦者,乘此腾谤,连内外匈匈,有司竟文致之,众知其枉而莫能直也。国子生卢君方历事中书,奋欲救之,或曰无益也且取罪奈何?君曰:‘师生犹父子也,父既溺,子可惧陷而不号呼以救之乎?’遂率同监百余人,伏阙上奏,明三人之枉,有司以案成不省也。一时皆高君之义,称叹之无已。”见《杨文懿公文集》,卷二十九,页331a—331b。
[15](明)焦竑:《玉堂丛语》(北京,中华书局,1997),《方正》,卷五,页159。除了守节自持外,杨氏面对政治权威,也是挺然不惧,例如其在主讲经筵时,以《武成篇》为主题,阐扬孟子所云“安其危而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者”之旨,以告诫皇帝。见《杨文懿公文集》,《讲读》,卷三,页73。
[16](明)何乔新:《嘉议大夫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谥文懿杨公守陈墓志铭》,见(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台北,学生书局,1965),《吏部三·侍郎》,卷二十六,页1084d—1085a。
[17]“六元文会”及“七元文会”成立之详情,参见(明)杨守陈:《七元文会诗序》,见《杨文懿公文集》,卷二十五,页283a—284a。
[18](明)杨守阯:《浙元三会录序》,见《碧川文选》(丛书集成续编·186)(台北,新文丰,1989),卷四,页410a—410c。
[19](清)党金衡原本、王恩注重定:《道光东阳县志》(上海,中国书店,1993),《人物志·儒林》,卷十八,页214d—215a。(明)刘宗周《重刊荷亭文集序》云:“所著《荷亭辨论》八卷,盖皆详古文之绪论,质之圣人而不能无疑,因反覆其说,以求当乎本心之所安。至与朱子相异同,亦且十居六七,若先生可为真能疑者矣!……集刻于弘治庚申(1500),盖先生镌以代缮写之劳,就正有道意也。久而被毁,后之信其言者日益众,求其书者日益多,裔孙叔惠氏重镌而行之,走数百里外,问序于予(1631),以予同诵法孔子、宗六经,而不区区拘笺释之言者也。”见《刘宗周全集(三册下)》(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1997),《文编十一·书序》,页710—711。
[20](清)黄宗羲也说:“镜川长于经术,诸经皆有《私抄》,其于先儒之传,唯善是从,附以已见,有不合者,虽大儒之说,不苟徇也。”见(清)朱彝尊:《经义考》(文渊阁四库全书·680)(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二百四十七,页231b—231c。
[21](明)杨守陈:《大学私钞序》,见《杨文懿公文集》,卷二,页37d—38b。
[22]例如姚广孝之事,见(清)张廷玉《明史》:“(姚广孝)晚著《道余录》,颇毁先儒,识者鄙焉。”(北京,中华书局,1995),《列传第三十三》,卷145,页4081。
[23](明)卢格:《大学格致传辩》,见《荷亭辩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101)(台南,庄严文化,1995),卷二,页491b—491d。
[24](明)王守仁:《送绍兴佟太守序》:“成化辛丑,予来京师,居长安西街。”见《王阳明全集》,《续编四》,卷二十九,页1056。
[25](明)姚鸣鸾修、余坤等纂《淳安县志》:“程文楷……壬子(1492),与乡解,上春官不偶,遂讲学京师,从者甚众,与今阳明王先生诸老,上下议论,赓和盈几,为一时缙绅所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文苑》,卷十二,页9a。
[26](明)王守仁:《程守夫墓碑(1524)》,见《王阳明全集》,《外集七》,卷二十五,页943。
[27](清)甘文蔚等修、王元音等纂《昌化县志》:“王轩,入太学为大司成谢方石铎(字鸣治,1435—1510)所敬礼,授松溪训道,投檄不赴。海宁张方洲(宁,字靖之)、同邑胡端敏(世宁,字永清)暨王阳明先生,号天下士,皆与之游,以图书文墨相引重。”(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文苑》,卷十三,页698;又《涌幢小品》记云:“王良臣,钱塘人,名轩,受业姚文敏公(姚夔)之门。经术精专,以贡为松溪教谕,时年五十,无子,弃去不赴,阳明先生为赋当年一诗。”见(明)朱国祯:《涌幢小品》,《肥香》,卷十一,页4410。
[28](明)钱德洪编《年谱·弘治五年》:“归余姚,结诗社龙泉山寺,致仕方伯魏瀚(字孔源)平时以雄才自放,与先生登龙山,对弈联诗,有佳句辄为先生得之,乃谢曰:‘老夫当退数舍。’”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页1224。又余姚张瀚与海盐张宁、嘉兴姚绶、慈溪张琦,称“浙江四才子”。见(明)徐象梅:《进士张廷珍琦》,见《两浙名贤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文苑·明》,卷四十七,页1342b—1342c。
[29](清)徐元梅等修、朱文翰等辑纂《嘉庆山阴县志》:“明宏(弘)治间,白洋朱和妻矢节抚子,设宅延王文成守仁为之师,其子侄簠、簦、萀、节等,俱成名。”(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寺观冢墓》,卷二十四,页964。
[30](明)彭辂《尹蓬头传》:“王文成公守仁礼闱落第,卒业南雍,从尹游,共寝处百余日。尹喜曰:‘汝大聪明,第本贵介,筋骨脆,难学我。我从危苦坚耐入道,世人总不堪也。虽无长生分,汝其以勋业显哉。’文成怅然。”见《冲溪文集》(台南,庄严文化,1997),卷十八,页234d—236b。
[31](明)张萱《西园闻见录》记云:“陈凤梧,字文鸣(号静斋,1475—1541),泰和人,朱希同榜进士,以庶吉士为刑部主事,公尝曰:‘仕优则学必先审刑狱、精律例,方及考古。’一时僚友王守仁、潘某、郑某皆名士也,讲学论文至夜分,当时称‘四翰林’云。”(台北,大中国图书公司,1968),《好学》,卷八,页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