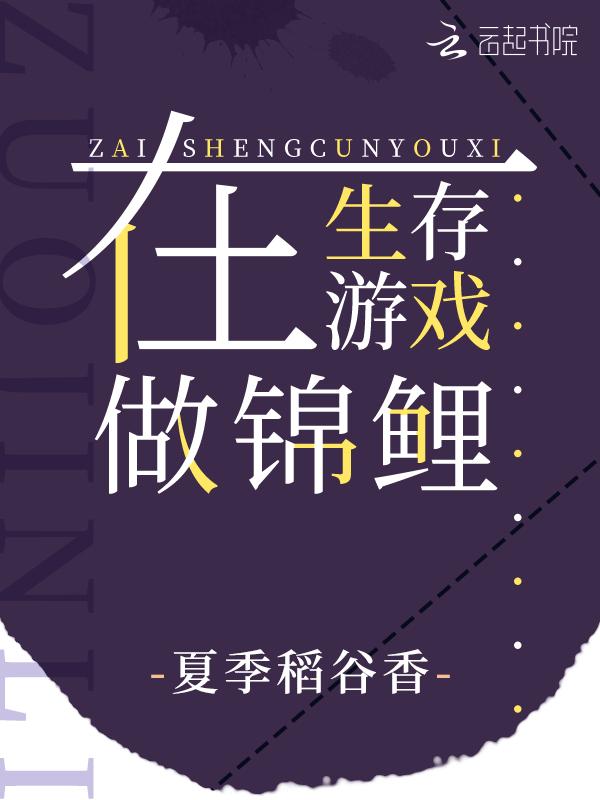奇书网>银河系样子 > 第152章 鬼神台下戏骨成灰(第1页)
第152章 鬼神台下戏骨成灰(第1页)
凌秋辞第一次踏上“鬼神台”的戏台时,槐树叶正簌簌落在她的水袖上。戏台在老城区的深处,朱红的柱子斑驳得露出底下的麻石,台口的“出将”“入相”匾额被雨水浸得发黑,唯有檐角那只缺了喙的铜雀,还在暮色里泛着冷光。
“丫头,这地方邪性得很。”墨先生拄着枣木拐杖,指节敲了敲戏台中央的青石板,“午夜开腔,听戏的可不止是人。”他的白胡子在风里飘着,像戏文里得道的仙翁,只是那双浑浊的眼睛里,藏着化不开的忧色。
凌秋辞没说话,指尖抚过戏台边缘的刻痕。那些深浅不一的凹槽里,还残留着胭脂和油彩的痕迹,是百年间无数戏子留下的印记。她的祖父曾是这“鬼神台”最后的班主,临终前攥着她的手,枯槁的手指在她掌心写“守”字,血珠渗进纹路里,像枚洗不掉的朱砂痣。
三个月前,开发商赵天成带着推土机闯进老城区时,凌秋辞正在后台给祖父的戏服拆线。那件绣着百鸟朝凤的蟒袍,金线己经氧化发黑,她一针一线地拆着,听见外面传来戏台柱子轰然倒塌的声响——那是西侧的“文场”柱,光绪年间的老木料,曾支起过无数出《长生殿》。
“凌小姐,识时务者为俊杰。”赵天成叼着烟,皮鞋碾过地上的碎木屑,“这破戏台子早该拆了,给你三倍补偿,够你在新区买套大平层。”
凌秋辞抱着蟒袍站起身,祖父的头面(戏曲演员的头饰)还在妆奁里闪着微光,点翠的凤钗缺了半只翅膀,是当年他为救一个坠台的武生摔坏的。“这不是钱的事。”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戏还没唱完。”
赵天成嗤笑一声,挥手让工人继续拆。铁铲刚碰到东侧的“武场”柱,突然刮起一阵怪风,卷着槐树叶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推土机的引擎“哐当”一声熄了火,再也打不着。
“邪门!”赵天成的助理啐了口唾沫,“这地方老辈人就说不干净,民国时演过一出《钟馗嫁妹》,台口塌了,压死了七个戏子。”
凌秋辞看着那根纹丝不动的“武场”柱,想起祖父说过的话:“鬼神台的戏,一旦开腔,就得唱完。唱不完的,要么成了台上的魂,要么成了台下的鬼。”
墨先生是在那天傍晚找到她的。老人提着个藤箱,里面装着全套的点翠头面,绿得像淬了毒的翡翠。“你祖父托我把这个给你。”他的拐杖在青石板上敲出笃笃的响,“他知道你会回来。”
凌秋辞的指尖抚过那只缺了翅膀的凤钗,突然想起十二岁那年,祖父在戏台教她唱《霸王别姬》。“虞姬的剑,要藏着七分情,三分悲。”他捏着她的手腕,让她的水袖在胸前划成半圆,“就像这鬼神台,看着是给人唱戏,实则是给天地听的。”
那晚的月光很薄,像层蝉翼贴在戏台顶上。凌秋辞换上祖父留下的戏服,墨先生给她上妆,指尖的老茧擦过她的眉骨,带着熟悉的檀香气息。“秋辞,你可想好了?”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午夜开腔,唱的就不是人间的戏了。”
“我知道。”凌秋辞看着镜中渐渐成型的虞姬,眼角的胭脂像滴未落的血,“祖父当年停在‘垓下歌’,我得替他唱完。”
子时的梆子声刚过,第一缕月光穿过戏台的窗棂,落在青石板上。凌秋辞提着宝剑,踩着锣鼓点踏上戏台,水袖拂过柱子的瞬间,她听见身后传来细碎的响动——不是墨先生的拐杖声,像是无数双鞋在黑暗中移动。
她定了定神,开口唱道:“自从我,随大王,东征西战……”
嗓音刚起,戏台周围的槐树叶突然静了,连风都停了。墨先生坐在台下的第一排,手里的梆子悬在半空,眼睛盯着戏台东侧的阴影——那里站着些模糊的影子,穿着褪色的戏服,有的缺了胳膊,有的少了腿,却都保持着看戏的姿态。
那是“三方为鬼”。凌秋辞在心里默念祖父的话,唱腔愈发沉稳。她看见第二排的空位上,慢慢坐满了穿长衫马褂的人,有的摇着折扇,有的捧着茶碗,指尖的烟火在黑暗中明明灭灭。他们是几十年前的戏迷,当年在台下听戏时突发恶疾,断了气,魂魄却留在了这里。
“八方来听,一方为人。”墨先生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剩下的西方,是神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