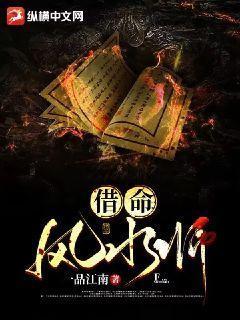奇书网>身向榆关那畔行的身字有什么作用 > 误会的拆解(第5页)
误会的拆解(第5页)
许长昭说这两个字的时候,不是宽恕式的那种“我原谅你”,更像是“我早就理解了”。
“所以后来我转学的时候,”他笑了一下,“才会跟你说那句‘那就恨吧’。”
“那会儿我已经隐约猜到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
“你是那种不敢往外炸的人,”他看着他,“你只会往里藏。”
“我想,既然你迟早会把我埋进记忆里,那我就干脆给你一个比较体面的理由。”
“‘恨’听上去,总比‘我被他保护得很难堪’好一点。”
“起码,你可以用这个词跟自己过得去。”
沈向榆怔了怔。
他一直以为那句“那就恨吧,恨也是一种爱”只是许长昭一时嘴硬。
现在才知道,那里面掺了这么多他没看懂的算计——
算的是他的自尊,他的防御,他那点狼狈的骄傲。
“你就这么确定,我会把你埋了?”沈向榆问。
“我又不傻。”许长昭挑眉,“你那人,从来不敢把怒气朝外甩。”
“你要么忍,要么把人直接划进‘过去式’。”
“那我不如帮你一把。”
“……”
病房里安静了一会儿,只剩输液滴答声在填空。
“那你呢?”沈向榆开口,“这么多年,你有后悔吗?”
“后悔什么?”
“后悔在教务处抢着认那句‘是我给他看题’。”
“……”
许长昭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被胶布贴得乱七八糟的手背,想了几秒。
“后悔过。”他很坦白,“尤其是后来知道被取消保送、记过拦了我不少路的时候。”
“我也有过那么几次,半夜躺床上想——要是当时我没那么冲动,是不是现在另一个人生。”
“可那都只是‘另一种可能’。”
“回头再想,当时的我如果不站出来,”他说,“那我现在大概会更讨厌自己。”
“就像你一样。”
“我们俩都有一个不能接受的‘自己’版本。”
“所以那天教务处门口,我们其实都只是想办法——让自己未来回头看的时候,好受一点。”
“结果就是谁也没顾上对方。”
他抬起眼,看着沈向榆:“从这个角度讲,我不想完全说‘后悔’。”
“我后悔的不是这件事本身。”
“我后悔的是——认完之后,我没有马上把你按在走廊问到底。”
“没有逼你说清楚你脑子里那一半‘凭什么’。”
“这点,是我失手。”
沈向榆听到“失手”两个字的时候,心口突然轻了一点。
一直以来,他都把那天的全部责任往自己身上堆——
觉得是自己懦弱,是自己没问清楚,是自己办完葬礼就逃。
现在第一次,有人把那一天拆开,分给了两个人。
不是为了减轻谁的罪,只是为了把真相摆平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