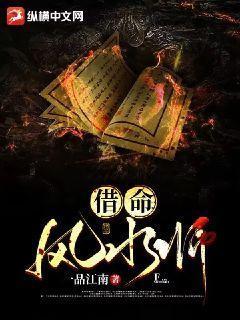奇书网>身向榆关那畔行的身字有什么作用 > 误会的拆解(第6页)
误会的拆解(第6页)
“所以我们现在算什么?”他苦笑了一下,“一人一半?你一半冲动,我一半逃跑?”
“听着挺公平的。”许长昭说,“只是这个公平来得有点晚。”
“……”
“不过总比不来好。”他又补了一句。
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护生探头进来:“沈同学,时间差不多了,你要不要先回去休息一下?”
“好。”
沈向榆应了一声,扶着床沿站起来,脚下还有点虚。护生赶紧走进来扶他。
“我走了。”沈向榆说。
“嗯。”许长昭点点头,“回去多睡会儿。”
“别又在床上分析人性分析到三点。”
“你也是。”
“我分析不了那么多。”许长昭笑,“我现在最高目标就是——明天还能醒过来继续吐槽医院伙食。”
说完这句,他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又叫了一声:“哎,同桌。”
沈向榆停在门口,回头看他。
“我那天是主动抗下来的。”许长昭说,“这点,从来不是你的错。”
“你当时觉得被保护、被推着走,那也不是错。”
“错的是我们俩都没当场把话说完。”
“以后如果还有什么需要两个人扛的事——”他顿了一下,“你别再一个人开葬礼。”
“……”
沈向榆喉结动了动,很轻地应了一声:“好。”
“那你呢?”他反问,“以后有什么想替别人挡的事,先问一句。”
“问一句什么?”
“问一句——‘你愿不愿意让我这么做’。”
许长昭愣了一下,随即弯起眼睛:“行。”
“那我们就这么约了。”
“你做心理咨询师,我配合你当个……勉强合格的病人。”
“……”
沈向榆笑了一下:“那可真是难得。”
门带上,病房里的光被挡在后面。
走廊里又是各种杂音——电视声、轮子声、远处小孩的哭声。
沈向榆扶着冰凉的扶手,一步一步往前走。
刚才那一场长谈,并没有把所有误会一下子洗白。
那些年的坑还在,那场雨、那张处分单也都不会因为几句话就消失。
但至少,他们都承认了——
那不是谁一个人的错。
那是两个人一起,在同一条走廊上做出的一个糙得要命的决定。
当年他们背对着彼此,从各自的方向逃开。
现在,隔着病房的床和输液管,他们终于坐在同一边,把那天翻出来,摊开放在光里看了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