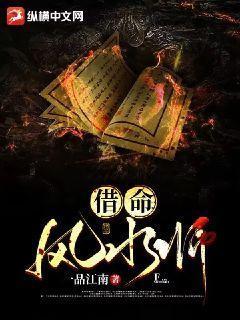奇书网>身向榆关那畔行的身字有什么作用 > 误会的拆解(第3页)
误会的拆解(第3页)
沈向榆没有立刻说话。
那天走出教务处的时候,他记得很清楚——
走廊里有一股粉笔灰混着潮气的味道,窗外雨声乱成一片。
许长昭站在前面,笑得吊儿郎当,说“反正我成绩好一点,被记过也死不了”,又说“你家庭情况跟我不一样,你需要档案好看”。
那一刻,他脑子里同时冒出来两句话:
——谢谢你。
——你凭什么替我决定?
但最后,他一句都没说出口。
他只记得自己那种难以形容的窒息感——胸口像被塞了东西,说什么都不对。
现在再被刀子一样捅回来,他只好慢慢点了点头:“……有。”
“有一半在想‘谢谢你’,另一半在想‘凭什么’。”
“我就知道。”许长昭说,“你那脸,当时一看就不是单纯在感激。”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沈向榆抬眼,“你明明知道会让我有这种感觉。”
“我知道你会觉得被保护。”
许长昭往后靠了靠,视线移到天花板上,“但我也知道——如果我不那么做,回头我会更讨厌自己。”
“你家那边什么气氛,你自己比我清楚。”他慢慢说,“你爸那种人,我在你家见过几次。”
“你要是被记过了,回去要面对什么,我能大概猜到。”
“我那时候脑子特别简单,只想一件事——这件烂事总得有个人来扛。”
“那我成绩比你好一点,老师对我印象也不错,家里条件不算最糟……那我扛。”
“扛完了,将来回头看,我至少不会觉得自己当时缩了。”
他说得很直白,没有半点自怜,甚至还带着一点年轻时候那股横冲直撞的劲儿,只是被病房的光压得柔了一点。
“所以你那天才——”沈向榆压低声音,“一句都没给我留。”
“对。”许长昭点头,“我怕你反应过来,跟我一起认。”
“你要是当时跟我一起说‘是我们俩商量过’,那处分还是会记在你头上。”
“那就完全白扛了。”
“我那会儿就是赌。”他耸耸肩,“赌老师信我这套说辞,赌学校愿意把主要责任扣在我头上,赌你回头不会去翻案。”
“你看,我赌赢了。”
“……”
“只是赌赢了之后,才发现其实挺混账的。”他顿了顿,“我那天确实没给你选择。”
“你可以怪我这点。”
“我那时候也确实在用我自己的方式——保护你。”
他说到“保护”两个字的时候,并不羞涩,也没有自夸,只是把事实平静地摆出来。
沈向榆盯着床单上的折痕,一条一条看过去,指尖缓慢地收紧。
“我当时真的觉得……”他开口,“自己像是被你拖到你身后。”
“老师看你,叫你‘主要责任人’,家长、班主任也都围着你转。”
“所有人都在说‘许长昭这孩子,怎么这么冲动’,说你可惜,说你不该这么做。”
“没有人问我想不想。”
“他们只会顺便看我一眼,说一句‘你要好好感谢他’。”
“那天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他很轻地说,“我觉得自己像贴在你背后的那一块影子。”
“你一认下来,我就被一起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