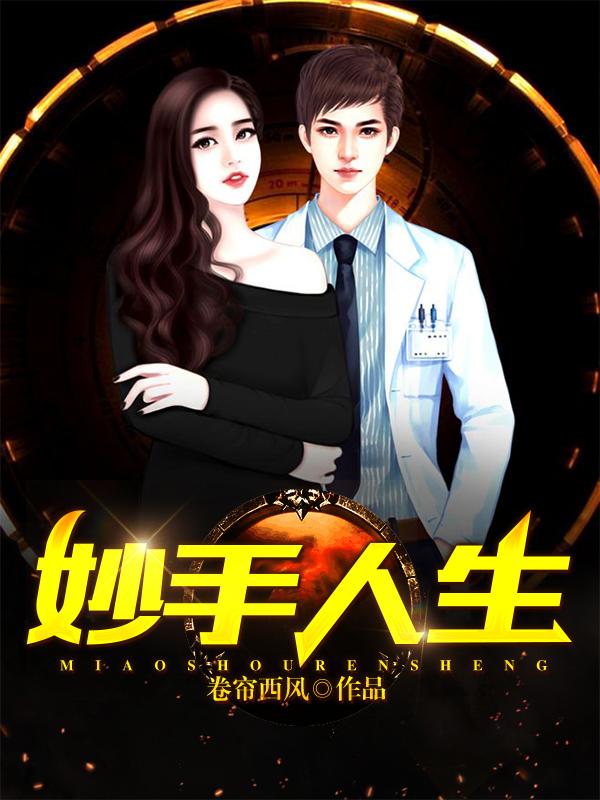奇书网>朱衣加身什么意思 > 第 12 章(第1页)
第 12 章(第1页)
【第十二章】
程瑾轻轻合上最后一册文档,小心地将其归还原处。她站起身,活动了下僵硬的脖颈,内心却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感填满。
这十余日的静默阅读,让她对这个庞大王朝的运作,终于有了具体而微的认知。她开始能从文书的格式、用印、批注的位置和笔迹,快速判断出其流转状态和重要程度。眼前的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一幅幅鲜活的政务图景:中书官员在灯下斟酌字句,门下官员在堂上据理力争,尚书官员在衙署分派任务。
她开始理解条文的重量。一份关于漕粮折价的普通度支奏抄,背后关乎千里之外万千农户的生计;一纸看似例行公事的刺史任命,可能维系着一方边疆的安稳。她隐约感觉到,在这严密的文书流转之下,似乎有无数双无形的手在牵引、在角力,但具体为何,此刻的她尚看不分明。
暮色渐沉,程瑾合上手中最后一份奏抄。她明白了自己日后所言的每一句话,所书的每一个字,都将汇入这浩瀚文海,接受这套精密规则的检验。她走出甲库,暮色已笼罩皇城。
郑明不知何时已站在廊下,似乎正要来找她。
“程补阙,这些时日可有所得?”郑明依旧是那副平淡的语调。
程瑾停下脚步,郑重地向郑明行了一礼:“受益匪浅。如今方知文书之重,政事之实。多谢郑录事指引。”
郑明看着她眼中尚未褪去的专注与明悟,微微颔首,眼中似乎闪过一丝极淡的认可。“明日辰时,至给事中厅外廊署事,学习文书分类与摘要。”
“是。”程瑾应道。
翌日辰时,程瑾准时来到给事中厅外的廊署。还未踏入,便听见里面传来一阵压抑的争执声。
“这份奏疏分明是借陈情之名,行请托之实!”
“可其中引经据典,情词恳切,若是直接驳回……”
程瑾步入其中,只见几名绿袍官员围着一份展开的文书争论不休。郑明见她来了,抬手止住议论,对程瑾微微颔首:“周给事正在等候,随我来。”
给事中厅内,一位年约四十、面容俊朗的官员正在伏案疾书。他身着浅绯色官袍,肩背挺得笔直,紧抿的薄唇和微蹙的眉宇间凝着一股挥之不去的严肃。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双手——指节分明,右手食指与中指第一指节处有着明显的茧痕,一看便知是长年累月执笔批阅文书所致。这便是给事中周琰。
“周给事,”郑明上前禀报:“这位是新任左补阙程瑾,奉侍中之命前来学习文书处置。”
周琰抬起头,那双锐利如鹰的眼眸在程瑾身上停留片刻。他早就听闻过程瑾的名声——昔日的“京城四俊”之一,程侯世子,月前刚因触怒圣颜被罚入宫侍奉,如今竟被破格授予门下省要职。这般起落,着实令人玩味。
“程补阙。”周琰的声音平淡无波,听不出喜怒,“听闻你昔日以诗文闻名京城。”
程瑾躬身行礼:“下官程瑾,见过周给事。往日虚名,不足挂齿。”
“在门下省,诗文作得再好,也比不上把文书看透的本事。”周琰让程瑾走近些,拿起一份刚送到的奏报,神情严肃。
周琰取过一份奏章,径直翻到末尾,指着一条贴在文书空白处的黄纸道:
“在门下省,首要的本事,就是学会看这个——贴黄。”
程瑾凝神看去,只见黄纸上用工楷写着几行小字:
“一、河南道七州水患,饥民约三万。二、请拨赈粮两万石。三、请免今岁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