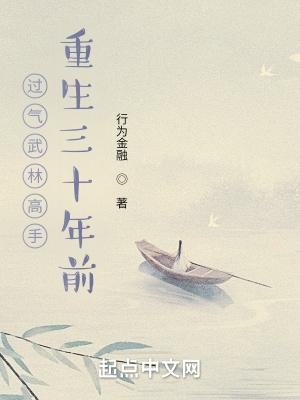奇书网>穆木天的诗集 > 我的诗歌创作之回忆诗集流亡者之歌代序(第2页)
我的诗歌创作之回忆诗集流亡者之歌代序(第2页)
东京,在我进大学的那年夏天,发生了大地震。在十月间,由故乡吉林回到了东京,东京只剩下一片灰烬了。残垣破瓦,触目凄凄。可是,在当时我的眼睛中,反觉得那是千载不遇的美景。就是从那种颓废破烂的遗骸中出去,到了伊东。而从伊东归来后,也是在那种零乱的废墟中,攻读着我的诗歌。我记得那时候,我耽读古尔孟(Re-mydeGourmont),莎曼(Samain),鲁丹巴哈(Rodenbach),万·列尔贝尔克(CharlesVanLerberghe),魏尔林(PaulVerlaine),莫里亚斯(Moreas),梅特林(M。Maeterl-inck),魏尔哈林(Verhaeren),路易(PienreLouys),波多莱尔(Baudelaire)诸家的诗作。我热烈地爱好着那些象征派,颓废派的诗人。当时最不欢喜布尔乔亚的革命诗人雨果(Hugo)的诗歌的。特别地令我喜欢的则是莎曼和鲁丹巴哈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我那种颓废的情绪吧。我寻找着我的表现的形式。在飞鸟山公园里,暮色迷茫之下,俯瞰着王子驿,不由地,我想起来那首诗,一首是:《我愿作一点小小的微光》,一首是《泪滴》。然而,终不能把我的感情尽量地表现出来。
1924年冬,因事,又去回到吉林住了几天。故乡的冬景,特别地,引起我的憧憬。而那年,雪是特别地大。大雪之后,山上,路上,人家的房上,封了冰的松花江上,特别的皑白,令人爱赏,令人凭吊。这种风景,特别地,在江岸上的天主堂里钟声一响时,直是引起人的感慨无量了。在那种氛围气中,我作了《江雪》。翌年春正月,到了北京一次,凤举,启明诸兄把《泪滴》和《我愿作一点小小的微光》两篇,在《语丝》上给发表出来。他们更给我吹进了好多勇气。于是,在我折回了东京之后,诗就陆续不绝地产生出来了。不忍池畔,上野驿前,神田的夜市中,赤门的并木道上,井头公园中,武藏野的道上,都是时时有我的彷徨的脚印。而在那种封建色彩的空气中,我默默地低吟出我那些诗歌。
在细雨中,在薄雾中,在夕暮的钟声中,在暗夜的灯光中,寂寞地,孤独地,吐出来我的悲哀。昼间,则去茶店喝咖啡,吸纸烟。每天,更读二十分钟的诗歌,找一两篇心爱的作品,细细玩赏。在这种印象的,唯美的空气中,我直住到1925年的冬季,而以后我则住不下去了。
为小资产阶级化了的没落地主的我,一边追求印象的唯美的陶醉,而他方,则在心中对于祖国的过去有了深切的怀恋。同伯奇论过“国民文学”,想要复活起来祖国的过去,可是启明一再地予我以打击,于是,在无有同情者援助之条件下,默默地,把自己的主张放弃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绪,则是传统主义的了。这种传统主义的情绪,最初的表现是《江雪》。其后,如《野庙》《北山坡上》《苏武》《薄暮的乡村》《心响》《薄光》等作,都是多少具有这种传统主义的气氛的。而就是在《不要看十字街头象牙的殿堂》那首诗中,也是深深地残留着传统主义的成分的。
东京的生活,实在,令我再忍受不下去了。我,那时,略略地,读着拉佛尔格(JulesLafue)希图得着安慰,得着归宿。可是,怎么样呢?我成为德娄尔莫(JorepheDelorme)一流的人物了。我失眠,我看见什么东西都是黄的。我非常地爱读圣伯符(SainteBeuve)的诗歌。他的《黄光》(IeRayonjaune)影响出来我的《薄光》。那年之末,印象主义被发展到极端,成为了“苍白的钟声”和“朝之埠头”。而同时我的悲哀,我的失眠,以致于使带三分狂气,在《鸡鸣声》那首诗(形式,当然是独清的《从咖啡店出来》那首诗暗示给我的)中,是反映出来我是如何地狂乱了。在《猩红的灰黯里》,我不是既歌唱出来那“吮不尽了,猩红境中,干泪的酒杯,尝不出了,灰黯里,无言的悲哀”了么?《鸡鸣声》之后是再也写不出什么诗来了。东京的生活是叫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到了广州,到了北平,一切都是空虚的。以后,再不能多量地生产了。广州只产生《弦上》等三首。北京只产生了《薄暮小曲》等两首。而其中似相当地有硬作的成分。好像那一个园地已被我耕种完了。不是不可再生产东西,然而不会生产再好的东西了。
以后接着就是数年的沉默,直到重回到吉林之后,知道东北的农村破产,日本帝国的铁蹄是一天比一天逼紧地向我们头上践踏,我是守着沉默的。我自己掘了自己的坟墓了。虽然诗中隐伏着无限的血泪,但是,我只是回顾,没有向前看去,没有想从现实中去求生活。
五
从北平飘泊到墙子河畔,从墙子河畔又回到北平。在那个短的期间所接触的印象中,使我感到有什么危机快临在头上了。1929年夏,回到故乡的新设的大学里教书。那时,我越发地深感到世界变样了。故乡的情形,已不复旧观了。有些地方,似有些进步,而有些地方,确是大可令人担忧的。
吉敦铁路修成了,蜿蜒地,在奔驰着的松花江上,架上了一道大铁桥了。汽车也似乎是多起来了。从得胜门到北山已修上了柏油的马路了。在北山上,已高高地耸起一座自来水塔了。江桥和水塔,在那座古城中,呈出来近代的伟大。听说吉海铁路不久完成。听说那年乡村得庆丰收。冷眼一看,吉林社会似乎是进步了的。然而,过了不久,我又看出来另一方面的现象了。
好些亲友们,在吉敦铁路局里作事,因之,一边为得玩景,一边为得访友,我到了蛟河,去过敦化。我瞻仰了老爷岭的崇山峻岭,我瞻仰了黄松甸上的一望无边满目青葱的黄松树。我看见了奶子山的黑油油的煤块,我看见了长白山的直径有五六尺的木材。东北的宝藏,真是“名不虚传”。“耳闻不如眼见”了。可是在我对着这些宝藏叹美之际,我的朋友们告诉了我吉敦路的各种纠纷,帝国主义者如何地占有了吉长路,吉敦、吉长是如何地成为了南满铁路的培养线,中国的木材业是如何地渐归完全破产,吉敦路的收入如何地连借款利息都不够。我们就不禁浩叹起来了。接着,我们谈到农村都市之各种破产情形。而,那种情形,在我的眼睛里,越发地,暴露出来了。有人从乡下来,告诉我农村大不如昔了。并不是“米珠薪桂”,而是,粮食卖不钱来。丰收确是丰收,可是农村越发地贫穷了。卖地的多了,可是受主没有。钱利高了,可是没有放债的。种地的人家也走不起车了。只是雇工人,还好,每年钱挣得多了。一个雇工人,是比一个小学校教员挣得还多得多。那年冬,因为,日金是一日千里地往上长,好多商店就不得不关门了。
转过年,就是1930年了。1930年,吉林社会里,更越发地呈出紧张的现象。吉海与吉敦的接轨问题,引起社会中的很大的注意。南满铁路屡屡地开会议。帝国主义者,更变本加厉地来干涉压迫我们。东北遍地是日本的药房,当铺,卖的是枪械子弹,是鸦片,吗啡。所以东北在那时是遍地土匪。在那时,打吗啡的,是不可胜计,有的人甚至把骸骨抵押给药房,换得吗啡以陶醉自己。而日本人贩卖吗啡的消息,东北的报上是一向不准登载的。以先,只干涉我们的日报,现在又干涉起我们的学校刊物来了。吉林大学春蕾社几个人所筹划的《鲜民研究专号》,不知道为什么也叫帝国主义知道,于是他们就提出抗议叫我们的教育厅预防地禁止了。满铁,在1930年,因为吉海路的通行,“赤字”一天一天地增加。在1930年的下半年,东北已呈现出来“弓在弦上”的情势,一般人谁都似预感出战乱有一触即发之势了。
而且,在另一方面,奉系军阀的铁蹄更践踏在吉林民众的头上。虽然,大部分人,是敢怒而不敢言,可是,每一个压迫是播了一个种子了。“醉鲜饭店”、“倶乐部”、“大老徐”……在各个的印象上,都令我们感到有白刃对着我们。我们都感到快要亡国了。而“亡省之苦痛”是也令我们忍受不住的,因为太久了。我们想办一所小学校都不可能,而他们呢,则是尽量的刮地皮,养了好些通匪而且公开绑票的保卫团。往事真是不堪回首!想起来是如何地痛心啊。“国语文”都在违禁之例。因为学生看《白屋文话》,一个中学校都被查封了。这一类的事情,真是数不胜数。于是,安分教书的我亦忍不住了。秋天,“永吉影戏院”遭了火,一夕烧死了百数十人。警察消防立视不救。这该是如何地痛心的一件事呀。学校学生叫我作了一副挽联。我挤出来如下的一副东西来:
警察说人头真好看,消防说快救财政厅,一晚间竟牺牲那些人命,处此封建社会,谁说非势所必至?
报纸里无丝毫哀掉,官府里只记过塞责,满城中笑谈着这场惨剧,在彼野蛮人群,原来是理有固然!
这一副挽联是使吉林的好些朋友叫快的。然而,仅仅地叫快,又能怎样呢?那些奉系军阀现在大部分是作了“满洲国”的高官了。
到了冬季,吉林的农村越发地破产了。“九·一八”的前兆越发地显露了。吉林的生活,再忍不下去了。于是,在年末,向着故乡致了永别的敬礼,我一个人就走上了我的长长的旅途了。因为想离开教员生活,转到卖文的生活的方面来,所以就飘泊到南方来了。到了上海,不到数月,就听到“万宝山事件”。不久就是“九·一八”了。
六
虽然处在都市中心,不能亲睹东北的惨状了,但是,或从报纸上,或从朋友的口中,是总得彼方的一点消息的。我心中时时酸痛。乘着我还有声音,叫我时时地唱《流亡者之歌》吧。可是,现在的东北究竟是怎么样了?
1933年11月18日
(原载《现代》第4卷第4期,1934年2月1曰)
[1]法文,此处可译作“克制”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