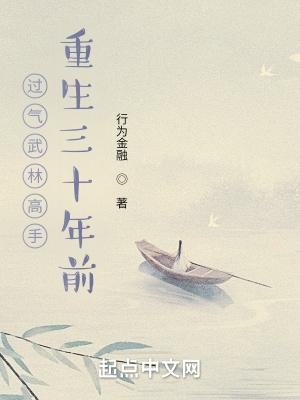奇书网>穆木天的诗集 > 我的诗歌创作之回忆诗集流亡者之歌代序(第1页)
我的诗歌创作之回忆诗集流亡者之歌代序(第1页)
我的诗歌创作之回忆——诗集《流亡者之歌》代序
一
“九·一八”已经过两年多了。我同东北作了最后的诀别,已经快到三年了。而在这同故乡作了诀别的长时间之后,我把我过去的诗作,集拢起来,编成了这部《流亡者之歌》。我,在这时,心里真是有无限的悲哀,无限的酸痛在萦绕着呢。这三两年来,我的故乡的情形,是怎么样了?
倒也从东北来了些朋友,告诉了我一些那边的消息。有的说:“满洲国”的基础已经巩固了,义勇军不久快要被“肃清”了。有的人说:在东北大野中,正流着“铁之洪流”,农村的毁灭已到极点,新的生活在到处展开着,动乱是要一天比一天多,随着压迫苦难之一天一天的增加,而反抗也是一天一天地愈趋猛烈的。虽然说法不同,但我心中总像是有几条利刃在挖扎着似的。有时甚至把我刺激得麻木,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东北的民众,是天天在那里遭屠杀。飞机天天掷炸弹在他们头上,大炮天天向着他们轰击。像“一·二八”那样的大屠杀,在东北是整整地干了两三年了。那么,我的诗人的心又该怎样了?
自从《旅心》之后,外界的各种条件,使我没有唱歌的余裕。但,自从同东北作了永诀之后,唱哀歌以吊故国的情绪是时时地涌上我的心头。也许是因为找不到适当的形式的缘故,也许是东北的现实的样子,变幻得太出人意料的缘故,我时时压住我的悲哀使他不发泄出来。我总觉着“流亡者”是不应当哭丧脸似的。能想办法就想办法,不能也应当有一点stoiquo[1]的精神。何必哀歌地作“亡国之音”呢?因之,把好多诗情压制住了。
然而,在压制之中,情感终会跳溅出来。所以,偶尔,也制作了一两首诗。然而,因为管理加严的缘故,所以最近的这少量生产之中,到比较客观性多了一些。也不像《旅心》时代那样容易地哭丧脸似的了。我总是热望着,像杜甫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似的,把东北这几年来的民间的艰难困苦的情形,在诗里,高唱出来。由现在起自己勉励起来。所以从要离开故乡以至于现在的虽止于十首的诗作,也想集起来问世了。或有人依据着这几篇东西给我一个好的指示。
近三年来作的这几首诗,是反映着我的“流亡者”的心情的,因名之为《去国集》。旧日的《旅心》则仍名之为《旅心集》。同时,把未收入该集中的同时代的诗作也集入其内。《旅心集》虽没有同现在不同的情绪,但是那种地主阶级的没落的悲哀,亦是隐含着亡国之泪。如果用透视的显微镜去看,那里是不是也暗伏着“流亡者”之心情?在那种农村没落之凭吊里,是不是也暗伏着帝国主义经济的压迫呢?虽然是代表着两个时期,有他们的不同点在,但,因为反映着一种有机的持续,而且,都是帝国主义压迫下的血泪的产物,所以,总名之为《流亡者之歌》。
二
虽然在1923年就跃跃欲动地想作诗,而我能多量地产生诗歌,则在1925年。1925年,乃超从京都转学东京,使我在学校里,多了一位作诗的朋友。于是到咖啡店里去的次数似乎比较地多了。关于创作的兴趣也一点一点地浓厚了。《旅心》中的大部分的作品,是1925年作的。
虽然,诗的大部分是1925年写成的,而,其中的诗感则是1924年暑假期间在伊东的那两个月的生活所培养成了的。那两个月的海滨的生活,给了我不少的兴奋和刺激,而那种兴奋和刺激直造成了我的那些诗歌。那一个近于原始的农村,那一道海湾,那些山,那些水,那些人家,而特别地是那一个肥胖的少女,直是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尖锐的刺激,而使我永远地不能忘怀的哟。我追求她,她不理我。以后到了我发现我的旅伴S君和那位少女成为知己,天天出去漫步的时候,我真是忍无可忍了。我没有别的,我只有沉痛地唱吟我的哀歌。那一次失恋,使我认真地感到了自己的没落和身世凄凉了。
本来,我到伊东海岸去避暑,是S君拉我去的。1923和1924年,是我一生最不幸的年头。封建势力极其巧妙地来包围我,节节地向我进攻。我向来所抱的理想幻灭了,感到了人生之无出路。有时,甚至想自杀以解脱自己。S君是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那是我至死都不能否认的哟,叫我到伊东海岸上休息一下,转换转换精神。可是,伊东的数月生活,更是使我苦上加苦,愁上加愁,而至于直感到自己的必然的无出路,决定的没落来了。
S君,薄暮中,总是同那位少女慢慢地散步的。在林中,在其间的道上,在河边,在桥头,在山谷中,在田地里,他们慢慢地走着。那位肥胖的少女是特别地具有着一副清脆的声音。在暮色朦胧中,她是轻快地,断断续续地,唱着她的歌曲。晚风,软软地,不绝如缕地,把她的歌声吹送到各处。她那种歌声,则是我所憧憬的对象,我的心向的所在了。每天晚上,我是一个人独自地追逐着她的歌声。我不愿意离得它太远,也不愿意离得它太近。我更不愿意同他们俩一同散步。我就是愿意一个人不即不离地追逐着她的歌声。有时,就是她没有在唱歌,我也觉得像在什么地方有她的声音在**动着似的。那里寄托着我的悲哀。同时,那种追逐成了我的每日的享乐了。
然而,也终有忍不住的一天的。是什么原因,我记不得了。那天,在夜里,我在楼下温泉里洗了一个澡。时间,大概还不过一二点钟。随后穿上我的那件大学生制服,我就跑出去了,跑到海滨,望着远远的渔火,听着微风吹来的声动,顺着平滑的沙路,顺着太阳要出来的那方向走了下去。爬山越岭,经过了网代到了曾经游过的热海。然而,到了热海,旅途上的疲倦,以及别无它处可去的直感,使我不得不转回头来。于是乘着晚班的火轮船又折回了伊东。到了寓所,房东的老太婆和那位肥胖的小姐以及S诸人告诉我说日间找了我好久,山巅水涯都找遍了,以为我是自杀了。我只是笑了一笑。《我愿……》那首诗,就是那天海滨上所得到的印象。
伊东之两个多月,使我感到没落,感到深的悲哀,使我感受了哀歌的素材。同时,在伊东,我读了诗人维尼(AlfreddeVigny)的诗集。那两月间,好像是决定了我的作诗人的运命了似的。
三
我为什么怀到了很多的理想,为什么感到那么深的悲哀呢?伊东的两月间,只是一个引子,只是使我痛感到我的没落罢了。原因,自然是要从我的全部生活去说明的。我是没落的地主的儿子哟。
在我的祖父的时代,我的家庭是我们的县里的数一数二的人家,良田百顷,还开着好多的店铺,是素以“占山户”自豪的。然而,生意破产了,因之,家也析居开了。据祖母说:“是因为开烧锅烧坏了”。在我的父亲的那一代人,除了我的父亲之外,是没有一个不抽大烟,不赌大钱的。我们这一支,我父亲是一个独生子,破产的时候,尚年幼,幸赖着祖母的经营和亲友的助力,所以还余得几顷祖遗的田产,得以温饱。但是,没落的家庭总是希望中兴的,总是不忘过去的黄金时代的。我是长孙,于是,祖母就把一切的希望放在我的身上了。她老人家常指着我说:“这个孩子天分还不坏,人说我们家里坟上有贵人牵马,主出一个翰林,大概就该是在这个孩子身上了。”接着,她又叹息着说:“就怕他的祖宗无德,他的×伯父中了府案就得了病,死了。”家里请先生叫我读书,我,虽小,也是自命非凡似的。一个人就着塾师读着书。但是,眼睛每天所看见的,就是我们所住的久不修理的破烂烂的大房子,和满园蓬蒿的大院子。我只知道安分读书,就是莫名其妙地知道读书好。可是我是没看到什么有生命的东西。
我的没落的家庭突然间像是起了变化似的。那是在光绪三十二年之后。那是我上学读书的第二年,日俄战争之后,大家都到大连湾去作豆商,于是,我的父亲也被拉着到大连湾去作“老客”去了,日本的资本主义之发达,大连湾之繁荣,也使我们的家庭获得了不少的利益,沾到了不少的光荣。于是,久年闭锁的油房也重开了。院墙也重新修理了。许多的房子也翻新了。好多铺房也租给人住了。昔日荒芜满目的大院子也天天有好多人运粮运草,有好多车辆出入了。家中生活好像是宽裕了好多。而正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入了中学。
由吉林中学转入了南开,那是我的16岁的时候。在南开快卒业时,国文先生叫我升学入文科,而理科先生叫我入理工科。在“五四”的前夜,胡适也曾在南开作过“新国家与新文学”的讲演,《新青年》也在我们的学校内相当地流行,可是文学终未有给我过度的引力。实在,我是把文学看做雕虫小技了。我对于理科是具有相当的才能的,而特别地是对于数学我具有天才。高小的数学,是我在私塾自己悟会的。在南开时,在数学的领域上,我确是出过风头,使同学们为之骇异。在那“五四”的前夜,中国,借着欧战方酣,帝国主义无暇光顾次殖民地,而风起云涌地,发达起了自己的资本主义。于是,产生出来新兴的工业布尔乔亚汜,同封建的集团作起了决死的斗争。在这种新文化的潮流中,大部分头脑好的青年都狂风怒涛般地要投身于工业界里。新的青年,大部分地,不是要作实业家,就是想作工程师。于是,自然地,我也要作这个资产阶级的幻梦了。我就是抱着这种幻梦到了日本。
十个月的准备,容容易易地考入了东京第一高等,我的志望,是不学化学,即学数学。但是,不幸地,我的眼睛使我不能制机械图。这怎么办呢?我的眼睛不许可发展我的天才了!于是,只得改行换业了。学商呢?我当时又憎恶商人,说那是“奸商利徒”。学政治法律呢?我又最憎恶做官。而正在这时,“五四”的文学运动的怒潮袭到我的心头上来了。当时更认识一位名物:田寿昌。那或者给了我一点影响都不定。因之,觉得干文学也是一条出路,虽非己之所长,也就不得不转入这一途了。
当时,对于新的自由诗虽表示拥护,但是,最关心的,则是布尔乔亚的新样式(Genre):小说。记得有一次我发过誓,此生只写小说,不写别的。但终没有写过一篇布尔乔亚的小说。“创造社”成立,我虽被加入为发起人之一,可是,在《季刊》上,只写了一篇散文诗:《复活日》。那是模仿王尔德(OscarWilde)的。1920年遭了父丧,家境渐趋零乱。同时,日本资本主义在欧战后已到熟烂期。在这个时期,我也没有了1918年前后那样的斗争情绪了。于是从阳气变成忧郁的。由冲击的变成回顾的。京都的三年生活,只是看到伽蓝。这时,在我的意识中,布尔乔亚的成分渐渐变为小布尔乔亚的成分了。一方面回顾着崩溃的农村,一方面追求着刹那的官感的享乐,蔷薇美酒的陶醉。于是就到在我久已憧憬着的东京了。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