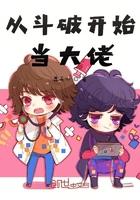奇书网>寂静史 罗伟章 > 一种鸟的名字(第3页)
一种鸟的名字(第3页)
原来,罗眼镜没打算出卖他,那幅画,只不过是他的一幅作品。
但李向志不放心,直到再次更换了墙报,他才去把收音机取回来。
收音机埋在很深的土里,已严重受潮,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杂音很重,别说听敌台。他把耳朵贴在机身上,尽量不漏掉一个字。听出的结果,是那个栏目已经停办了……这都是罗眼镜害的。
次日一早,他把收音机扔进了炉膛。
事过多年,当得知了父亲的真正下落后,他才原谅了那个已经成为大画家的人。
李向志很少谈到他的母亲。他怀念或者说追随一个遥不可及的人,却对含辛茹苦把自己拉扯大的母亲极少提及。在我的印象中,关于母亲的话题,他只主动给我谈起过两次。一次是遮遮掩掩地讲述大胡子怎样半夜三更到他们家,另一次,是我俩在一家咖啡馆里,他说到自己当年为什么从故乡逃跑。
他说兄弟,我实在不忍心看我妈挨斗。响水滩斗人,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其他地方可能扇耳光,跪柴块,或者在毒日头下罚站,响水滩不这样,他们把斗争做成娱乐,事先选几个身强力壮的家伙,在镇子中央的祠堂里(枯水季节,就在河滩上),占据天、地、人、和四方,把我妈这样的牛鬼蛇神夹在中间,你一肩膀撞过去,我一肩膀顶过来,比谁把力道拿捏得最好:既不把人撞倒,又要撞得足够有力,让牛鬼蛇神打出的趔趄,像扭出的舞步一样好看。笑声把响水滩的天都掀翻了。观众笑,甩肩膀的笑,斗争对象也要笑,不笑就证明你不高兴,就一直这么撞下去,直到你笑出来为止。他们的脸的确笑了,但那是假笑;他们的屁眼才是真笑:好些人的屎尿都被撞出来了。当时有人给这种玩法取了个名字,叫“开天劈地”。真是名不虚传。我母亲的屎尿没被撞出来,却从裤管里掉下一团血糊糊的东西。那是卫生巾。那时候不叫卫生巾,叫月经带,一根丝瓜样的长条形布袋里,塞满柴灰,吸女人的血水。
而下一回跟我聊同样的话题,他又不是说的这回事,而是说太饿了。他说响水滩那旮旯,除了鹅卵石,啥都不产,家里来了客人,就捡一盆鹅卵石,用盐炒了,你拿一块,我拿一块,滋滋地嘬那卵石上的盐味儿。后来食盐紧缺,连这道菜也端不出来,就只有大眼瞪小眼。他想活命,只有逃走。
第三次聊,他说的是:兄弟,不跑,我就结不到婆娘。响水滩人人都知道我的底细,谁愿意嫁给我?我想啊,想婆娘啊!当时我以为,只有特务婆娘的儿子才想婆娘,到达钢才明白,罗眼镜也跟我一样想,罗眼镜根正苗红,怎么也想呢?这让我相当吃惊。他想婆娘,就把婆娘画出来,有次我俩偷回一窝白菜,我拿刀正要切,他说别忙!之后提起画笔,画那窝白菜,结果他画出的是一个女人,绿衣绿裤,水灵得要让人晕倒……我感觉响水滩的年轻女人都知道我在想她们,跟她们碰面,我的头抬起来不是,低下去不是,我在她们眼里,五脏去了四脏,只剩下一颗肮脏的心,我能不跑吗?
他说了这么多,但我觉得,在为什么逃跑的问题上,他一直在十分真诚地欺骗自己。
他没骗我,而是骗他自己。
他说出的每一种理由,都可以看成理由,却不是真正的理由。
真正的理由,是他恨自己的母亲。
自从到了成都,他就把母亲搁在疗养院里,如果他是个大忙人,还情有可原,然而事实不是这样。那回他去米亚罗买了几斤天鹅蛋,也是送给小区里的老太婆,让她们尝了鲜,却没给母亲尝尝。最奇怪的是,2008年5月20日,也就是汶川地震一个星期过后,我坐他的车去北川,刚到绵阳,他接到一个电话,是成都某敬老院的马院长打来的。李向志怒气冲冲,说马院长你别管她,她撞死了我不会找你们说半句话!她不会死的,要是她真想死,为什么撞铺盖卷呢?为什么不往墙上撞呢?言毕啪的一声关了手机。之后车开出十几公里远,他依然是满脸怒容。
马院长来电话,自然是说他母亲,他怎么会这样?
有回他突然冒出一句:“我老婆就是被我妈赶走的。”
他似乎是想表明,因为这件事,他才恨母亲。他说他老婆很漂亮,是达钢厂的厂花。这话我并不相信,凭他的地位和长相,不大可能把厂花弄到手,除非达钢厂的男人全都不喜欢漂亮女人;话又说回来,就算老婆真是厂花,婆媳间起一些争执,也是平常不过的事,为这事就离婚,错不在母亲。
我有一种感觉,他对母亲的恨,并非离婚之后才有,而是在响水滩就有了。要不然,从响水滩逃走的那个夜晚,为什么把母亲瞒住?他这一逃,就是十二年,在这长长久久的时日里,他没给过母亲一个消息,开始几年倒说心存畏惧,八年之后,形势变了,他不仅可以给母亲写信,还可以大大方方地去把母亲接走,但他没有写信,更没有及时去接……
这次去红原的路上,我俩夜宿川主寺。成都热得不行,高原上却冷得像冬天,房间里被盖单薄,又没空调,睡到半夜,两人都被冷醒了。他起来看电视,可摆弄来摆弄去,就是打不开,他“噢——嗬嗬——”的喊叫几声,像发火,又像练嗓子。整个一幢宾馆,只住着我们两个客人,他把嗓子喊破,也只有离得很近的星星听见,人听不见。练了嗓子,他又把琴取出来拉。他随身带着小提琴。小提琴也是在达钢厂学的。他的好多本事都是在达钢厂学的。我简直不明白他在那家厂里究竟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学过。他曾经告诉过我,说他是厂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但他拉得实在不怎么样。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解释说,他二十年没摸过琴,两个月前才重新捡起来,手指不听使唤,何况还冻僵了。
言未毕,他接连打了几个喷嚏,之后说:“别感冒了啊。我还是我妈死的时候才感冒过一次。”
我这才知道他母亲已经死了。
“啥时候的事?”
“去年十月份。”
“为啥不通知我?”
“人死如灯灭……”他说,“我哪个也没通知。”
路越来越烂。一条河傍着公路往下走,或者说,公路傍着河流往下走。河流很窄,却咆哮得像条大河,把两边的山壁撞得轰轰隆隆响。山体倒是渐趋生动了,林木深密,岚烟如雾。这么茂密的林子,却看不见一只鸟,也听不见一声鸟鸣。我原以为,鹧鸪山上一定是鹧鸪成群的。
往常,我最害怕李向志话多,有时候,他的话多得如同灾难,天南地北的,张口就来。可今天他没怎么说话,他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唱那首歌,每一句都唱得很动情,仿佛那片刚刚被我们甩在身后的草原,真是他的家。事实上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他在那里买了两匹马,请人养着。给他养马的人,名叫色儿青,是个十九岁的藏族姑娘。他走色儿青家,就像走自己的家。其实,他去年才跟色儿青认识。
去年也是这季节,他带着保姆,去了若尔盖,然后去红原,车在鲜花遍野的草原上飞奔——他开车总是这样,路再烂,也把车开得像逃跑,何况红原作为长江、黄河的发源地,正打造与九寨沟、黄龙溪的旅游共同体,路都是硬化过的——他眼睛的余光瞥见路边有家店子,出售酸奶,便停下来,挽着保姆的手,去了那家店子。守店的就是色儿青。色儿青刚从成都畜牧学校毕业,汉话说得相当地道,把酸奶卖给他们,还请他们进屋坐。他本就是个闲散人,只要高兴,在哪里都能坐上一天半天。于是他就进去了。山区汉人住的那种木屋,并不宽大,倒也整洁。
他虽已六十多岁,却健壮得就像个中年人,因此色儿青叫他叔叔,把他保姆叫姐姐。她以为那保姆是他女儿,不知道是他保姆,还兼做他的情人。离婚在他心里留下了一块活着的伤疤,他始终忘不了老婆,发誓不再娶,却并没停止过找情人。他找的情人都是在校大学生或者研究生,毕业过后,双方关系自动解除。
色儿青这么叫,李向志没纠正,他保姆也没纠正。凡跟他的保姆,基本上都是不大说话的。她们把话留给他说。李向志问色儿青为什么没在成都谋事,却回了山高水高的草原。色儿青说,我就是想在成都找事情呢,可找不到啊,李叔叔你帮帮忙吧。他说没问题啊,然后问她会些什么。“我会医牛医马,”色儿青说,“我学的就是这个。”李向志又说好,没问题。听上去,像成都有成群的牛马等着医治。这时候,色儿青的父亲回来了。她父亲则白是红原县壤口村村长;红原地域广大,却难见人烟,全都是一乡一村,因此也可以说则白是壤口乡乡长。色儿青对父亲说:“阿爸,这是李叔叔,他要在成都给我找事情。”则白咧了嘴笑,满口整齐的白牙,似能嚼碎世界上任何一种骨头。
跟则白握了手,李向志就要走了,可则白不让走。则白摸出手机打电话。十余分钟后,远处驶过来一辆摩托。驾车的是色儿青的母亲尼玛准。尼玛准带着青涩如少女般的微笑,走进屋来,并没给客人打招呼,就洗了手,进了厨房。她勉强能听懂汉话,但不会说。家里,就她跟婆婆不会说汉话。从穿着上看,也只有她跟婆婆才像藏人:则白穿衬衫,色儿青穿T恤,尼玛准和婆婆都是满身藏服。
没过多久,尼玛准端出一大盆手抓牛肉,还有一盘“和尚包子”。
吃了牛肉和包子,天色已晚。则白一家盛情挽留,李向志和他保姆便决定住下来。
公路两边都是草场。南边的草场之外,是连绵的群山。北边的草场没那么宽广,出店百米就被河流分割(一路跟随我们在鹧鸪山穿行的,就是这条河),河的那边也是山,尼姆登山,比鹧鸪山的海拔高了千余米,却照样被针叶林覆盖,望过去,蓊蓊郁郁的,满眼的绿。
李向志问则白:“你家有多少草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