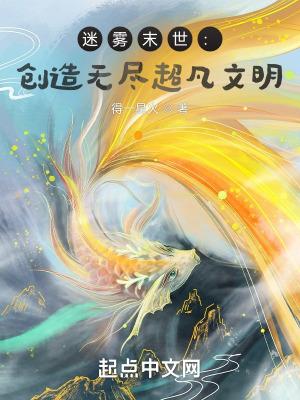奇书网>偏执太子 > 第158章(第1页)
第158章(第1页)
他没有开灯,在完全的黑暗中摸索着走进卧室,然后像一截被砍断的朽木般,“砰”地一声直挺挺倒进床里,一动不动,仿佛魂魄早已离体。
彻底的黑暗放大了所有感官,回忆如同失控的洪流,凶猛地冲击着他早已不堪重负的神经。
耳畔一片尖锐的嗡鸣,他整个人如同被卷入痛苦的漩涡,不断下沉。
极致的疲惫和困意终于将他拖入混沌的睡眠,然而意识却仿佛穿越了时空,清晰地坠入了十多年前那个绝望的夜晚——
他正走在那条熟悉得令人作呕的狭小巷道里。
地面潮湿黏腻,空气中弥漫着垃圾腐烂气味。几只肥硕的老鼠窸窣着从脚边窜过。
这是金海赌场背后一条无人问津的肮脏通道,是他偷偷去见宋清年唯一的路径。
他屏住呼吸,凭借记忆巧妙地避开所有巡逻的守卫,最终抵达那片尚未改造的老式楼区。
这里破败、拥挤,是金海用来豢养“物品”的囚笼。
他心跳如擂鼓,在寂静的夜里发出巨大的声响,几乎要撞破胸膛。
他小心翼翼地摸到那扇门前,极轻地敲了敲——这是他们约定的暗号。这个时间,通常只有清年一个人在。
门很快被拉开一条缝隙。
一股廉价的、试图掩盖什么的香皂气味混杂着另一种难以言喻的腥膻味扑面而来。
宋清年就站在门后,那张在现实中早已模糊的脸,此刻在梦中清晰得令人心碎。
他眼神闪烁,带着显而易见的局促和惊慌,眼眶通红,飞快地侧身半掩着门,声音低哑:“阿辞…你、你等我一下,我收拾一下东西……”
当戴辞终于踏进那个狭小逼仄的房间时,一切都明白了——所谓的“客人”刚离开不久。
宋清年身上那些刺眼的痕迹,那些青紫的掐痕、暧昧的红印,如同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他的视网膜上,疼得他几乎瞬间窒息。
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然后残忍地拧绞,痛彻心扉。
宋清年看着他瞬间苍白的脸色和剧烈颤抖的瞳孔,最后一丝强撑的伪装彻底崩塌。
他猛地扑进戴辞怀里,身体冷得像冰,声音破碎得不成样子,带着彻底的绝望和自我厌弃:
“阿辞……我好脏……我太脏了……”
“我好脏……”
这三个字像淬了毒的匕首,将戴辞的心脏捅得千疮百孔。
他用尽全身力气回抱住怀里不断颤抖的身体,泪水瞬间决堤,滚烫地砸在宋清年单薄的肩颈上。
巨大的无力和愤怒几乎要将他撕裂,他恨自己的无能,恨这吃人的世道!
“清年…我们走……”他声音嘶哑,像过去无数次那样重复着那个虚幻的承诺,“我带你离开这里,我们逃得远远的,再也不回来了……好不好?”
“我们离开这里好不好?”
可是这句话问出口,带来的只有更深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