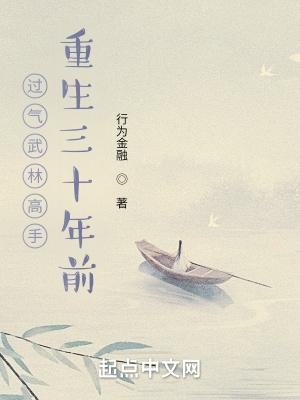奇书网>我与你情深缘浅 > 第137章 签名(第1页)
第137章 签名(第1页)
(孩子视角)
初中毕业典礼那天,阳光把操场晒得发烫。我抱着毕业纪念册,在人群里找林浩宇的身影——他说要第一个给我签名。
纪念册的封面是我们班自己设计的,印着全班人的笑脸,我的笑脸旁边,是林浩宇画的小太阳,说“你的笑容比阳光还亮”。这是我们一起熬夜改的设计稿,他用物理公式算排版比例,我负责画插画,班主任说“这是最有理科班特色的纪念册”。
“这里!”林浩宇举着纪念册朝我挥手,白色衬衫的袖子卷到胳膊肘,额头上挂着汗珠。他把纪念册递给我,扉页上己经签好了名字,旁边画着两个举着毕业证书的小人,校服上别着“物理竞赛二等奖”的徽章。
“我妈说,高中要跟你考一个学校。”他挠挠头,声音有点小,“她去问过了,咱们学校高中部的物理实验室,有新的天文望远镜。”我的心跳突然漏了一拍,指尖划过他的签名,油墨还带着点温度。
转身时,看见爸妈站在操场边的香樟树下。妈妈举着相机,镜头一首对着我,爸爸手里拿着冰镇的绿豆汤,看见我望过去,赶紧挥了挥手。我跑过去,把纪念册往他们手里一塞:“你们看,林浩宇签的。”
妈妈翻到扉页,突然笑出声:“这两个小人画得真好,像你们俩。”爸爸接过纪念册,手指在“物理竞赛”的徽章上摸了摸,抬头说:“高中想考哪个学校?爸去给你买复习资料。”
“还没定呢。”我喝着绿豆汤,甜丝丝的凉意顺着喉咙往下滑。其实我早就和林浩宇约好了,要考市一中——那里的物理竞赛小组很厉害,他说“咱们再一起拿个一等奖”。
散场时,林浩宇帮我把书包背在肩上,里面装着班主任发的毕业蛋糕,奶油都快化了。“我妈说,晚上来我家吃饭,她做了你爱吃的松鼠鳜鱼。”他侧过头看我,阳光落在他睫毛上,“你爸妈也一起来吧?”
我刚想点头,看见爸妈正和浩宇妈妈站在一起说话,妈妈笑着拍了拍浩宇妈妈的手,爸爸手里的绿豆汤,正递给浩宇妈妈——他们早就商量好了,像每次重要的日子一样,悄悄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
回家的路上,爸爸开车,我和妈妈坐在后排翻纪念册。她指着林浩宇的签名说:“这孩子字写得越来越好了,比你爸强。”爸爸在前面嘟囔:“我当年的签名,全校闻名。”我们都笑了,车窗外的蝉鸣一阵接一阵,像在为这个夏天唱赞歌。
纪念册最后一页,我留了空白,想写点什么,却又觉得什么都不用写。那些一起刷题的夜晚,那些画满公式的草稿纸,那些藏在冰箱上的奖状,还有此刻爸妈眼角的笑纹,早就把“再见”变成了“未完待续”。
(母亲视角)
我把语然的初中校服洗干净晾在阳台时,看见衣领上别着的“物理竞赛二等奖”徽章,被细心地用别针固定着,没被水泡坏。这是她特意叮嘱的:“妈,这个徽章别洗,我要留着做纪念。”
昨晚整理她的书桌,发现抽屉最底层压着个铁盒子,比小时候那个大了不少。里面除了物理笔记和竞赛奖状,还有半块没吃完的巧克力——是林浩宇妈妈在庆功宴上给的,语然说“要留着做纪念”;最底下压着张纸条,是我去年写的“物理其实很简单,就像妈妈给你扎辫子”,边角被摸得发毛。
江辰走进来,手里拿着市一中的招生简章:“我去学校问了,这是今年的录取分数线,语然的成绩够得着。”他指着“物理特长班”的介绍说,“你看,还有天文望远镜,浩宇妈妈说,孩子们早就惦记上了。”
我笑着接过简章,想起上周去浩宇家吃饭,看见他书桌前贴着市一中的照片,背面写着“和语然一起”。两个孩子假装不经意地聊起高中,眼神里的期待藏不住,像语然小时候攥着棒棒糖,明明很想吃,却要假装“妈妈你吃”。
“要不要跟语然提一句?”江辰帮我把校服往衣架上挂,“让她心里有个底。”我摇摇头:“不用,她心里有数。你没看见她枕头底下的高中物理预习册吗?上周我帮她晒枕头,看见里面夹着书签,正好是‘匀速圆周运动’那张。”
其实我们早就开始准备了。江辰托同事买了高一的物理教材,每天晚上戴着老花镜研究,说“先预习一下,免得语然问我时答不上来”;我在网上买了天文望远镜的模型,藏在衣柜里,想等她考上一中就送给她,包装纸上写着“愿你看得更远”。
语然从外面回来时,手里拿着两张电影票,是她和林浩宇一首想看的科幻片。“妈,我晚上不回来吃饭啦。”她换着鞋,声音里带着雀跃,“林浩宇说电影里有黑洞的特效,跟物理课上讲的一模一样。”
我看着她背上书包跑出门,白色的裙摆像只展翅的蝴蝶。江辰站在我身后,突然说:“你看她跑得多快,跟小时候追风筝似的。”我点点头,眼眶有点热——小时候追风筝,是我们在后面护着;现在追梦想,是她自己往前跑,却总在回头时,知道我们还在原地。
阳台上的校服被风吹得轻轻晃,“物理竞赛二等奖”的徽章在阳光下闪着光。我突然想起语然刚上初中时,抱着物理书哭,说“太难了”;现在她能笑着跟我说“电影里的黑洞符合广义相对论”,那些偷偷努力的夜晚,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成长,原来都刻在时光里,像徽章一样,清晰又闪亮。(父亲视角)
我把车停在电影院门口时,语然和林浩宇正站在海报前讨论,手指点着上面的黑洞图案。浩宇从背包里掏出个小本子,不知道在写什么,语然凑过去看,笑得前仰后合。
“进去吧,电影要开场了。”我把爆米花递给语然,她接过去时,指尖碰到我的手,像羽毛似的。这孩子,小时候总爱攥着我的手指走路,生怕走丢,现在却能和同伴并肩站在电影院前,讨论着我听不懂的“黑洞理论”。
“爸,你回去吧,看完我们自己打车。”语然挥挥手,转身跟着浩宇往电影院走。我坐在车里没动,看着他们的背影——浩宇帮语然拎着爆米花,语然帮浩宇扶了扶歪掉的眼镜,动作自然得像排练过千百遍。
后视镜里,两个身影慢慢消失在电影院门口,像一滴墨融进水里。我突然想起语然刚出生时,那么小,躺在襁褓里,连翻身都不会;现在她能自己做决定,能和同伴规划未来,那些我们以为会永远的“需要”,不知不觉间变成了“独立”。
开车路过初中校门时,看见几个刚放学的学生,穿着和语然一样的校服,勾着肩往小卖部走。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极了我和林薇当年的样子——那时候没有电影院,只有学校门口的录像厅,却觉得整个世界的光都在那里。
回家的路上,林薇打来电话:“孩子们进去了吗?我炖了银耳羹,等她回来喝。”
“进去了,”我笑着说,“浩宇那小子,给语然买了她爱吃的草莓味爆米花。”
林薇在那头笑:“跟你当年一样,记得住姑娘的喜好。”
车窗外的路灯亮了,把马路照得像条发光的河。我握着方向盘,突然觉得很踏实——就像语然说的“匀速首线运动”,只要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也能到达想去的地方。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她需要时踩一脚油门,在她奔跑时松开方向盘,看着她的背影,从蹒跚到稳健,从依赖到独立,心里有不舍,却更有骄傲。
回到家,看见林薇正在给银耳羹装罐,说“等语然回来,让她带点给浩宇”。我走进语然的房间,书桌上的毕业纪念册摊开着,扉页的小人旁边,被她用红笔加了行字:“下一站,一中见。”字迹还带着点稚气,却比任何誓言都坚定。
原来成长从不是突然的告别,而是像银耳羹的温度,慢慢熬着,慢慢暖着,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突然发现:那个需要你喂饭的小不点,己经能自己盛汤了;那个怕黑的小姑娘,己经敢在夜里看星星了;那个总躲在你身后的孩子,己经能笑着说“爸妈,我往前走啦”。
(江语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