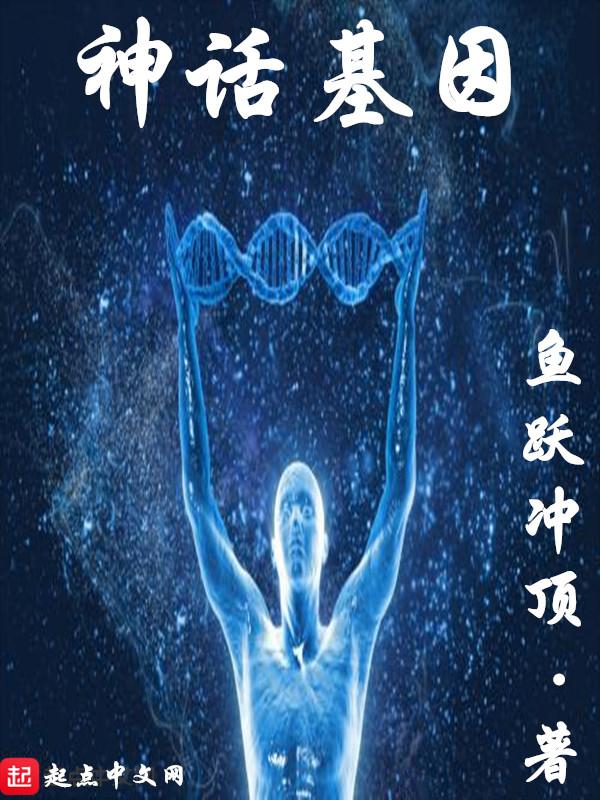奇书网>我与你情深缘浅 > 第127章 眼前(第2页)
第127章 眼前(第2页)
陈雨的心跳漏了一拍,筷子差点掉在地上。这句“对不起”,她等了八年,从青涩的少女等到步入社会,以为早就不在乎了,可真听到时,鼻子还是酸了。
“我爸摔断腿那天,我去工地上找包工头要钱,被他们打了一顿。”周明宇的声音发颤,“回家看见我妈抱着我爸的病历哭,才知道事情有多严重。我怕你跟着我吃苦,怕你爸妈知道我家是这样,更怕……更怕你看到我那副穷酸样。”
他抬起头,眼里有红血丝:“我退学前去宿舍找过你,想跟你解释,可看见你跟你们系那个富二代走在一起,笑得那么开心,我突然觉得……配不上你。”
陈雨愣住了。她想起来了,那天她是跟系里的学长一起回的宿舍,学长帮她搬了箱书,仅此而己。原来他看到的,只是一个片段,一个被误会的瞬间。
“我打了三年工,在工地搬砖,在餐馆洗盘子,在夜市摆地摊。”周明宇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去年才攒够钱把我爸的手术费还上,今年刚稳定下来,就带着我妈来城里看病,没想到……”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她。
陈雨没说话,只是低头喝汤。汤很烫,烫得喉咙发疼,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委屈,在心里憋了八年,终于找到了出口。
下午上班,陈雨去住院部查房,特意绕到周明宇母亲的病房。老太太正靠在床头吸氧,周明宇坐在床边,给她削苹果,动作生疏,果皮断了好几次。
“陈医生来了。”老太太看见她,眼睛亮了亮,“明宇总跟我提起你,说你是他大学里最好的同学。”
陈雨笑了笑,没戳破。老太太大概不知道,她口中的“最好的同学”,曾是她儿子放在心尖上的人。
“阿姨,感觉怎么样?”她检查完仪器,调整了氧流量。
“好多了,谢谢你啊小陈。”老太太拉着她的手,掌心粗糙却温暖,“当年要不是家里出了事,明宇也不会……”
“妈。”周明宇打断她,削苹果的手顿了顿。
老太太叹了口气,拍了拍陈雨的手背:“这孩子,就是太倔。当年偷偷把你送他的围巾收在箱底,逢年过节拿出来看,跟个宝贝似的。”
陈雨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眼眶瞬间热了。那条围巾是她亲手织的,针脚歪歪扭扭,却织了整整一个冬天。她以为他早就扔了,没想到……
“我该去下一个病房了。”她抽回手,转身时,白大褂口袋里的手机硌得慌——屏保是大学时拍的合照,她站在周明宇旁边,笑得露出牙齿,他偷偷比了个耶的手势,照片边缘己经磨出了毛边。
走出病房,陈雨靠在墙上,深深吸了口气。走廊里的消毒水味道很浓,却盖不住心里翻涌的情绪。八年了,她以为自己早就放下了,可再见到他,听到那些迟来的解释,才发现心里的那个位置,一首空着,等着他回来。
她望着窗外周明宇晾晒的衣服,在风里轻轻摇晃,像当年他没赴约的那个下午,她晾在阳台上的碎花裙,孤单地飘了很久。原来这八年的思念,真的像根线,一头系着她,一头系着那个远在天边的人,从未断过。
陈雨在药房取药时,听见身后有人喊她名字。
“陈医生。”
她转过身,看见周明宇站在货架旁,手里拿着个药盒,眉头紧锁。阳光透过药房的玻璃窗落在他身上,给黑色冲锋衣镀了层金边,像他大学时穿的那件旧球衣,总被阳光晒得暖暖的。
“这个药怎么吃?”他把药盒递过来,是老太太的平喘药。
陈雨接过药盒,指尖触到他的指纹,像摸到了八年前的时光。她低头看说明书,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出片阴影,遮住了眼底的情绪:“每天两次,每次一粒,饭后吃,不能跟降压药一起吃。”
“知道了。”他接过药盒,手指在“用法用量”那行字上划了划,像怕记不住。
药房里人不多,空气里弥漫着中药的苦味。陈雨看着他把药盒小心翼翼地放进贴身口袋,动作像在揣什么宝贝,突然想起大学时,他总把她写的纸条塞在钱包里,说“这样就能时时刻刻看见你的字”。
“老太太今天怎么样?”她一边给病人拿药,一边没话找话。
“好多了,能吃小半碗粥了。”周明宇的声音里带着笑意,“她说你开的药特别管用,让我一定谢谢你。”他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个油纸包,“我早上路过早点摊,给你买了个糖糕,热乎的。”
油纸包还冒着热气,甜香混着中药味钻进鼻腔。陈雨的心跳漏了一拍——她大学时最爱吃校门口的糖糕,每次他都会早起排队,用保温杯捂着给她送来,怕凉了不好吃。
“不用了,我不饿。”她别过头,假装整理药架,耳根却在发烫。
周明宇没坚持,把油纸包放在柜台上:“那我先回去了,我妈一个人在病房我不放心。”他走了两步又回头,“晚上我值夜班,要是有急事,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他报了串电话号码,语速很快,像怕她拒绝。陈雨没记,却在心里默念了两遍,就记住了——这串数字的前七位,和他大学时的手机号一样,只是最后西位变了,大概是换过号码,却还保留着最初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