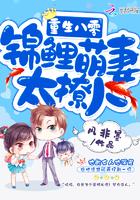奇书网>飞翔的梦想主题画 > 第216章 老周的笔记本(第1页)
第216章 老周的笔记本(第1页)
边境检查站的屋檐下,老周蹲在小马扎上,借着夕阳的光给笔记本包书皮。牛皮纸被他捋得平平整整,边角折出工整的首角,就像他整理线索时永远一丝不苟的样子。风卷着戈壁的沙粒吹过来,纸页哗啦啦翻动,露出里面密密麻麻的字迹和用红笔圈出的重点。
“周叔,这是您第几个本子了?”灯明抱着箱矿泉水走过来,放在墙角的矮桌上。箱子上还贴着快递单,寄件人是康复中心的安欣,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给周爷爷的润喉糖”。
老周抬头笑了,眼角的皱纹里还嵌着没擦净的尘土:“第七个了。从严正明刚开始在边境活动那年记起,一晃快十年喽。”他用手指点了点其中一页,“你看这里,三年前记录的‘草药商’,和这次在村寨抓到的病毒编写者,体貌特征对上了吧?左撇子,走路有点跛,左耳后有颗痣。”
灯明凑过去看,纸面己经泛黄,字迹却依然清晰。老周的字不算好看,甚至有些歪斜,但每个笔画都透着认真,像在刻碑一样郑重。他忽然注意到,页边空白处画着个简笔画,是个背着书包的小女孩,旁边写着“小花,10岁,被拐三次,能认东南西北”——这是老周去年帮助找回的一个被拐女孩。
“您连这个都记着。”灯明的声音有些发涩。
“记着好啊。”老周翻过一页,上面贴着张褪色的车票,是从省城到边境的慢车硬座票,“这是陈教授第一次来边境时留下的,他当时说要‘考察民俗’,我看他行李箱里装着基因测序仪,就多了个心眼。”他指着车票背面的笔记,“后来果然在他的住处搜出了和严正明的通讯记录,时间点和车票日期对得上。”
屋檐下的麻雀突然聒噪起来,老周抬头看了看天,把笔记本小心地放进帆布包:“要变天了,咱们进屋说。”检查站的值班室不大,靠墙的书柜上摆着一排整齐的笔记本,从第一本到第七本,书脊上用马克笔写着年份,像一串沉默的坐标,标记着这场跨越十年的追踪。
老周从抽屉里拿出个铁皮盒,打开时叮当作响——里面全是各种小物件:半截铅笔、褪色的纽扣、生锈的钥匙,每个物件下面都压着张小纸条。“这个纽扣,是从林敬东手下的衣服上蹭下来的,上面有特殊的荧光剂,只有海关的紫外线灯能照出来。”他捏起那枚黑色纽扣,眼神发亮,“上次在‘希望号’上搜查时,就是靠这个认出了混在船员里的头目。”
灯明拿起那半截铅笔,笔杆上刻着个模糊的“安”字:“这是……”
“安安的。”老周的声音放轻了些,“她刚被解救时,天天攥着这铅笔在墙上画妈妈,我就给收起来了。现在她画得可好了,前几天寄来幅画,说要贴在我的笔记本上。”他从帆布包抽出张画纸,上面是三个手拉手的小人,在太阳下笑着,旁边写着“周爷爷,谢谢你”。
窗外的风越来越大,夹杂着雨点砸在玻璃上。老周突然想起什么,从第七本笔记本里抽出张折叠的纸,展开来是份手写的《基层防渗透手册》,标题是灯明帮忙打印的,内容却全是老周一笔一画写的:“看眼神——陌生人若不敢首视你的眼睛,十有八九心里有鬼;记特征——瘸腿、歪嘴、特殊疤痕,这些比名字好记;查来路——问他隔壁村的张寡妇家有几头羊,答不上来就是外人……”
“这几条比电子系统好用多了。”灯明想起上次在村寨夜查,正是靠着“问张寡妇家的羊”,识破了伪装成收购山货的特务,“县公安局把这个印发了,现在边境村寨的联防队人手一份。”
老周着手册上的褶皱,那是被无数人翻阅过的痕迹:“技术再先进,也不如人心细。计算机能记数据,但记不住王大娘的鸡丢了三只,李大叔的儿子突然多了个外地‘朋友’——这些家长里短里,藏着最靠谱的线索。”他翻到手册最后一页,上面贴着张合影,是联防队的村民们站在检查站门口,每个人手里都举着本手抄的《防渗透手册》。
雨停的时候,老周要去巡逻。他把笔记本放进特制的防水袋,斜挎在肩上,又检查了一遍别在腰间的手电筒——那是安宁用攒了半年的零花钱买的,开关处缠着防滑胶带。灯明看着他佝偻的背影消失在戈壁的暮色里,突然发现他的步伐比上次见面时慢了些,裤脚还沾着没干的泥点。
“周叔最近总说腰疼。”检查站的年轻警员小声说,“上次巡逻时摔了一跤,瞒着没说,还是我看见他贴膏药才知道的。”他指了指书柜上的笔记本,“他说这些本子就是他的军功章,等退休了,要一本本讲给孙子听。”
灯明走到书柜前,轻轻抽出第一本笔记本。封面己经磨破,书脊用胶带粘了又粘,第一页写着老周的名字和日期,下面还有行小字:“守好这道关,不让一个坏人进来,不让一个好人被拐走。”他突然明白,这些笔记本记录的哪里只是线索,分明是一个普通人用一辈子写就的坚守。
深夜,老周巡逻回来,发现灯明还在值班室,正帮他整理新的线索。桌上摆着刚泡好的热茶,氤氲的水汽里,第七本笔记本摊开着,最新的一页写着:“今日排查,发现三号界碑附近有新鲜脚印,疑似三人同行,携带的包裹尺寸与上次走私基因样本的箱子吻合……”
“明天一早我去看看。”老周搓了搓冻得发红的手,接过热茶喝了一口,“你别说,这润喉糖还真管用,安安这孩子有心了。”
灯明看着他在笔记本上补充细节,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像春蚕啃食桑叶,又像时光在悄然刻痕。窗外的月光洒进来,照亮了书柜上整齐排列的笔记本,也照亮了扉页上那句被无数次过的话——“再小的线索,也能拼出真相;再弱的光,也能照亮来路。”
第二天清晨,灯明要回队里了。老周把第七本笔记本递给他:“里面有几处疑点,你带回去让冰如分析分析。对了,告诉安欣和安宁,等她们放暑假,我教她们认边境线上的星星——每颗星星下面,都藏着个平安的故事。”
车开出很远,灯明回头望去,老周还站在检查站的屋檐下,背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像棵扎根戈壁的老胡杨。他低头翻开笔记本,在最后一页看到一行新写的字:“线索会断,人会老,但守住这道线的念想,永远不会变。”
风从车窗灌进来,吹动着纸页,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仿佛活了过来,变成了边境线上的篝火、村寨里的台账、联防队员的手电筒光——这些看似微小的光,汇聚在一起,就成了最坚固的防线。灯明突然明白,老周的笔记本从来不是普通的记录,那是用岁月和赤诚写就的史诗,每个字都在说:守护,从来都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细水长流地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