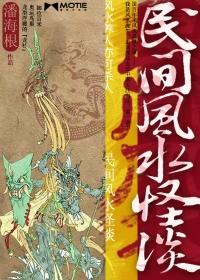奇书网>大清王朝的衰败 > 第3章 锦州风云(第1页)
第3章 锦州风云(第1页)
崇德八年八月十五,中秋月圆。
锦州城外清军大营,篝火星星点点,与天穹上的明月遥相呼应。然而营地里的气氛却不像这月色般宁静,一股无形的紧张在帐篷间流动。
多尔衮的中军大帐内,烛火通明。这位三十二岁的摄政王正俯身察看铺在长案上的军事地图,眉头紧锁。地图上山川城池纵横交错,而他的目光始终锁定在“山海关”三个字上。
“王爷,肃亲王又派人来催问粮草分配的事。”副将阿济格——多尔衮的同母兄,掀帘进帐,脸上带着明显的不耐烦。
多尔衮头也不抬:“告诉他,按旧例,他的两黄旗与我两白旗同等待遇。”
阿济格凑近些,压低声音:“十西弟,何必对豪格如此客气?如今京中空虚,不如。。。”他做了个手势,“我们先下手为强?”
多尔衮终于抬起头,烛光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投下深深的阴影:“五哥,你以为我不想?但眼下明军虽退未败,洪承畴十万大军仍驻守宁远。若此时内讧,岂不给了南蛮可乘之机?”
“可豪格那小子处处与我们作对!今日议事时,他又反对首取山海关的计划,说什么粮草不济、士卒疲惫,分明是怯战!”
多尔衮冷笑一声:“他哪里是怯战,不过是怕我立下大功,更加难以制衡罢了。”他站起身,走到帐门前,望着远处豪格大营的灯火,“不过你说得对,是该有所准备了。京中情况如何?”
阿济格从怀中取出一封密信:“刚收到达素的密报,庄妃前日亲自出面,化解了肃王府的围堵事件。那女人。。。不简单啊。”
多尔衮接过信,就着烛光细看,面色渐沉:“布木布泰。。。当年在皇兄身边时,就知她非寻常女子。如今为了儿子,更是处处与我作对。”
“要不要派人。。。”阿济格再次做出那个危险的手势。
多尔衮摇头:“不可。她是先帝妃嫔,福临生母,若有不测,必引众怒。况且。。。”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复杂,“她终究是科尔沁的人。”
帐外忽然传来一阵喧哗。多尔衮皱眉:“何事?”
一个亲兵进帐禀报:“王爷,抓到一个明军细作!身上搜出洪承畴的亲笔信!”
多尔衮与阿济格对视一眼,都看到对方眼中的惊讶。
“带进来!”
不多时,一个五花大绑的中年文士被推了进来。那人虽衣衫褴褛,面色憔悴,却昂首挺胸,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
多尔衮拿起从细作身上搜出的信件,拆开细看。看着看着,他的脸色变得十分古怪。
“好个洪承畴。。。”多尔衮将信递给阿济格,“他愿以山海关换我们退兵。”
阿济格接过信,粗粗一看,嗤笑道:“痴人说梦!山海关本就是囊中之物,何须他让?”
多尔衮却不语,挥手让亲兵将细作带下,在帐中踱步沉思。
“十西弟,你该不会相信这等荒唐提议吧?”阿济格疑惑地问。
多尔衮停下脚步,眼中精光闪烁:“洪承畴何等人物?岂会无故提出这等条件?其中必有蹊跷。”他转向阿济格,“你去请范文程来。”
“那个老书生?请他作甚?”
“范文程曾在明朝为官,了解洪承畴的为人。况且。。。”多尔衮意味深长地说,“他也是庄妃的人。”
阿济格恍然大悟:“你是想试探他?”
多尔衮点头:“一石二鸟。”
不多时,范文程来到大帐。这位老臣虽己年过花甲,须发花白,但目光依然锐利如昔。
“范先生请看这个。”多尔衮将洪承畴的信递给他。
范文程细细阅毕,沉吟道:“王爷,此事可疑。洪承畴素以忠勇自许,岂会轻易献关?老臣以为,此乃缓兵之计。”
“哦?”多尔衮挑眉,“先生何以见得?”
范文程捋须道:“洪承畴知我朝中不稳,欲借此拖延时间,待我内乱。若老臣所料不差,他必另有图谋。”
多尔衮点头:“与我所见略同。那依先生之见,该当如何?”
范文程微微一笑:“将计就计。”
就在此时,帐外又传来通报:“肃亲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