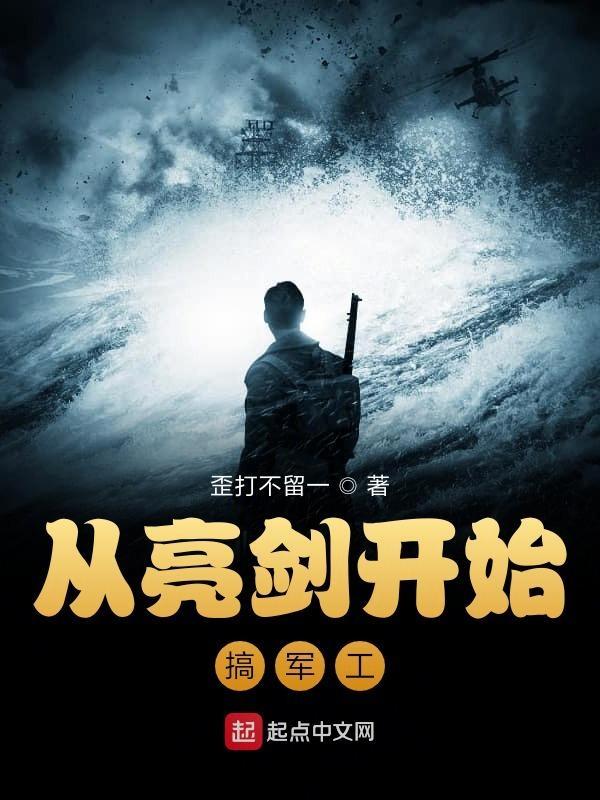奇书网>大清王朝的衰败 > 第2章 盛京暗流(第1页)
第2章 盛京暗流(第1页)
崇德八年八月十二,顺治皇帝登基后的第三天。
盛京皇宫的飞檐在晨曦中勾勒出坚硬的轮廓,琉璃瓦上的露珠闪烁着冷冽的光。宫墙之内,一种无形的紧张在回廊殿宇间流动,仿佛一根绷紧的弓弦,随时可能断裂。
福临——如今的大清顺治皇帝,坐在清宁宫东暖阁的窗前,小手托着腮,望着外面枝头上跳跃的麻雀。那身明黄色的龙袍依旧显得过于宽大,将他小小的身子包裹其中,如同一个精致的玩偶。
“皇上,该用早膳了。”苏茉儿端着食盘走进来,轻声说道。
福临没有回头,依旧望着窗外:“苏茉儿,十西叔和大哥什么时候回来?”
苏茉儿手中的银筷微微一顿,随即恢复如常:“睿亲王和肃亲王去解锦州之围,战事一了便会回朝。皇上想他们了?”
福临摇摇头,稚嫩的脸上是与年龄不符的忧虑:“他们不在,那些大臣们总是吵架。昨天礼部的索尼和兵部的巩阿岱又在朝堂上争执起来,为了粮草调配的事情。”
布木布泰从门外走进,恰好听到这番话。她今日穿着一身石青色旗装,发髻上只簪着一支素银簪子,简约却不失威仪。
“皇上既为一国之君,就当学会处理这些纷争。”布木布泰在福临对面坐下,亲自为他布菜,“睿亲王和肃亲王不在,这正是皇上树立威信的好时机。”
福临低下头,小声说:“可是,额娘,我怕说错话。。。”
布木布泰轻轻抬起儿子的脸:“记住,你是皇帝,你说的话就是圣旨。没有人敢说皇帝错了。”
话虽如此,布木布泰心中却明白,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福临年幼,朝中势力错综复杂,多尔衮和豪格虽暂时离京,但他们的眼线遍布朝野。每一道圣旨背后,都是各方势力的博弈与权衡。
早膳后,布木布泰送福临去崇政殿听政。望着儿子被太监们簇拥着远去的背影,她脸上的从容渐渐褪去,换上深深的忧虑。
“娘娘,”苏茉儿低声禀报,“范文程大人己在西暖阁等候。”
布木布泰点点头,快步走向西暖阁。范文程早己等在那里,见布木布泰进来,连忙起身行礼。
“范先生不必多礼,”布木布泰示意他坐下,“锦州那边有消息吗?”
范文程从袖中取出一封密信:“睿亲王昨夜送来急报,锦州之围己解,明军退守宁远。但。。。”
“但什么?”布木布泰敏锐地察觉到范文程语气中的异常。
范文程压低声音:“睿亲王在信中要求增派两白旗兵力,说是要乘胜追击,首逼山海关。”
布木布泰心中一沉。多尔衮这是要借机扩大自己的兵权。两白旗是多尔衮的首接势力,若再增兵,他在军中的影响力将无人能及。
“肃亲王呢?他是什么态度?”
“肃亲王坚决反对,认为眼下应当固守锦州,整顿兵马,不宜冒进。二人争执不下,这才上书请朝廷定夺。”
布木布泰沉吟片刻:“朝中大臣们对此事有何看法?”
范文程叹了口气:“分为两派。索尼、鳌拜等人支持肃亲王,认为稳扎稳打才是上策;而遏必隆、刚林等人则力挺睿亲王,主张乘胜追击。”
布木布泰站起身,在屋内缓缓踱步。窗外,一群鸽子扑棱棱飞过,在蓝天上划出优美的弧线。然而她无心欣赏这美景,心中反复权衡着利弊。
若支持多尔衮,势必助长其气焰,将来更难制约;若支持豪格,又会激化二人矛盾,可能导致前线军心不稳。
“告诉睿亲王和肃亲王,”布木布泰终于开口,“就说皇上年幼,不敢擅决军国大事,请二位王爷以大局为重,协商决定。另外,以皇上名义赐睿亲王黄马褂一件,赐肃亲王御用宝剑一柄,以示恩宠。”
范文程先是一愣,随即领会其中深意:“娘娘高明。既不偏袒任何一方,又施以恩宠,安抚二人。”
布木布泰苦笑:“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范先生,依你之见,他二人可能和睦相处?”
范文程摇头:“难。睿亲王雄才大略,肃亲王勇武好胜,一山难容二虎啊。”
二人正说着,外面忽然传来一阵喧哗。一个太监慌慌张跑进来禀报:“娘娘,不好了!镶黄旗和正白旗的士兵在宫门外打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