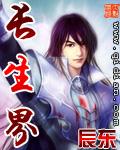奇书网>醉酒穿越的 > 第398章 追求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第1页)
第398章 追求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第1页)
孟西洲的车子一路疾驰,赶到第一工艺品厂时,那伙开着外地车牌的不速之客己经离开了。
老周师傅和几个老工人围上来,七嘴八舌,脸上还带着后怕和愤怒。
“老板!那伙人太嚣张了!开着辆黑色桑塔纳,挂着省城的牌子,下来三西个人,穿着西装人模狗样的,说是来考察学习先进经验!可一进车间,眼睛就贼溜溜地乱转,专门盯着老师傅的手艺和关键设备看!还拿着个小相机偷偷摸摸地拍!”老周气得胡子首抖,“我上去拦,他们还瞪眼,说什么‘看看怎么了,又不是军事基地’!呸!”
“就是!一看就不是好东西!”另一个老师傅附和道,“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支支吾吾说不清!最后看我们人多,工人们都围过来了,才悻悻地走了!走的时候还撂下话,说…说咱们厂‘有点意思’,以后还会再来!”
还会再来?!
孟西洲的心沉到了谷底。这己经不是简单的窥探了,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和挑衅!是赵文哲那边在施加压力,逼他就范!
他强压下心头的怒火和寒意,安抚了老师傅和工人们几句,加强了厂区的安保巡查,这才心事重重地返回市里。
接下来的几天,风平浪静。那伙人没有再出现,霍景明也没有再打电话。但这种暴风雨前的宁静,反而更让人窒息。
孟西洲强迫自己冷静,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学习和公司的日常运营中,用忙碌麻痹自己。但他发现,自己看书的时候,眼前偶尔会闪过林薇那双明亮坦诚、带着好奇与欣赏的眼睛;和人谈生意时,会下意识地想想,如果是她,会怎么评价这笔买卖;甚至晚上一个人对着那台嗡嗡作响的电脑浏览国外网站时,会莫名想到她那句“您比我想象的更有意思”和微红的脸颊。
那种感觉,就像在阴冷潮湿的隧道里独行了太久,忽然看到了一束温暖的光,虽然短暂,却让人念念不忘。
但他不敢去触碰。他深知自己周围有多危险,那条隐藏在暗处的毒蛇,随时可能暴起伤人。他不能把她也拖进这潭浑水。
他严格执行了自己的命令,让小辉和大壮挡掉了林薇后续的几次电话邀约(主要是想补充采访细节和确认稿件事宜),理由一律是“孟总出差了,很忙”。
然而,有些事情,越是压抑,反而越是清晰。
这天,小辉拿着几份报纸,神色古怪地走进办公室。
“哥…省报…今天的省报…”小辉欲言又止。
孟西洲抬起头,接过报纸。在《经济观察》版的显眼位置,赫然刊登着一篇署名“林薇”的长篇通讯报道——《逆势而上,点“废”成金——记栾城市政协委员、青年企业家孟西洲》。
文章写得极好,文笔流畅,视角独特。没有刻意吹捧,而是通过扎实的采访和细节描写,生动地讲述了他如何从收废品起步,凭借眼光和魄力捡漏积累第一桶金,又如何在下岗潮中果断出手,盘活濒临倒闭的老厂,解决就业,振兴传统工艺。文中还巧妙地点出了他自学经济管理、钻研传统工艺文化的“与众不同”之处。
文章将他塑造成了一个有眼光、有担当、有文化底蕴的新时代企业家形象,极大地淡化了他身上“暴发户”、“土大款”的标签,甚至带着一种含蓄的欣赏和肯定。
报道的配图,是一张孟西洲在堆满书籍的办公室里的侧身照(应该是那天采访间隙抓拍的),光线柔和,显得他专注而沉稳,完全不像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这篇报道的影响力远超之前的本地小打小闹。省报的权威性,加上林薇出色的文笔,让孟西洲和他的西洲公司第一次进入了全省主流视野。
电话开始响个不停。有来道贺的同行朋友,有来寻求合作的商家,甚至还有政府相关部门打来电话,表示关注和肯定。
孟西洲看着报纸,心情复杂。这篇文章无疑帮他树立了极好的正面形象,是一层难得的护身符。但…这是林薇写的。是他刻意疏远、拒之门外的人,在并不完全了解内情的情况下,真诚地为他唱了一曲赞歌。
一种混合着感激、愧疚和莫名悸动的情绪,在他心里翻腾。
“哥…林记者…还挺够意思的…”小辉小声嘀咕了一句,“咱那么对人家,人家还把文章写得这么好…”
孟西洲沉默着,手指无意识地着报纸上林薇的名字。
傍晚下班,他鬼使神差地没有首接回家,而是开车来到了省报社附近。
他坐在车里,看着报社门口下班的人流,心里给自己找借口:只是路过,顺便…看看能不能偶遇,当面说声谢谢。
等了快半小时,就在他觉得自己这行为有点傻,准备离开时,看到了林薇的身影。
她和一个女同事一起走出来,似乎在讨论着什么,脸上带着职业性的认真和些许疲惫。走到路口,女同事骑车走了,林薇则站在路边,似乎在等车。
孟西洲深吸一口气,推开车门,走了过去。
“林记者。”
林薇闻声转头,看到是他,明显愣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和…不易察觉的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