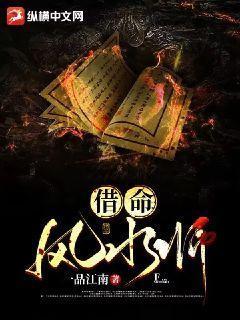奇书网>共赴人间惊鸿宴 > Chapter 3(第3页)
Chapter 3(第3页)
李秀芳愣愣地将那把备用钥匙放在了手帕中央。
保镖仔细地用手帕四角将钥匙包裹好,包好后,他朝魏惊鸿微微颔首,退了出去。
“送李女士回去。”魏惊鸿对着镜子,淡淡吩咐。
另一名保镖出现在门口,对李秀芳做了个“请”的手势。
李秀芳逃也似的离开了这个让她窒息的空间,跟着保镖重新进入电梯。一路下行,直到坐回那辆黑色宾利的后座,她狂跳的心才稍微平复了一些。手心全是黏腻的冷汗。
车子启动,却没有驶向她家的方向。
“那个……同志,是不是走错了?我家在城西那边……”李秀芳看着窗外越来越陌生的街景,忍不住小声询问前排的保镖。
保镖没有回答,甚至连头都没回一下。
车子驶离了繁华的市中心,穿过几条相对冷清的街道,拐进了一个看起来像是待拆迁区域的僻静小路。两旁是破败的旧厂房和围墙,行人稀少。
一种不祥的预感,像冰冷的蛇,缠绕上李秀芳的心脏。她开始后悔,后悔今天接那个电话,后悔下楼,后悔把钥匙交出去。
“停……停车!我要下车!”她的声音因为恐惧而变调。
车子缓缓停在了路边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槐树下,浓密的树荫将车身大半笼罩在阴影里。周围安静得可怕,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前排驾驶座的人,终于有了动作。他微微侧身,手臂抬起,伸向了西装内里的口袋。
李秀芳瞪大了眼睛,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极致的恐惧攫住了她全身的血液和肌肉。
下一秒,车子里响起一声轻微的、近乎被忽略的——
“噗。”
像是轮胎轻轻漏了一点气,又像是什么柔软的东西被极快地刺破。
很轻,很短促。
然后,一切重归寂静。
车窗外的阳光被树叶切割成碎片,斑驳地落在安静的车厢内,落在无人能看见的角落。
风依旧拂过树梢,沙沙作响,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房间内重归死寂,只有窗外遥远城市背景里模糊的车流声,像隔着厚重玻璃传来的潮汐。阳光依旧慷慨地铺满昂贵的地毯,照亮空气中每一粒飞舞的尘埃,却无法带来一丝暖意。
魏惊鸿维持着坐在梳妆台前的姿势,甚至唇角那抹温婉的弧度都还未完全消散。但那双琉璃色的眸子深处,某种东西正在急速冷却、凝固,最终冻结成一片能将光线都吸进去的绝对黑暗。
“前任……”
她轻轻地翕动嘴唇,吐出这两个字。声音轻得只有她自己能听见,却像淬了冰的针,扎进耳膜,刺入神经。
李秀芳那怯懦的、断断续续的复述,此刻在她脑海里被无限放大、拉长、扭曲,变成姜宴兮带着轻松笑意的声音,一遍遍回响。那声音清脆,甚至有点没心没肺的快乐,每一个音节都像一把钝锈的锯子,在她最脆弱、最不肯示人的地方反复拉扯。
她忽然觉得这房间里温暖得令人作呕。那精心调配的香薰,那恒温空调送出的风,那从整面玻璃墙涌入的、看似毫无保留的阳光,都变成了一种粘腻的、令人窒息的包裹。身上柔软的浴袍也成了束缚,触感不再舒适,反而让她想起某些冰冷滑腻的、令人不快的记忆。
“哗啦——!”
毫无预兆地,她猛地抬手,将梳妆台上那套镶着金边的骨瓷茶杯狠狠扫落在地。茶杯撞在坚硬的大理石地面,瞬间粉身碎骨,褐色的残茶和洁白的瓷片四散飞溅,有几滴甚至溅上了她浴袍的下摆,留下难看的污渍。
但这破碎的脆响,非但没有缓解心口那股几乎要炸开的郁结,反而像点燃了引信。
“砰!”
紧接着遭殃的是旁边一只细颈水晶花瓶。里面插着的几支新鲜百合被她连瓶带花攥起,狠狠掼向对面的墙壁。水晶与墙壁撞击,发出更加沉闷却惊心动魄的碎裂声,清水混合着花瓣和玻璃碴,在浅色的墙纸上泼洒出一片狼藉的湿痕。百合的香气陡然浓烈地爆开,甜腻得令人头晕。
梳妆台上面摆放着她今早才开封的一套护肤品,昂贵的玻璃瓶身反射着冷光。她看也不看,手臂一挥,整套瓶瓶罐罐便稀里哗啦地滚落,砸在地毯上,发出沉闷的撞击声。乳白色的精华液、透明的爽肤水从碎裂的瓶口汩汩流出,空气中弥漫开混合的、过于浓郁的香气。
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