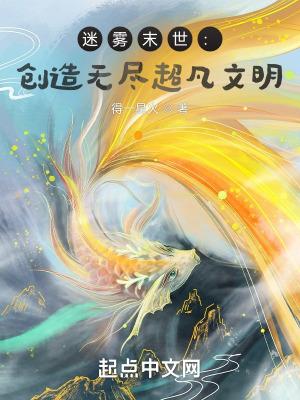奇书网>银河系样子 > 第391章 雾染青阶(第1页)
第391章 雾染青阶(第1页)
林砚第一次见到那株玉兰时,是在惊蛰刚过的清晨。
她抱着半旧的画板站在巷口,露水打湿了帆布鞋的边缘。青石板路上浮着层薄薄的雾,像被揉碎的月光,漫过斑驳的墙根。巷子深处忽然传来吱呀的开门声,紧接着是金属碰撞的轻响,有人在搬弄竹制的躺椅。
“新来的?”苍老的声音穿过雾气,带着草木晒过太阳的暖干气。
林砚转过头,看见墙根下坐着位白发老人,手里正用棉布擦拭一支黄铜烟斗。老人身后的院墙上爬满了常春藤,几片新抽的嫩叶怯生生地探出来,沾着晶莹的水珠。而更醒目的,是院墙里斜伸出来的玉兰枝,光秃秃的枝桠上顶着个的花苞,像被冻住的月光。
“嗯,租了32号的房子。”林砚把画板往怀里紧了紧,指尖触到帆布上未干的颜料,是昨夜调的灰蓝色。
老人点点头,烟斗在掌心转了个圈:“这株玉兰有年头了,等开了花,整条巷子都是香的。”他抬眼看向林砚,目光落在她画板边缘露出的半张素描上,“画得不错。”
林砚的耳尖微微发烫。那是她昨天路过江边时画的芦苇,风把苇穗吹得歪歪斜斜,像一群站不稳的醉汉。她没接话,只是顺着老人的目光看向那株玉兰,花苞的尖端泛着极淡的青,像被谁不小心抹了笔水彩。
接下来的日子,林砚总在清晨或傍晚遇见老人。有时他坐在竹椅上晒太阳,手里翻着泛黄的线装书;有时他蹲在玉兰树下,用小铲子给花根周围的泥土松土。林砚渐渐知道他姓陈,以前是中学的美术老师,老伴走后就一首一个人住。
“年轻时总觉得要画出惊世骇俗的东西,才算没白活。”一次傍晚,陈老先生看着林砚画板上的玉兰草稿,忽然开口,“后来才明白,能把寻常日子里的光画出来,就己经很不容易了。”
林砚握着铅笔的手顿了顿。画板上的玉兰花苞又鼓胀了些,她仔细勾勒着花苞边缘的绒毛,笔尖在纸上簌簌作响。她想起上周画展上评委的话,“你的画技巧很成熟,但缺了点东西”,至于缺了什么,评委没说,只是摇着头在评分表上打了个及格分。
那天晚上,林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翻遍了所有画稿。从静物到人像,从城市街景到远山湖泊,每张画都像隔着层磨砂玻璃,看得见轮廓,却触不到温度。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发呆,镜中人眼下有淡淡的青黑,眼神里的疲惫像化不开的墨。
凌晨三点,窗外下起了小雨。林砚披上外套走到巷口,雨丝斜斜地织着,把玉兰枝打湿成深褐色。陈老先生的竹椅还放在原地,椅背上搭着件深蓝色的旧毛衣,被雨水洇出深色的痕迹。
她走过去把毛衣收进怀里,布料粗糙却带着阳光的味道。转身时,忽然看见院墙里的玉兰花苞裂了道缝,露出里面极淡的白,像雪落在了绸缎上。
第二天清晨,雨停了。林砚推开窗,一股清冽的香气涌了进来,带着雨后泥土的。她跑到巷子里,看见那株玉兰开了第一朵花,花瓣像被月光熨过,在晨风中轻轻颤动。
陈老先生己经坐在竹椅上了,手里捧着个白瓷茶杯,雾气袅袅地升起,模糊了他眼角的皱纹。“我说过吧,很香。”
林砚没说话,只是拿出画板,飞快地调了支奶白色。笔尖落在纸上时,她忽然想起小时候在外婆家,也是这样的清晨,外婆会摘下带着露水的栀子花,插在玻璃瓶里放在她的书桌上。阳光穿过花瓣,能看见里面细细的纹路,像藏着无数个细小的太阳。
画到一半,手机响了,是画廊的电话,说她上次送展的画被一位先生看中,想预约一幅定制的风景。林砚握着手机,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混着玉兰的香气,在空气里轻轻漾开。
接下来的几周,林砚开始为那幅定制画忙碌。她去了好几次江边,看芦苇在风中摇晃的姿态,看夕阳把江水染成金红色,看渔船归航时掀起的涟漪。每次回到巷口,都能看见陈老先生在玉兰树下,有时修剪枝叶,有时只是坐着,像一尊安静的石像。
“画得怎么样了?”一次,陈老先生忽然问。
林砚把画稿递给他,上面是夕阳下的江面,波光粼粼,芦苇的影子被拉得很长。陈老先生眯起眼睛看了许久,指着画面左下角:“这里少了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