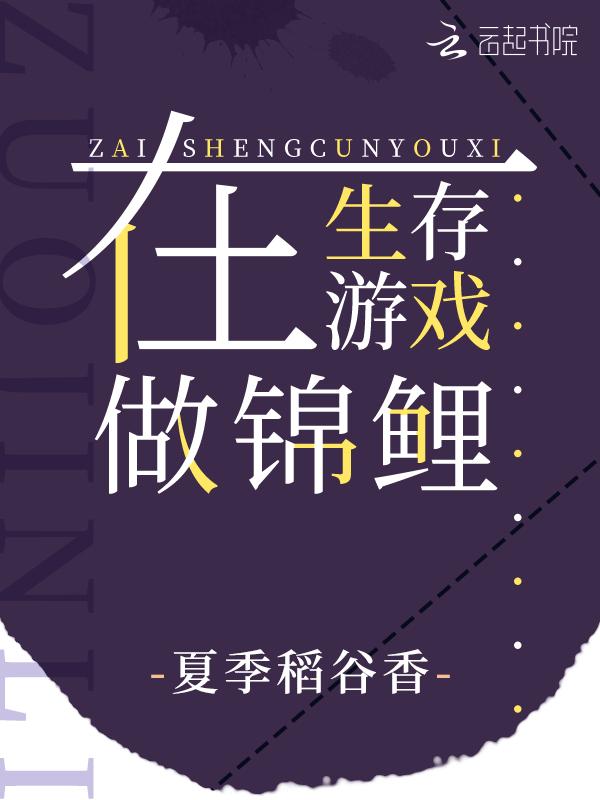奇书网>黄河儿女演员表 > 第139章 为拒婚顶撞母命母女生隙心难平上(第2页)
第139章 为拒婚顶撞母命母女生隙心难平上(第2页)
玉玲跟过来,小声说:“姐,妈哭了。”
玉娥的手顿了顿。
“我看见她在屋里抹眼泪。”玉玲挨着姐姐蹲下,“姐,你真不嫁那个赵同志吗?他上次来,还给我带了水果糖。”
玉娥转头看着妹妹,十三岁的女孩,眼里己经有了超出年龄的懂事。她伸手理了理妹妹的刘海:“玉玲,如果有一天,有个人给你糖吃,对你很好,可你跟他说话的时候,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个人,你会嫁给他吗?”
玉玲茫然地摇摇头:“那……那另一个人是谁?”
玉娥没有回答。她低下头,继续刷洗木板。水面倒映出她的脸,二十一岁的年纪,眼角己经有了细纹,那是长期熬夜磨豆腐留下的痕迹。
她想起秦远山。那个在牛棚里还坚持教孩子们认字的知青,那个说“豆腐里有人生至理”的书生,那个在黄河边递给她一块干净手帕的年轻人。
三年了。她只知道他被送去西北劳教,音信全无。也许早就……不,不会的。
可是就算他回来了,又能怎样呢?他是城里人,是知识分子,就算落难了,也跟自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母亲说得对,她和赵国栋才是实实在在的搭配——一个做豆腐的个体户,一个供销社的职工,门当户对。
“姐,”玉玲忽然说,“你要是不想嫁,就不嫁。等我长大了,我养你。”
玉娥“扑哧”一声笑了,笑着笑着,眼角就湿了。她把妹妹搂进怀里:“傻丫头,姐不用你养。姐能养活自己,也能养活这个家。”
前院传来母亲的声音:“玉娥,豆浆糊锅了!”
玉娥慌忙起身跑进厨房。果然,灶上的豆浆己经溢了出来,流得灶台到处都是。她赶紧把锅端下来,看着那一锅快要煮废的豆浆,忽然觉得这就像自己的人生——火候掌握不好,就容易糊锅。
王秀英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女儿手忙脚乱地收拾。她的气己经消了大半,剩下的只有心疼。
“下午还要给供销社送二十斤豆腐干吧?”她问,语气己经缓和下来。
“嗯。”玉娥头也不抬地擦灶台。
“那赶紧点卤吧,别耽误了。”王秀英走过来,接过她手里的抹布,“我来收拾,你做正事。”
玉娥怔怔地看着母亲。王秀英不看她,自顾自地擦着灶台,动作麻利:“看什么看?你是我女儿,我还能真不管你?”
那一瞬间,玉娥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她转过身去取卤水,背对着母亲说:“妈,对不起,让您丢人了。”
王秀英的动作停了一下,又继续擦:“丢什么人?我王秀英的女儿,有自己的主意,不丢人。”
她顿了顿,声音低下去:“妈只是怕……怕你将来后悔。”
玉娥舀起一勺卤水,在豆浆锅里轻轻划着圈。乳白色的豆浆渐渐凝结,一朵朵豆花浮起来,像是云,又像是命运莫测的形状。
“妈,我不后悔。”她看着锅里的变化,声音很轻,但很坚定,“就算将来真的一个人过,我也不后悔今天的选择。”
王秀英没有再说话。厨房里只有豆浆凝结的细微声响,和灶膛里柴火偶尔的噼啪声。
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母女俩身上。那些聘礼还在堂屋里静静放着,红灯牌收音机沉默着,红纸包着的礼金沉默着,两匹的确良布在光线下泛着生硬的光泽。
但在这个飘满豆香的厨房里,某种更坚韧的东西正在生长。它不像爱情那样炽热,不像婚姻那样庄严,它只是一个女儿和一个母亲,在世事艰难中,终于开始尝试着去理解彼此的选择。
豆浆渐渐凝固成豆腐脑。玉娥拿起瓢,开始一瓢一瓢舀进铺着纱布的模具里。她的动作沉稳有力,每一次舀起、倾倒,都带着一种决绝的美感。
王秀英擦完了灶台,就站在旁边看着。她忽然想起女儿小时候,第一次学点卤的样子——小手抖得厉害,卤水洒得到处都是。而现在,女儿的手稳如磐石。
“少舀点,压出来的豆腐才瓷实。”她忍不住出声提醒。
“知道。”玉娥应着,手上的动作更加精准。
母女俩再没有说话,但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己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就像点卤——多一分则老,少一分则嫩,要在恰到好处的时刻停手。
玉娥压好最后一板豆腐,抬起头,发现母亲正看着她,眼神复杂。
“妈,”她说,“这些聘礼,明天我亲自给赵家送回去。”
王秀英长叹一声,终究是点了头。
院墙外,不知谁家的收音机正在播放歌曲:“世上的路啊,弯弯曲曲长;人生的酒啊,甜酸苦辣都要尝……”
歌声飘进小院,飘进这个满是豆香的厨房。玉娥听着,手上的活计没有停。她知道,自己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路。但就像父亲说的——但凡急于成形,便失了万千可能。
她还想看看,自己的人生,还能有多少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