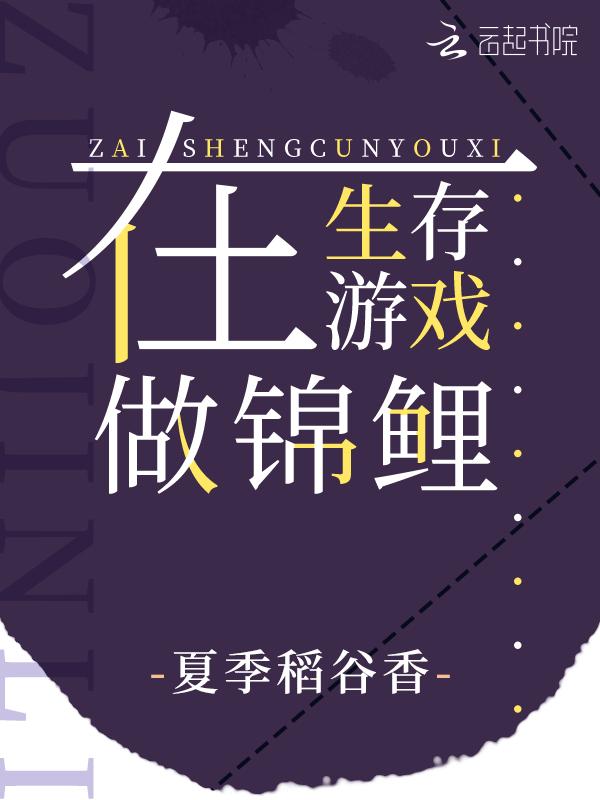奇书网>西岭雪山人流情况 > 五会飞的流言棉衣(第1页)
五会飞的流言棉衣(第1页)
五、会飞的流言棉衣
A、
吴先生走了,走之前,留给我一张存进一笔小款子的太平洋卡,用的是我的名字:云无心。
他说:“这张卡留给你,我们都知道密码,我会记得叮嘱秘书随时查询。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把钱提空了,我会安排秘书存款进去。”
这样的关照,比我期待的还要好。
这使我在他走前的最后一天,忽然对他生出了几分真情。此前,使尽种种手段,也说过许多甜言蜜语,都是做戏,但是那一天,跟他挥手道别时,我眼中的泪痕是真的。
我会对许多不相干的人免费赠送我的笑容,但从不奉献泪水。
眼泪,是我最珍贵的真实。
吴先生走后,我多少有些落寞。毕竟,他是唯一一个在临走时追问我名字的客人。
他在离开梅州之际,在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再见面的临别前夕,问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的名字叫什么?
就冲这一点,我知道我和他之间,不是嫖客与妓女那么简单。
嫖客不必关心妓女的名字。
我怀疑吴先生是不是有一些爱我。真诚的,不止于肉欲与美色的,那种属于纯精神领域的爱情。
这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我也还是渴望爱情的。
从大一,到现在,不曾改变。
大学时代的我曾经如此美丽。
如花的年纪,如花的样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零花钱丰富,处处表现得都像一个公主,谁会了解那钻石冠后面半弃儿的辛酸?
每天下了自习,都有小男生站在寝室门外等;电话铃一响,室友们头也不抬说:“无心,找你的。”所有的节假日都被约会塞满;光是挑选周末晚会的舞伴已经让人头疼不已……
舞会在大教室举行,雪白的日光灯管,简单的音响设备,没有乐队,没有布景,把课桌推到墙角辟出一片乐园,男生女生羞红的脸,眼神不敢相对,可是眼里满是流光溢彩。我总会在舞会进行到多一半的时候才进入,引起小小**,艳羡与妒恨的眼神纠结在一起包围我,不相识的男生走上前来问:“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吗?”
我展开一个安琪儿般甜蜜单纯的笑,不回答,亦不拆穿。校花云无心的名字,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不过是要借这个老问题来亲近罢了。
隔了那么多年,又有人来问我了:你叫什么名字?
问的人,是真的真的不知道,虽然早已亲近。
青春的铺满鲜花的成功路是在什么地方忽然转入岔道的呢?
昨天品学兼优的大学生,《庄子》研究的何教授的关门弟子,转瞬间成了“夜天使”的女歌手,靡靡之音取代了朗朗书声,从一个男人的怀里舞向另一个男人的怀里,难得有人问一句“你的真名是什么”已足以令心潮澎湃……
为什么我会是我母亲的女儿?
我对夕颜说:“为什么我会是我母亲的女儿?”
夕颜答:“这是没得抉择的。”
那一刻我如遭雷亟。
这明明就是我的口吻,夕颜仿佛一面镜子,不,仿佛是我另一个自己,替我说出我最想说的话来。
但她只是轻轻叹息:“无心,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不,我们是两种人,截然不同。”
“有什么不同呢?都是成长在破碎的家庭里,却苦苦地寻找完整。”
我再一次被击中了。无边的恨意涌起。恨她的聪明,恨她的清醒,恨她那么彻底地看穿了我,而我却对她一无所知。
夕颜在泮坑之游的当晚请假。但是关于她的故事,她的身世之谜,却不断地有新的版本传出来,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
流言就像一床张开袖子飞舞的陈年旧棉衣,拍打上去,灰尘嘭一下飞起,从一间屋子飞到另一间屋子,从一个人面前飞到另一个人的面前,经过之处,灰尘扑面,每个人都好像试穿过一次似的,身上留下了棉衣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