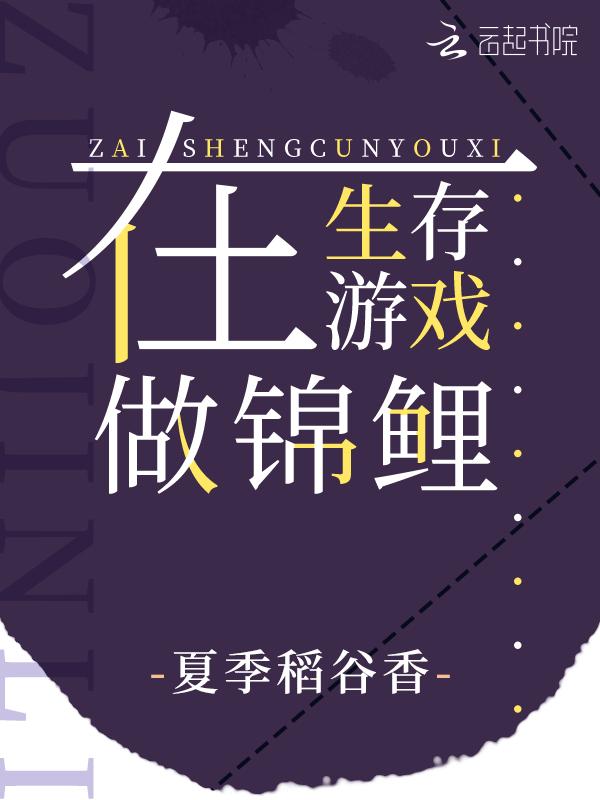奇书网>中国侦探作者 > 在火车上(第2页)
在火车上(第2页)
“去家里过年,是吗?”
“不是,去工作。”
贡尚烈本来希望对方能说出旅行的目的,现在虽还不曾完全如愿,可是话题确实已接近一步。他就单刀直入地接触主题。
“请问,两位在哪一个机关工作?”
年轻的正要再回答,但一抬头,看见他的同伴向他瞅了一眼,便把话煞住了。
年长的简短地答道:“我们是工人。”
“喔,工人老大哥,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吃得开!”他竖起了右手的大拇指,“失敬,失敬。”贡尚烈还把身子向前偻一偻,简直像鞠躬的样子。他把一顶“高帽子”送给对方之后,紧接着逼问一句:“是在钢铁工厂里工作吧?”
“高帽子”没产生效果。穿呢制服的不回答,只侧过些脸,向他瞧一瞧。那年轻人只把眼光在他同伴和贡尚烈的脸上溜来溜去,同样闭紧了嘴。贡尚烈觉得形势不顺利,不便再问下去。
他默默地想:“口风真紧,话一触到关子,就关门,真厉害。”
他感觉到有必要再找一两句离开主题的敷衍话,来把这局面调剂一下,不让它形成僵局,因为僵下去,可能露出他的狐狸尾巴,有危险。他迅速地拿起留在座垫上的纸烟盒,抽出一支来,送过去。
“同志,请抽一支。”
那叫做老李的摇摇头。“我不抽烟,谢谢。”他的视线转到贡尚烈手里的那只金蓝色的纸烟盒上。“这是什么烟?”他淡淡地问,眼光又回到他的脸上去。
“喔,是白锡包。”他再把纸烟送过去,“抽一支玩玩,没关系。这烟味儿还不坏,保你不呛口。出门人到处是朋友,别客气。来。”
老李仍冷淡地摇摇头,连“谢谢”也没有了。
“你从哪儿来?”少年提一句反问。
“广州,跟你们两位一样的啊。”
贡尚烈觉得这个人不但戒备森严,不吐一句关子话,而且像要开始向他反攻了,但是他仍老练地回答。
“是一向在广州的?”老李再问。
“不,我一直在香港。”
“你搞什么的?”
话一句紧一句,不但是正式反攻,而且有直捣核心的意图,因为这一句话含着双关作用,可以算问他做什么事情的,也可以解释做“你是不是搞特务勾当的”。这不能不使贡尚烈暗暗地吃惊。他原来的企图失败了,现在已处于被动地位。不过他究竟是个“老手”,外貌上仍旧丝毫不慌乱。
“我开一爿小商店。”他嘻一嘻,让身子偻近老李些,好像对一个熟朋友说一句知心话似的,又轻声说,“老大哥,我是小本经营,别把我看做资本家啊。嘿嘿嘿!”
一阵傻笑果然把渐渐紧张起来的气氛冲淡了些。一个年轻的列车员恰巧走进来扫地,这又给贡尚烈做了解围的救星。他趁机站起来,从容地烧着了一支纸烟,踱到寝室外边那狭长的过道里去。
他擦过几个站在过道中看野景的旅客,慢慢地沿着过道走,偶然向几间寝室门内望一望,人家也扭过脸在看他。他总觉得这些眼光好像有些异样,不敢多看,就匆匆地过去了。将近车厢尽头,他看见车厢门口的空隙处,有两个穿棉制服的解放军,靠着车厢门口的玻璃窗,面对面地站着。他们的脸儿都是红润润的,精神很饱满,服装也整齐,这时正出神地谈着什么问题。贡尚烈连忙煞住步子,想先偷听一下,要是机会好,他还企图走上前去搭讪。对于这些人,他是无论如何不肯放弃的,尽管这两个人的说话声音很低,但他一句都不让漏掉。
一个说:“苦闷?干吗苦闷?‘不怕慢,只怕站。’这一句老古话挺有意思。只要肯经常不断地练,保管你下一次会超过。”他的个子高大,年纪比较大一些。
“不是练不练的问题。”另一个短小精悍的年轻人回答,“说到练,我从来没有放松过。这一次我简直倒足了霉!”
“哼!还是倒霉,倒霉!”
“上一次卧射,我三枪三中,打25环。你不是也瞧见的?前天,竟只打14环、这不是倒霉是什么?”
高个子的忽然笑起来:“孩子,你在文化班上学会的算学到哪儿去了呀?”
“什么意思?”年轻人分明不能理解对方的话意。
“我问你,前一次比赛是几米?”
“100米。”
“这一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