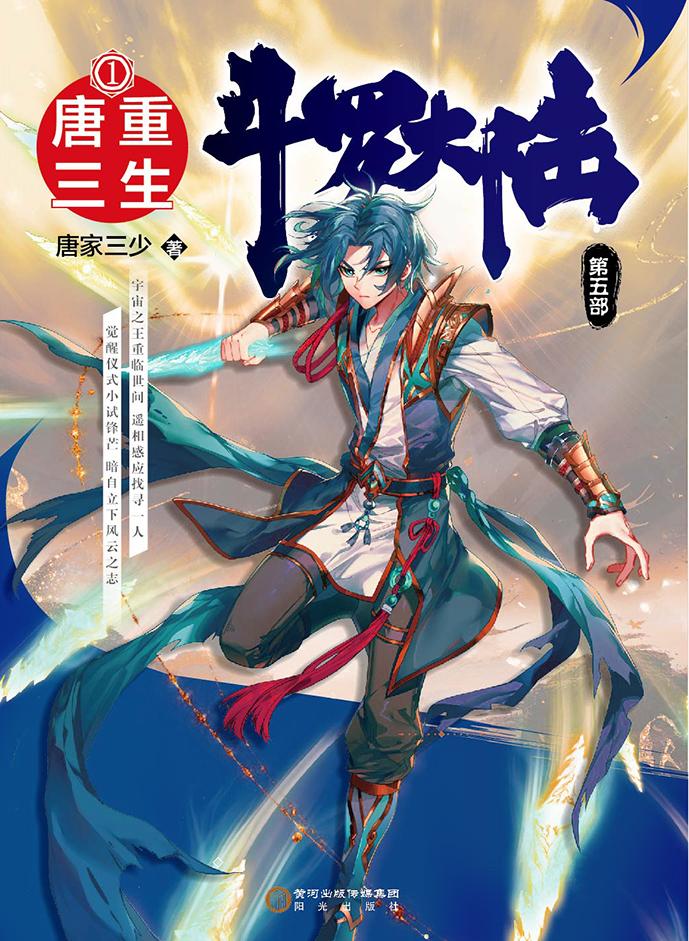奇书网>镜像的自己才是真实的自己吗 > 2011(第1页)
2011(第1页)
2011
直线与漩流
11月25日至27日,我应邀到贵州大学做一个讲座。凌晨六点出发,上午十一点抵达。午饭匆匆,下午两点半开讲,四点半结束。接下来似乎应该收拾行李打道回府。这是原初的计划,也是近年来已经习惯的工作方式。但下面的事实证明,情况有变。
人到中年,会背负种种工作和生活的重负,但人也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寻找快乐。所以报告会之后,应两位学兄和学弟邀请,也就义无反顾地直奔一个隐没于黔东南的古城。这个古城叫镇远。
中国的地名很有意思。按照自《尚书·禹贡》即规划出的国家疆域的雏形,王朝所在的核心区域在中原,王城的名字大多散发出温柔敦厚的气息。像长安、洛阳、开封或汴京,都意在显现帝王所居的博大雍容。而越趋于边境,其地名必然刚猛肃杀之气越强。北京这座城市也一样。在它的中心地带,“天安”“地安”包裹着中间的“长安”,“左祖右社”拱卫中间的“太和”。周围的延庆、怀柔、顺义,则显示着一种从仁德到节义、从文攻到武卫的递变。
镇远也是一样。按照古代中国的地理框架,这座小城地处中国的西南边陲,与中原王朝的核心地带有距离,所以够“远”。远的就让人不安心、不信任,所以要用武力去“镇”。镇远之为镇远,大概就起于这种“空间之远”与“人力之镇”的词义配合。
26日晚抵达镇远,下榻在一个名叫宇洁宾馆的民居里。一夜无话。第二天清晨,便看见窗外临了一条自西之东的大河,河上有一座千年古桥,便知道此行要和一段久远的历史展开极有意义的对话了。
我喜欢古镇,因为古镇有自己的历史。历史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它是虚幻的,但加上想象抑或是事物本身提供的诱因,它总是能将人引入一种让人怅惘的纵深。这种纵深是不是历史的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广延的空间之内置入了纵向的时间。空间关乎视觉感知,时间关乎情感记忆。所以唯有被历史表征的时间是与人记忆与情感的沉积相联系的,也唯有时间才能实现一段美景从视觉性景观向精神深层体验的挪转。
但今天,我并不想记述我对这个小镇趋于完整的感觉,比如它的布局,它被一条河流区隔出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以及它那让人迷醉的雕花的窗。我想珍存于记忆的,只是它建筑的式样。
建筑,是一座城市的纪念碑。不管它有意为之,还是无心造成,都最能揭示出一座古镇被岁月尘封的历史。记得那晚在镇远,可以勾起人历史记忆的东西很多,但唯一让人难以忘怀的,却是它的白墙黑瓦,尤其是那挑起的飞檐以及作为中国徽派建筑最显著标志的马头墙。
我不明白,为什么,在中国的贵州,这与安徽相隔数千里、隐没于重峦叠嶂之中的黔东南小城,会有成片成林的徽派建筑存在;我也难以知道,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让人穿越时空的隧道,会将一种被历史定格于某一地理区域的建筑方式,以几乎同样的方式在另一无法设想其关联性的区域复现。
返回北京,一切渐渐变得明了。这与这个民族漫长的移民历史有关。建筑的让人惊艳的方式,只能被视作一个民族迁徙历史留下的让后人慨叹的印迹。
过去,我总感觉,中华民族的移民历史,基本沿着自北向南的方向。比如,北方恶劣的生态环境,驱使着草原民族向南迁移,成为黄河流域的新主人。而被驱赶的原住民,则向湖广、江浙或岭南地区转移。于是,中国这片国土上居民的生活史,基本上呈现出从北向南的浪涌式更迭史。而黄河流域,基本上可视为这种候鸟式的南北迁移史的一个存于中间地带的驿站。
但事实上,贵阳之行却证明,这种线性化的对中国移民史的认识是错误的。如果将中国历史设定为一个从北向南的浪涌模式,将无法解释这种惯性运动所遭遇到的局限。这是因为,如果设定生态问题压迫着北方草原民族南迁,而中原民族则一波接一波地迁往更遥远的南方,那么有一个问题就必须注意,即南方并不是没有尽头。比如,在江浙及岭南的更南方,面临的将是一望无际的浩瀚海洋。我们不能设定,人类会重复今天只有在动物世界中才能看到的让人心悸的悲壮图景,即这些被驱赶者或被挤压者,会像黑压压的种种动物们一样,选择投海,而且前赴后继!
当然,人类历史中,像动物一样因走投无路而投海者并不鲜见。像南宋幼主卫王赵昺,就顺着生物学的规律,被一个名叫陆秀夫的所谓忠臣背着投了海。在此,所谓忠贞,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赞扬的。因为这种选择,并不比今天看到千万只负鼠义无反顾地跳海自杀更惊心动魄或者壮烈。我相信,所谓道义或忠贞,最终可能仅仅只是对生物学规律的复归或顺应。所谓道德的至高无上,最终可能仅是复归于动物性的最原始的本能。
但很显然,自北至南,这种东亚大陆人类最具惯性的迁徙方式,或者南宋幼主以投海所彰显的最至高无上的道德或者返归的最具本能的生物性,并不是每一只作为候鸟的人类都可遵循的。在1279年3月19日陆秀夫背着卫王投海的那个当口,可能更多的人沿着南方大海为人类生存划定的边界,选择了向西的转弯。这种转弯很重要,在最原始的意义上,它意味着人除了壮烈的死本能外,还有更强劲的求生本能和智慧。这种智慧昭示的不是宁折不弯的果决,而是为避免无谓的“折”必须选择“弯”。
作为这种“弯”的智慧的体现,东亚大陆人口自北向南式的直线型迁徙路径,自元明以后被调整成了一个弧形。也就是说,生态的压迫使人口首先发生了自北向南的浪涌,然后南部大海划定的边界,又让这股人口的巨流转弯涌向西南。
南宋以前,中国人口自北向南、然后再折转向西的移民路径的选择,在史料中找不到比较显明的验证,但自明代以后,这种西迁的路线图却日益变得清晰。朱元璋建立明朝,其依托的江淮子弟对西南的经营,大抵是沿着从江淮向湖广、云贵地区的西移路径。至此一切也就变得明了,也就是说,镇远古城之所以表现出那么明显的徽派建筑的风格,大多是因为江淮地区人口西移的结果。
历史上,这种人口的西移,也是以浪涌的方式完成的。到民国时期,这种趋势依然在延续。也就是民国政府在抗战时期将其都城向重庆的迁徙。云、贵、川随之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移民汇聚之地。
当然,中国人口迁徙一旦改变了它自北而南的路径,随后也就变得更富弹性。自民国以后,这种由直线弯转而成的弧形,依然继续以更弯曲的线条延续它的方向。新方向是从云贵到四川,再到青海和新疆。正是因此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新疆,除了中原地区人口的直接西移外,以四川的外移人口为盛。
这样,从“骏马秋风塞北”的北方草原,到被“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装点的秀丽吴越,从“极目楚天舒”的湖广,再到重峦叠嶂的云贵高原。再折返而至四川,继而延伸至新疆,这种弧形的轮廓,也就基本可以概述中国数千年人口的迁徙线路。至于东渡而至日本者,跨海而至南洋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北来南往者,只能被视为这一主流路径周围溅出的一些零碎火星。
历史充满了人性,但真正构建起运行规律的,依然是自然。正像南方以“天涯海角”为标志的海岸线斩断了中国人自北至南的惯性迁徙。此后,空气稀薄的青藏高原又何尝不在阻断中国人口从云贵移向更遥远的“西”?这一人口巨流在现代从四川涌向西北,又何尝不是遵循了青藏高原为人的生死划出的一条不可轻易僭越的陆上边界?
不管如何,看似无序的历史变迁,在此形成了一个人口运动的弧形。或者按照雪莱的讲法,时间的湍流在此一变而化为“水晶的卷轴”。
这种有趣的弧形,极易让人想起佛祖轻轻翘起的莲花指。所谓“一毛孔中,万亿莲花。一弹指顷,百千浩劫”,难道一个民族让人**气回肠又让人兴发无尽兴亡之叹的历史,就是为了应验佛祖那纤纤细手的不经意弯曲?或者仅仅只是以惯性的运动去完成一种“卷轴化”的审美形式?
也许,历史以其生物性的规律给人类设定了诸多不可逾越的限界,所以天道似乎永远重于人道。但是,在诸种已被历史固化的带有宿命感的运动形式中,探寻人性的歌哭与悲欢,可能才真正构成了人文科学的任务。
正是因此,可能若干年之后,镇远之行最能勾起人的记忆的,不是景观,也不是上面这个被历史以其运动曲线勾勒出的“卷轴式”的冷漠图像,而是宇洁宾馆的老板娘对她的家族史的讲述:她的祖辈来自江西,中过举人,父辈仍是能说流利英语的读书人。到她这一代,家族的事业则矗立成祝圣桥头的这座宾馆。
与宾馆老板娘的聊天很温馨,正像历史很人性。但历史又总是以其滚滚车轮般的惯性辗压每一个脆弱的个体,所以它又很残酷。这是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就像理性与感性永远对立,真理与价值永远悖反。现代以来,历史家往往更愿意通过小人物来透视大历史,用大历史去折射被命运操弄的小人物,大概就是要在天道与人道、理性与感性、真理与价值之间探寻一条中间道路。
哲学也是如此,它需要硬心肠也需要软心肠。既需要让两种心肠保持张力,又需要在两者之间进退自如。
201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