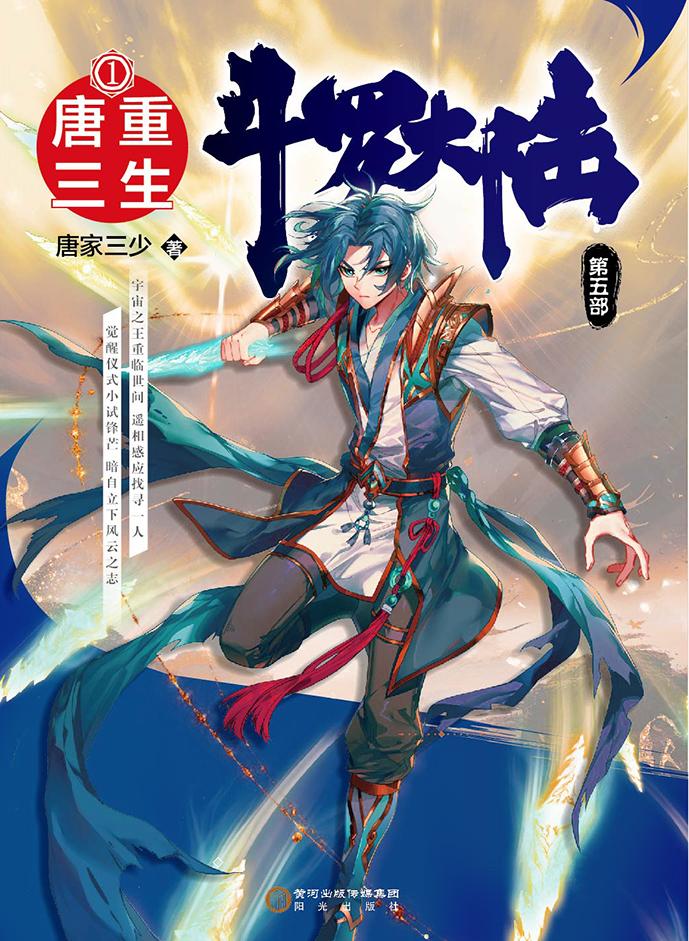奇书网>给他当狗是要排队的 > 第112章(第1页)
第112章(第1页)
他将新拟的流程章程分发下去,条理分明,让众人豁然开朗。
李大人闻讯赶来,看着那本整洁的账册,抚须长叹:“书砚之才,远超老夫预期啊!”
就在周书砚渐获户部人心时,早朝的金銮殿上,一场风暴正悄然酝酿。
早朝的钟声穿透晨雾时,周书砚已立在朝班之列。
新授的户部右侍郎官袍穿在身上,比太傅朝服更显沉敛,只是那过于宽大的袖口,衬得他手腕愈发纤细。
他微微垂着眼,听着百官奏事,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玉带——每隔两日的早朝,对他本就虚弱的身子是桩不小的负担,可想到下午还要去东宫授课,便又挺直了脊背。
御史中丞突然跪伏在地。
“皇上,臣有要事启奏!”
“哦?何事?”坐在龙椅上的永熙帝谢乾宇将半阖的眼睛眯起来。
“臣要告发太子殿下私吞三个月边关军饷!”
“可有证据?”
御史中丞从怀里掏出几本账册,“三日前有人将这些账册抄本送至府院门口,臣点灯夜查,发现与太子有关,不得不将此事上报。”
周书砚瞳孔一缩,这绝不可能!
二皇子谢栖泽站在一旁,嘴角噙着若有似无的笑意。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像一簇火苗,瞬间将朝堂众人点燃,朝臣纷纷交头接耳。
三皇子谢栖睿则垂着眼,指尖摩挲着朝珠,似在看好戏。
这时一个白胡子官员皱着眉站了出来:“太子乃一国储君,不可听信一家之言,不如将太子殿下宣至朝堂,了解事件全貌。”
至于为什么二皇子和三皇子能出现在朝堂上,太子却在东宫上课?
这是有原因的,二皇子三皇子都被授予官职,自然可以站在朝堂上,只有谢栖迟刚从边疆回来,不仅未被授予官职,还被安排太傅授课。
其中深意,不言而喻。
“准,宣太子。”永熙帝闭眼应允。
谢栖迟被传入殿中,玄色锦服衬得他眉眼愈发冷厉。
永熙帝倚靠在龙椅上,支着头,语气淡淡:“太子,有人告你私吞边关军饷,你可有何话要说。”
“一派胡言!”他攥紧拳头,指节泛白。
他转向朝臣们,目光炯炯,“本太子在边关浴血奋战时,你们这群只会动嘴皮子的,倒学会构陷忠良了?”
御史中丞害怕的后退一步,谢栖迟一眼就发现了,当即便要上前教训他。“就是你在胡言乱语!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御史中丞吓得瘫倒在地,双手抱头,“我,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