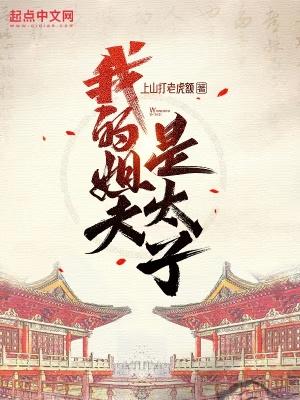奇书网>胡赛尔现象 > 第三节 发生现象学的研究状况(第2页)
第三节 发生现象学的研究状况(第2页)
在此基础上,阿古雷试图确立这样一个观点:悬搁或还原是经验批判的结果,而这种批判恰恰是先验观念论本身的建构。因此,悬搁或还原是先验观念论的结果。但问题是,这种作为还原之动机引发的先验观念论本身就应是现象学的自身思义(Selbstbesinnung)。据此,这种自身思义就处于一种悖论境地:为了能够成为现象学的,这种先验观念论恰恰需要现象学还原,而它本身却应是还原的引发动机。也就是说,它以其想要论证的东西为前提。为了解决这一悖论,阿古雷区分了单纯方法性的还原和先验现象学或哲学的还原。
单纯方法性的还原使我们的目光从对世间之物的唯一的指向性中解放出来,转向我们的体验。它把这种体验看作显现(Ersg),亦即看作现实性之自身给予的(selbstgebende)场所。但是,这种单纯方法性的还原中已存在一个原则性的决断:仅将对象或世界一般看作经验的经验物。这种原则性的决断的合法性何在?阿古雷认为,其合法性在于一个基本的明察:“世界存在,但它的存在在于我的陈述。”这里所表达的是一种怀疑的意识,它使所有的存在物都与现时经验着的主体相关。因此,先验现象学的自身思义之内在的、系统的开端在于怀疑。在阿古雷看来,这种开端的悬搁,亦即单纯方法性的悬搁,是一种怀疑的悬搁。它不触及存在之物的客体性,也不对存在和存在者的意义做陈述。但是,它使思义者看到了意识与现实性之普遍的相关性。因而,不是绝对的对象或世界而是其对于意识的相关性方式,不是存在者而是显现,将成为这种思义的开端。
阿古雷由此推进到其研究的中心论题:作为严格科学的现象学建立在这样一种可能性的基础上,即在严格排除存在现实性的情况下,只将显现,亦即现实性之意识的方式论题化。显现作为原素之立义的产物,与立义、原素一同构成意识的实项(reelle)要素,体验在其活的实行中就由这些要素组成。但是,在体验中,意识超出实项要素而朝向被意指的对象。它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意向对象不可分割地属于这种经验性的生活。阿古雷认为,胡塞尔的立义—原素或统觉—原素图式尽管遭受多方诟病,却是构成整个先验现象学学说或先验现象学观念论的支柱。因为,胡塞尔自始至终都将意识看作被统摄地构造着的意识。换句话说,他总是将世界规定为原功能性的主体性的普遍的统觉。在静态的意向分析中,统觉与原素的区别只是暂时的,其最终意义只有通过对内时间意识的分析才能得到理解。而当这种统觉—原素图式获得一种时间性的—历史性的意义时,静态现象学就过渡到发生现象学。只有发生现象学才能完成先验现象学的观念论,才能兑现彻底的经验批判。
根据阿古雷的观点,现象学要想澄清存在和存在者的最终意义,就必须从静态现象学过渡到发生现象学。这种过渡是现象学思义逐步深化的过程,直至内时间意识。其出发点是静态现象学所获得的作为意向意指物的对象。通过对其经验的视域结构的揭示,经验着世界的生活的各种不同的层级和结构逐渐显露出来。它揭示自身是一个“无限的生活关联域”(Lebenszusammenhang),一切对象性都以严格的动机引发的方式产生于其中。从发生现象学的观点看,现实的经验物是统觉的产物,亦即被统摄、被经验为某物,而这个某物总是隶属于某种预先熟悉的经验类型。这种预先熟悉的经验类型是源于经验历史的习性获得物。统觉把当下的被给予物转载到其历史之上,这种经验的历史以历史地获得的视域形态规定着先验主体性的当下生活。因此,统觉是生成于现时经验中的、先验主体性的发生性的—历史性的状态。当现象学的思义深入这种发生性的—历史性的层级时,所有的现实性就揭示自身是某个绝对的、未分化的开端之发生性分化的结果。与原功能性的(urfungierende)主体性的非历史性不同,所有存在者和全部现实性都是统摄性的构成物,因而完全是历史的产物。由此,阿古雷站在发生现象学的立场上做出了论证:先验主体性的充分展显就是先验观念论,它作为经验的批判将动机引发先验现象学还原。而由于先验观念论显露了一切存在者普遍的历史性,亦即其统摄性的状态,因此,还原就是回溯到纯粹的现象。这种纯粹的现象是一种无视域的和无统摄的显现,亦即未分化的、非时间的开端。[15]
5。阿尔麦达论开端与起源
在《胡塞尔发生现象学中的意义与内容》中,阿尔麦达从胡塞尔的代现理论(Repr?sentationstheorie)或立义(Auffassung)—内容(Inhalt)图式切入,以静态现象学向发生现象学的发展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为线索,通过对静态的构造与发生性的构造之本质区别的阐明,揭示出立义—内容图式在发生现象学中所必然导致的“最初的开端”和“无穷回退”的悖论。借此,他阐明了发生现象学的本质:关于构造过程之世界起源的探究。
代现理论是胡塞尔早期现象学研究最重要的理论假设之一。尽管随着先验主体性和先验构造的揭示,代现理论呈现出某种新的意义,但是,其主导思想始终未变:在意识的体验流中,认识对象由直观内容展示自身,直观内容只有借助于主观实行的立义综合才能成为对象的展示性内容。由于被给予内容只能被看作对象的展示性内容,而立义自身带有某种意义,它赋予被给予内容灵魂,并借此赋予其对象关涉性(Gege)。因此,意义和内容是认识意向性的两个基本原则,它们在立义综合中彼此中介。阿尔麦达的分析表明,在静态现象学的范围内,代现理论或立义—内容图式不会招致明显的理论疑难。但是,当现象学开始通过一种发生性的分析将意向过程本身论题化时,一旦问题涉及被动综合中被给予内容或感觉素材(Empfindungsdaten)的构造和主动综合(aktiveSynthese)中意义的制作,就必须放弃这种解释图式。
阿尔麦达认为,首先,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决定性区别在于对先验主体性之存在方式的不同理解。在静态现象学中,自我本身只具有一种逻辑意义,它是意识行为的一种意义结构,一个本身空乏的关系极。而在发生现象学中,自我是一个主动制作性的主体和习性的基底,因而是一个历史的、生成性的自我。这个自我不是源于构造,而是源于生活。其次,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区别在于构造概念的本质规定的差异。在静态现象学中,构造仅仅意味着意向活动的杂多与意向相关项的杂多之间的相关性,或自我的行为与对象之间功能性的相关性,因而仅仅考虑到意义给予(Sinngebung)本身。而在发生现象学中,构造则意味着意义给予本身之可能性的创立。在静态现象学的范围内,由于构造意义和内容之主体性的规则性还不是主体之具体的制作权能(Erzeugungsverm?gen),而只是逻辑的可能性条件,因此,意义的先天性和内容的预先被给予性尚不构成明显的理论疑难。而在发生现象学中,意向性被理解为一种主动的制作过程,意义和内容本身被看作具体主体的成就,因而意义和内容的构造问题就成了论题。这种发生性的构造问题域的展开,必然导致一种悖论性的结果。
在阿尔麦达看来,与静态现象学将最初的综合要素仅仅看作立义综合之结构性的奠基层次(Fundierungsschicht)不同,从发生性分析的立场出发,还必须探求一个时间上的最初之物。于是,意向过程的开端问题,亦即原统觉问题就产生了。在这种原统觉中,某物第一次获得被给予性,因此需要探究:构造性综合中的立义内容和立义意义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对此,似乎存在二者择一的回答,即要么接受“无穷回退”,要么承认存在“最初的开端”。按照第一种回答,所有综合的构造要素本身都是在先前的综合中被构造出来的,结果导致构造过程的无穷回退。按照第二种回答,存在最终的构造要素,即感觉素材和原初的对象意义。它们直接作为最终的和不可逾越的可理解性的视域存在于那里,亦即作为知性的事实性先天存在。但是,阿尔麦达认为,事实上,现象学中不存在这种二者择一的回答。就“无穷回退”而言,构造过程本身的无穷回退意味着构造最终是无根基的;就“最初的开端”而言,如果构造过程中存在一个纯粹意识事实方面的“最初的开端”,那么构造过程也是无根基的。因为虽然它似乎有一个最终的基础,但是,这与构造意向性的观念相悖。构造意向性意味着,对于主体来说,只有通过主体的构造力而生成的东西才是存在的。因此,这种纯粹的意识事实是一种非理性的被给予性。
阿尔麦达认为,这种“无穷回退”和“最初的开端”的两难抉择潜存于代现理论中。只要现象学仅限于对意向性做静态的描述,这种理论疑难就是潜在的;而当胡塞尔对意向性做发生性的分析时,它就会凸显出来。在静态现象学中,意向描述处理的是意向过程的共时性问题,没有将意向过程本身论题化。它仅揭示各种综合或意义给予的层级建构,因此,行为意向的分析——它将意向活动的功能和原素的或意向相关项的杂多作为论题——恰好适合于解析这种多层次的综合或意义给予。但是,在意向过程之发生问题的探讨中,这种行为意向的分析不仅不合适,而且清晰地凸显出理论上两难抉择的困境。在阿尔麦达看来,只有以行为意向的分析处理发生问题时,才会产生这种两难抉择的困境。因为从行为意向性(Akti?t)的立场出发,我们必须把所有综合的成就都看作某个现时的实行行为的结果,因而必须解析这种在时间进程中现时进行的综合。而这意味着,要么承认存在“最初的开端”(在它那里尚未有综合被实行),陷入非理性的开端的疑难;要么接受“无穷回退”,而这不仅与行为意向性分析所要求的开端的观念相悖,而且意味着构造过程本身是无根基的。阿尔麦达指出,行为意向性的发生性分析从一开始就未切中发生现象学的本质,而且必然导致这种两难困境。在他看来,视域意向性(Horizo?t)的发生性分析则能够避免这种两难抉择。因为它不再寻求最初的意义给予,而是力图指明,一切事实的意义给予都从对世界的原亲熟状态(Urbekanntsein)中获得其意义和其被给予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各个经验行为在自身中内在地拥有作为经验视域(Erfahrunghorizont)的世界,它构成各个经验行为的视域,也只有从这个视域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各个被经验之物。因此,对被奠基的对象性之发生关联的揭示表明,构成最终层次的不是感性的个体,而是作为视域整体的世界。
根据阿尔麦达的论述,世界现象必然在行为意向的分析视野之外。因为行为意向的分析指向对象之物的明见性,并把对象之物看作意义要素和内容要素之综合的产物。但是,发生性的分析表明,立义内容和立义意义不是封闭的统一性,它们具有视域般的整体性特征。也就是说,意义和内容自身含有一个非封闭的综合。通过对某个统摄性功能之被给予内容的解析,我们不是回返到那种从虚无中生成的基本要素,而是回返到在感觉的时间过程中时间结构的整体。同样,通过对谓词判断之意义复合体的解析,我们不是回返到最终的意义统一性,而是回返到作为无所不包的理解视域(Verstehenshorizont)的世界。阿尔麦达认为,作为视域的世界是无限的、可能的经验统一性,这种经验统一性具有观念的本质。它既是一个综合的、历史的生成过程,又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目的论的经验统一性。作为综合地生成着的经验统一性,世界是内容规定之被给予性的游戏空间;而作为观念存在着的经验统一性,世界是被给予物之意义规定的游戏空间。因此,意义构造和内容构造的最终基础是作为目的论的经验统一性的世界。对意义蕴含或意义历史的揭示并不回溯到原统觉或原被给予性,而是回溯到作为一个无限的和观念的综合的经验视域之开放整体的世界。
根据阿尔麦达的分析,一方面,只有从世界经验的视域性出发,亦即只有通过对视域意向性的揭示,我们才能理解被动综合之具体的可能性:存在某类综合。它总已被完成,但却没有被现时地实行。被动综合的“被动性”与对感性素材的“接受性”无关,而与一个目的论的经验统一性的观念相关。只有这个观念能开启世界经验之无限进程的视域。另一方面,对于世界经验的被动综合之本质的明察能使我们理解,为何构造过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开端,但却有一个出自世界的起源。世界总以构造生活之活的当下的视域的方式存在于那里。阿尔麦达的分析表明,发生问题不是关于行为意向过程的开端问题,而是关于构造过程的世界起源问题。因为作为经验视域,世界是一切意义性(Si)的基础和一切能被给予物(Gegebenseink?nnens)的游戏空间。因此,真正的发生问题是世界与被给予物、世界与意义之间的起源关系问题。[16]
6。兰德格雷贝论被动构造
在《事实性与个体化》中,兰德格雷贝清晰地勾勒出被动构造(passiveKonstitution)的问题维度和关联,及其在胡塞尔先验现象学中的地位。他认为,胡塞尔的构造概念的含义摇摆于“意义赋形”(Sinnbildung)与“创造”(Kreation)之间。构造概念的这种歧义性导致其后期“先验生活”这一核心概念的晦暗不明,而只有澄清“先验生活”概念,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先验主体性。因此,被动构造或被动综合问题对于正确理解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构造概念的这种歧义性并不存在于胡塞尔对主动构造(aktiveKonstitution)或主动综合现象的分析中,而仅仅与被动构造或被动综合相关。
首先,兰德格雷贝探讨了被动的前构造与现象学反思的关系。在胡塞尔那里,原被动性的最低层是指时间意识的综合。在时间意识的综合中,自我将自身构造成时间性之物,并且意识到自身是一个意识流。自我在时间性中的自身构造(Selbstkonstitution)问题是其后期现象学反思的重要论题。他认为,作为意识流而贯穿先验的内时间的普遍的意识生活是一种被奠基的意向成就。只有通过对这种意向成就的分析,现象学还原才能揭示一切经验之最终的可能化根据(Erm?glid)。而这种最终的基础层次,就是“原始地流动着的活的当下”或“在其持存着—流动着的生活中自身当下地流动着的绝对自我(absoluteIch)”。这个最终的功能性自我(fungierendeIch)是一切构造成就的源泉(Urquelle)。它构成一切超越之物的绝对基础,因而可以称之为“原现象(Urph?nomen)”,任何其他可以被称为现象的东西都起源于它。但问题是,我们应如何对待这种“原现象”,亦即如何确定最终的功能性自我的活动方式呢?
在兰德格雷贝看来,胡塞尔对此的回答似乎完全自相矛盾。一方面,他认为,最终的功能性自我之流动的时间化(Zeitigung)不是源于自我的作为(Tun),也就是说,被动的前构造的成就不是自我的成就。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时间性在所有方式上都是自我的成就。因此,问题在于,我们应如何确定最终的功能性自我的流动(Str?men)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胡塞尔对此所做的悖论性的解释:“这个流动总是预先存在,而自我也预先存在。”
兰德格雷贝认为,关键是我们应如何理解胡塞尔在此所谈论的自我和自我的成就。根据胡塞尔的观点,一方面,原初的自我不是源于经验,而是源于生活。这种生活不是为自我而存在的,而是其本身就是这个原初的自我。另一方面,不能在主动的成就意义上理解此处所说的自我成就,因为“在这个原始被动的流动中,某种匿名的存在意义(Seinssinn)通过前时间化(V)而使自身被时间化”。而只有通过事后的现象学反思,我们才能揭示这种匿名的存在意义及其前时间化过程。兰德格雷贝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活的当下这种匿名的存在意义,亦即“原现象”,不可能是一种自为的现象。因为只有当它成为反思的对象并因而被存在者化时,才能成为一种自为的现象。但是,反思指向的是业已完成了的活动,它是对这种活动的事后察觉。经过反思行为的中介,这种活动变样了。因此,在兰德格雷贝看来,反思不可能捕获这种活动本身,而现象学反思正是在“原现象”的认识中碰到了自身权能性的界限。
按照兰德格雷贝的分析,时间赋形(Zeitbildung)之构造成就的概念只是纯粹的功能—形式概念,其构造成就的实行需要某种被给予性内容。但是,这种被给予性内容并非《讲座》中那种与原印象(Urimpression)的意识相关的原素素材(hyletis)和《观念I》中那种作为无形式的材料的原素。尽管胡塞尔本人在后期关于发生性的构造的思考中已明确放弃了这种原素概念,比如在《现象学的心理学》中说“构造感觉素材的内时间意识”,在《沉思》中提及“提供一切材料的被动综合”,但是,他未能从中引出系统的结论。他没有对这种构造原素素材的成就做出明确的现象学分析。兰德格雷贝认为,只有通过动感意识(kiischeBewu?tsein)的分析,才能澄清原素素材的产生。因此,应当把时间意识的被动综合与动感的综合联系起来思考。因为如果没有印象就没有构造着时间的成就,如果没有动感就没有印象。在他看来,一切触发原初都是作为“我”的身体器官的感觉器官的触发,而一切动感运动都是感觉器官之触发的可能性条件。原素产生于动感过程,没有这种动感过程就没有活的流动着的当下。因此,身体性不仅是被构造之物,而且是构造性的。它是一个相应于各个感性领域的权能性系统,因而属于先验主体性。根据发生现象学的观点,身体在发生上首先是作为可支配物被获得的,因而对于“支配身体”的“能意识”(K?sein)在发生上先于发展了的“自我意识”(Ichbewu?tsein),对于“我的”(mein)的发现先于对于“自我”的发现。这表明,自我的自发性尚处于一种隐蔽状态,但却以隐蔽的方式起作用。兰德格雷贝认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胡塞尔那个悖论性的解释:“这个流动总是预先存在,而自我也预先存在。”
毋庸讳言,上述研究通过对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关系和被动发生问题的探讨,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观念,澄清了发生现象学的问题维度和层级结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发生现象学的方法论困境和发生现象学的可能限度。但是,从总体看来,这些相关研究仍缺乏对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系统展示。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学者聚焦于特定角度和问题;另一方面则在于胡塞尔有关发生现象学研究的许多重要手稿仍在整理出版阶段。例如,2014年出版的《胡塞尔考评版全集》第42卷,即《现象学的界限问题》,尚未进入上述学者的研究视野。因此,进一步整理和出版胡塞尔的相关研究手稿是深入研究和完整把握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必要准备和基础。
[1]参见罗克汀:《现象学理论体系剖析——现象学横向研究》,第七章,广州,广州文化出版社,1990;《从现象学到存在主义的演变——现象学纵向研究》,第六章,广州,广州文化出版社,1990。在第一部书中,尽管作者区分出静态现象学和发生现象学,并对发生现象学做了明确的界定,但这一含糊的界定尚不能使我们将其与静态现象学明确地区分开来,而且作者未就二者的关系做任何说明。第二部书中则有两点令人不解:(1)作者在第三节“构成现象学”中未能划分“静态构成”和“发生构成”;(2)在第五节“单子论的自我学的现象学与相互主观性的现象学”中丝毫未论及“发生”问题,反倒是在第四节“形相现象学”中论及“发生”问题。
[3]这部著作原本是德里达1954年的硕士答辩论文,法文版迟至1990年才得以出版。
[4]在这里,斯泰因伯克是个例外。他在《家乡与来世——胡塞尔之后的世代性现象学》一书中探讨了作为世代现象学问题的世代问题。他认为,探讨世代问题的世代现象学是现象学的第三个维度,而这一维度既超出了静态现象学的范围,也超出了发生现象学的范围。参见SteinboeandBeyoivePhenomenologyafterHusserl,EvanstoeryPress,1995,pp。3-4。
[5]参见Kern,I。:HusserluersugüberHusserlsVerh?ltniszuKantuianisum,DenHaag,MartinusNijhoff,1964,S。351-353;Almeida,G。A。de。:SinnundInhaltiisenologieE。Husserls,DenHaag,MartinusNijhoff,1972,S。7-8;Yamaguchi,I。:PassiveSynthesisuivit?tbeiEdmuheHague,MartinusNijhoffPublishers,1982,S。11-14;Donohoe,J。:Husserlohitersubjectivity:FromStatietienology,NewYork,HumanityBooks,2004,pp。11-12,20-21。
[6]参见FiudienzurPh?nomenologie:1930—1939,DenHaag,MartinusNijhoff,1966,S。139。
[7]参见FiudienzurPh?nomenologie:1930—1939,DenHaag,MartinusNijhoff,1966,S。142-143。
[8]参见Claesges,U。:EdmuheoriederRaumkonstitution,DenHaag,MartinusNijhoff,1964,S。34;Str?ker,E。:HusserlsTraalPh?nomenologie,FrankfurtamMain,1987,S。156-169。
[9]参见WeltoherHusserl:TheHorizonsofTraalPhenomenology,Bloomington,IndiayPress,2000,pp。235-236,251-255。
[10]参见Holenstein,E。:Ph?nomenologiederAssoziation:ZurStrukturundFunktioneinesGrundprinzipsderpassivenGenesisbeiE。Husserl,TheHague,MartinusNijhoff,1972,S。26-29;Carr,D。:PhenomenologyandtheProblemofHistory:AStudyofHusserl'sTraalPhilosophy,EvanstoeryPress,1974,pp。77-80;SteinboeandBeyoivePhenomenologyafterHusserl,EvanstoeryPress,1995,pp。4-8,37-48。
[12]参见Holenstein,E。:Ph?nomenologiederAssoziation:ZurStrukturundFunktioneinesGrundprinzipsderPassivenGenesisbeiE。Husserl,TheHague,MartinusNijhoff,1972。
[13]参见Lee,N。-I。:EdmundHusserlsPh?nomeinkte,Dordrecht,Kluublishers,1993。
[14]参见Yamaguchi,I。:PassiveSynthesisuivit?tbeiEdmuheHague,MartinusNijhoffPublishers,1982。
[15]参见Aguire,A。:GeisenologieuiründungderWissenschaftausderradikalenSkepsisimDenkeheHague,MartinusNijhoff,1970。
[16]参见Almeida,G。A。de。:SinnundInhaltiisenologieE。Husserls,DenHaag,MartinusNijhoff,1972。
[17]参见Laizit?tundIndividuation:StudienzudenGrundfragenderPh?nomenologie,Hamburg,Meiner,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