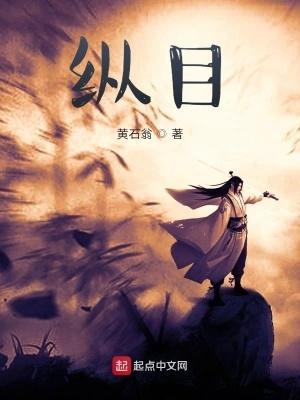奇书网>胡赛尔现象 > 第三节 发生现象学的研究状况(第1页)
第三节 发生现象学的研究状况(第1页)
第三节发生现象学的研究状况
尽管关于发生现象学的研究对于整体地理解和把握胡塞尔思想的本质形态和最终的哲学旨归至关重要,但是,它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总体研究中所占份额较小。这不仅缘于这一问题域本身的复杂性关联,还在于胡塞尔本人未能充分阐明发生现象学的观念和方法,未能足够清晰地揭示发生现象学的问题域的维度和层次结构。本书着重讨论胡塞尔后期思想中的“被动发生”(passiveGenesis)问题,借以澄清其先验现象学观念论的本质形态。与之相关,我们需要预先讨论这样两个问题:(1)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关系问题;(2)发生现象学的观念和方法问题。由于对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关系问题的探讨必然会展现发生现象学观念和方法问题的探讨方向,因此,我们主要就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关系问题和“被动发生”问题这两个方面谈一谈国内外发生现象学的研究状况。
首先,就国内研究而言,最早触及发生现象学问题的是罗克汀先生[1],稍后有倪梁康、张祥龙和汪文圣等先生。[2]2004年以后,国内学者关于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探讨渐趋系统和深入。专著方面有方向红的《生成与解构——德里达早期现象学批判疏论》、朱刚的《本原与延异:德里达对本原形而上学的解构》和王恒的《时间性:自身与他者——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列维纳斯》。《生成与解构——德里达早期现象学批判疏论》用较大篇幅讨论了发生问题,尤其可参见该书第一部分“生成与差异”。但是,该书是在胡塞尔与德里达的争论中给出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的观点的,没有正面对发生现象学的观念和方法进行系统的阐释和论证。《本原与延异:德里达对本原形而上学的解构》从德里达与胡塞尔的论争中凸显出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起源”观念。《时间性:自身与他者——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列维纳斯》第一章第四节“时间意识:被动综合与反思”较为深入地探讨了胡塞尔的“被动发生”问题。此外,王庆丰的《德里达发生现象学研究》和钱捷的《超绝发生学原理(第一卷)》,也从不同侧面触及了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问题。
论文方面主要有倪梁康、张廷国、钱捷、方向红、马迎辉、张浩军、王庆丰等人的相关研究。张廷国2004年发表的《简析胡塞尔的“前谓词经验”理论》一文在“前谓词经验”的标题下探讨了胡塞尔的“被动发生”问题。钱捷2006年发表的《〈几何学的起源〉和发生现象学》一文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视角比较性地探讨了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先生自2008年以后发表了关于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系列论文,深入和系统地探讨了发生现象学的核心观念和问题,引领了国内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研究的发展。其中,主要有《历史现象学与历史主义》《历史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中的历史哲学思想》《赖耶缘起与意识发生——唯识学与现象学在纵—横意向性研究方面的比较与互补》《思考“自我”的两种方式——对胡塞尔1920年前后所撰三篇文字的重新解读》《“自我”发生的三个阶段——对胡塞尔1920年前后所撰三篇文字的重新解读》《纵意向性:时间、发生、历史——胡塞尔对它们之间内在关联的理解》《纵横意向——关于胡塞尔一生从自然、逻辑之维到精神、历史之维的思想道路的再反思》《现象学的历史与发生向度——胡塞尔与狄尔泰的思想因缘》《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历史问题——历史哲学的现象学—存在论向度》等。倪梁康先生的系列论文立足于时间、发生和历史这三个发生现象学的核心问题,从三者的内在关联出发,深入揭示了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观念和问题维度。方向红的论文《静止的流动,间断的同一——基于胡塞尔时间手稿对意识之谜的辨析》和《自我的本己性质及其发展阶段——一个来自胡塞尔时间现象学手稿的视角》,从时间构造的角度探讨了自我的发生问题。马迎辉的论文《胡塞尔的双重意向性与〈观念〉》和《意向与时间化——胡塞尔时间构造中的发生问题》,借双重意向性和时间化问题探讨了发生与时间性的关系。张浩军的论文《论胡塞尔的“被动性”概念》《知觉的主动性与主动综合——对胡塞尔判断发生学的一个考察》和《从主动综合到被动综合——胡塞尔对康德“综合”理论的批评与发展》,探讨了主动发生(aktiveGenesis)、被动发生问题及二者的关系。王庆丰的论文《回问与发生现象学的方法》和《现象学的发生概念——从胡塞尔到德里达》,从发生性回问的方法论层面揭示了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观念。此外,朱刚的《理念、历史与交互意向性——试论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一文探讨主体间性与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的关系问题,陈伟《作为意识发生法则的动机引发——兼论胡塞尔超越论现象学的非笛卡尔式道路》一文探讨了意识发生的规则,李婉莉的《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及其对梅洛-庞蒂的启示》一文揭示了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思想效应,栾林的《从静态现象学到发生现象学——理解胡塞尔现象学发展的一条线索》一文探讨了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内在关联。
毋庸置疑,上述相关研究均在不同程度上触及了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核心观念和问题,并且做了有益的探讨。综括起来,这些学者所聚焦的主要问题有:(1)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关系问题,如倪梁康和马迎辉关于纵—横意向性问题的探讨;(2)意识和自我的发生问题,如倪梁康和方向红的相关研究;(3)发生与历史性的关系问题;(4)发生与时间性的关系问题,如倪梁康和马迎辉的相关探讨;(5)历史现象学问题,如倪梁康和朱刚的相关研究;(6)主动发生与被动发生的关系问题,如张浩军的相关探讨;(7)发生现象学的方法问题,如汪文圣和王庆丰的相关研究;(8)发生的规则问题,如陈伟的相关探讨;(9)被动发生问题,如张廷国和张浩军的相关研究。
这些探讨角度各异,涉及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研究的主要方面。但是,一方面,这些研究缺乏从观念到问题再到方法的系统研究;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缺乏系统性,它们未能深入揭示发生现象学问题域的总体维度和层次结构,以至于无法界定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无法真正澄清发生现象学的观念和方法,进而揭示发生现象学的可能限度。
其次,国外关于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有如下著作。20世纪30年代有芬克的《现象学研究(1930—1939)》。20世纪50年代有德里达(JacquesDerrida)的《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3]、布兰德(GerdBrand)的《世界、自我和时间》、迪麦尔(AlwinDiemer)的《胡塞尔:一种系统阐述他的现象学的尝试》和冯克(GerhardFunke)的《论先验现象学》。20世纪60年代有兰德格雷贝的《现象学之路》、黑尔德的《活的当下》和耿宁的《胡塞尔与康德》。20世纪70年代有阿古雷(AntonioAguire)的《发生现象学与还原》、索科罗夫斯基(RobertSokolowski)的《胡塞尔构造概念的形成》、费恩(HubertFein)的《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发生与有效性》、霍伦斯坦的《联想现象学》、阿尔麦达(G。A。deAlmeida)的《胡塞尔发生现象学中的意义与内容》和卡尔(DavidCarr)的《现象学与历史问题》。20世纪80年代有墨菲的《休谟与胡塞尔》、山口一郎(Yamaguchi,Ichiro)的《胡塞尔的被动综合与主体间性》、斯特洛克的《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和耿宁(与马尔巴赫、贝耐特合著)的《胡塞尔现象学导论》。20世纪90年代有李南麟的《胡塞尔的本能现象学》、斯泰因伯克的《家乡与来世》和库恩(RolfKuhn)的《胡塞尔的被动性概念》。2000年以来有威尔顿(Doon)的《别样的胡塞尔》、窦瑙霍(JaDonohoe)的《胡塞尔论伦理学与主体间性:从静态现象学到发生现象学》和蒙塔古瓦(K。S。Montagova)的《意识和认识的先验发生》等。另外还有一些讨论发生现象学问题的重要著作和论文在这里无法一一列出,我们会在后面的具体论述中涉及它们。
诚然,上述这些研究涉及胡塞尔发生现象学问题的方方面面,但与本书探讨的论题相关,我们重点就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关系问题、发生现象学的观念和方法以及“被动发生”问题缕述如下。
一、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关系问题
尽管胡塞尔后期转向发生现象学研究这一事实已得到确认,而且人们对“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共同构成先验现象学的完整系统”这一说法也几无异议[4],但是,在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关系问题上,论者之间却存在很大分歧。他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并且都能从胡塞尔的著作中找到根据。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1。补充说
这种观点认为,静态现象学以区域存在论的结构为引导线索,在意向行为与意向相关项的相关性中描述内在体验复合体的构造,借此达到对普遍的意识结构的构造性分析,但这种构造性分析仍停留于“现成的对象性”和“现成的统觉系统”的层次上;发生现象学则进一步探究这种静态意义上的构造的发生,亦即探究“现成的统觉系统”和“现成的对象性”的发生或起源,或者说,探究“现成的统觉系统”的历史和“现成的对象性”的历史。因此,在他们看来,发生现象学是静态现象学的必要补充,尽管静态的分析作为意识结构的描述方法始终是现象学的首要任务。这种观点以耿宁为代表,另外还有阿尔麦达、山口一郎和窦瑙霍等人。[5]当然,这些现象学专家的观点也存在某种区别。例如,在坚持这种补充说的基础上,山口一郎认为,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关系应被看作一种在“之”字形的前进步骤中相互补充的关系,阿尔麦达则用意识流横剖面与纵剖面的关系来说明静态分析与发生性分析的关系。
2。基本步骤说
这种观点认为,静态现象学只是发生现象学的基本步骤和预备阶段,不能代表一种独立的现象学观念,它是发生现象学的一部分。这种观点以芬克为代表。
在其著名的论战文章《当代批评中的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中,芬克将现象学还原的实行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现象学还原达到一个临时性的先验主体性层次,亦即通过消除世间性的自身统觉(Selbstapperzeption)而使先验生活(traaleLebeiviert)和脱世间化(e),并由此进入先验的信仰生活。对于先验的信仰生活来说,这种对世间性自身统觉的受缚状态(Befa)是一种有效性相关项。在此阶段,这种有效性相关项还是不确定的。第二阶段是通过对这种不确定的有效性相关项之内在特征的探究揭示出先验信仰生活之深层的构造层次。在芬克看来,尽管在现象学还原第一阶段只能达到这种具有其不确定的有效性相关项的临时性的先验主体性层次是必然的,并且保持这种有效性相关项的不确定性也是必要的,因为借此我们可以获得先验生活之统摄性关联的全域,但现象学在本质上是“构造现象学”,因为现象学的真正论题既不是单纯的世界,也不是单纯与其相对的先验主体性,而是“世界在先验主体性的构造中的生成”。[6]随着现象学还原的进一步实行,那个临时性的先验主体性层次必然为高层次的现象学所克服,成为先验生活之自身构造性的一个层次。因此,尽管现象学还原第二阶段的构造性分析必须以第一阶段所揭示的先验主体的世界拥有(Welthabe)为基础,但第一阶段所完成的、对于先验生活的意向分析成果只能被看作“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7]在此我们看到,尽管芬克只字未提“发生”“发生现象学”“发生性的分析”和“发生性的构造”(geution)这些概念,但其对于现象学还原两阶段关系的论述所涉及的正是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关系问题。这里的“还原第一阶段”的论题对应“静态现象学”的论题,而“还原第二阶段”的论题,亦即“构造现象学”的论题,对应发生现象学的论题。因此,在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关系问题上,芬克明确坚持这种基本步骤说。持这种观点的现象学家还有克赖斯格斯(UlrichClaesges)和斯特洛克等。[8]
3。重构或再结晶说
这种观点认为,静态现象学不能单纯被看作发生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步骤”或层次,发生现象学也不能单纯被看作静态现象学的一个必要“补充”。毋宁说,发生现象学的开显将会形成对静态现象学的“重构或再结晶”。这种观点以威尔顿为代表。在《别样的胡塞尔》中,威尔顿系统论述了这种“重构或再结晶”的观点。[9]在他看来,发生性分析从静态分析的结果出发,亦即探究静态的构造(statisstitution)的发生或起源,而一旦静态现象学本身成为发生现象学研究的引导线索,一种特有的“重构或再结晶”就成为必然。因为从发生性分析的观点来看,由于静态分析排除了发生问题,因而分析对象是一种从时间性中抽离出来的、“现成的”抽象物,是发生预先规定了静态的构造或静态现象。因此,为了达到对静态的构造或静态现象的具体把握,我们必须翻转引导线索的方向,从发生性的观点出发重新制定或修正以前静态分析的结果。持这种观点的还有霍伦斯坦、卡尔和斯泰因伯克等人。[10]
4。双重面孔说
这种观点认为,静态现象学和发生现象学代表两种独立的先验现象学观念,二者不能彼此还原。它们之间的差别表现在对构造之可能性条件的研究所选取的不同方向或采取的不同立场上。静态现象学的任务旨在揭示主观的有效性奠基,发生现象学的任务则是揭示发生性奠基,它们共同构成了先验现象学的完整形态,因而可以被称为“现象学的双重面孔”。持这种观点的有黑尔德、李南麟等。[11]
二、发生现象学的观念、方法和“被动发生”问题
从总体上说,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被划分为“主动发生”的问题域和“被动发生”的问题域,其中“被动发生”的问题域构成发生现象学的基层和核心,也是检验发生现象学的观念之成败的试金石。“被动发生”的标题下存在各种不同的问题维度和问题层次,如联想(Assoziatiolichkeit)、触发(Affektion)、动机引发(Motivation)、原素(Hyle)、身体性(Leiblichkeit)等。下面是一些简略的介绍,涉及迄今为止在国际现象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关于被动发生问题的专论。
1。霍伦斯坦论联想现象学
在《联想现象学》中,霍伦斯坦详细论述了被动发生之基本原则的结构和功能。据他考察,只是从1917—1918年胡塞尔转向现象学的发生问题以后,联想论题才真正得以先验地展开,而胡塞尔也正是从这一时期起将目光延伸到被动性(Passivit?t)现象。因此,他认为,发生、联想和被动性在胡塞尔那里是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标签。霍伦斯坦的探讨从联想的形式出发。他认为,联想不仅在当下、过去和未来的内容性关联中起作用,而且参与了当下的构造,而那种在当下、过去和未来之内容性关联中起作用的联想的唤起(Weg)正是以这种当下的构造为基点。据此,他区分了两种形式的联想,亦即原联想(Urassoziation)和通常意义上的联想。原联想包括触发性的联想和前触发性的联想;通常意义上的联想包括再造性的联想和预期性的联想。
与此相应,他对被动性现象做了区分。在他看来,被动性现象是没有自我参与(Ichbeteiligung)的意识现象,而它又可以区分出两个层次:原被动性(Urpassivit?t)层次和第二性的(sekund?re)被动性层次。原被动性现象是意识发生的最低层次。作为一种潜在的、一同起作用的过程,它伴随不同层次的主动意识成就一同进行,构成一切主动性(Aktivit?t)成就的前提。而第二性的被动性现象以主动性成就为前提,是主动性成就的积淀物,但又构成新的主动性成就的前提。在对联想的形式和被动性现象的层次做了这样的区分后,霍伦斯坦分别一般性地考察了联想在时间构造(Zeitkonstitution)、空间构造(Raumkonstitution)或动感构造(kiisstitution)、触发、共现(Appr?sentatio?t)、变式(M)、认同(Identifizieruierung)和习性化(Habitualisierung)等现象中的作用,借此确立了联想在被动性经验和接受性经验之构造中的地位。
据此,他又在分别考察了时间构造与联想性的综合、联想性的综合与对象的综合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几种联想性的综合的功能形式:融合(Versg)、统觉(Apperzeption)、共现、动机引发和被动综合(passiveSynthese)。霍伦斯坦的研究表明,在发生现象学中,联想既是一种发生性的综合,又是一种被动的综合,可以将其看作被动发生最重要的构造形式。被动性现象正是借助于内时间意识中联想的综合作用而发生的,因此,联想与内时间意识的综合不仅被看作被动发生之最重要的功能形态,而且被看作被动发生的最普遍的原则。[12]
2。李南麟论本能现象学
在《胡塞尔的本能现象学》中,李南麟探讨了意识之被动发生的最低层次,亦即本能意向性(Insti?t)问题。他首先从“在胡塞尔那里本能现象学究竟如何可能被理解为一门先验理论”这一问题出发,考察了先验现象学本身及其基本概念——如意向性(I?t)、内在、超越、原素、意向相关项、起源、奠基(Fundierung)、先验性(Tra)、先验观念论(traaleIdealismus)和先验主体性等——的歧义性特征。他认为,先验现象学的这种歧义性特征既非胡塞尔本人表述上的疏忽,也非后人阐释上的差误,而是一种本质的歧义性。它在“实事本身”方面有其根据,因为随着现象学分析的深入,“实事本身”将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是从头开始的(anfangenden)先验现象学的宿命。
在他看来,本能现象学之所以可以被看作一门先验理论。正是由于随着现象学分析的深入,先验主体性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先验主体性的这种歧义性恰恰构成了先验现象学之根本歧义性的最终根源”。因此,先验现象学论题本身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现在,“由现象学分析的深化所开显的先验主体性概念与本能概念产生了一种可理解的含义统一性”。因此,先验现象学澄清先验主体性的任务必然转向系统地分析本能的结构。李南麟的研究表明,为了对本能的结构进行系统分析,胡塞尔必须严格区分两种完全不同的构造现象学的观念,亦即静态现象学和发生现象学,尤其要明确制定出发生现象学的观念和方法。因为在整个先验现象学系统中,发生现象学不仅是系统展开本能现象学的操作平台,而且本能现象学是发生现象学的“原始部分”(Urstück),其任务就是揭示发生性的构造的最低层。他认为,本能现象学的发展不仅符合发生现象学的内在逻辑,而且发生现象学的最终形态由本能现象学规定。因此,本能现象学同时也体现了胡塞尔彻底澄清其发生现象学观念的企图。[13]
3。山口一郎论被动综合与主体间性
在《胡塞尔的被动综合与主体间性》中,山口一郎系统地考察了胡塞尔的被动综合问题及其对于解决主体间性问题的意义。他认为,“交织起来的、具体的预先被给予性”的直观问题是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其后期对于主体间性问题的探讨正是从原则上澄清这种“业已交织在具体的预先被给予性中的主体间关联域”。但是,尽管胡塞尔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并且对这种“业已交织在具体的预先被给予性中的主体间性关联”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却并未将此深入的分析引向系统的结论。例如,《危机》中关于陌生主体之构造的描述仍停留于抽象的原真领域的层次,亦即停留于对那个绝对的、匿名的先验自我进行先验唯我论的自身时间化(Selbstzeitigung)和自身展显的分析层次上。在山口一郎看来,为了澄清这种“业已交织在具体的预先被给予性中的主体间性关联”,我们必须通过对世界具体化之被动综合的深入分析对之进行系统的建构,借此方能在这种系统的建构中探求主体间性的原则性根据。因为只有借助于对被动的、联想的综合的分析,才能澄清这种被动的、主体间的本欲意向性(Triebi?t)的作用机制或规则性,亦即原初的、原联想的、主体间的本欲意向性,内部身体性和外部身体性那种被动的、触发的、联想的统一化和陌生身体性之结对感知等的作用机制或规则性。
这些规则性克服了高级的、自身意识的自我主动性之个体性的唯一性而建立起被动的主体间性。当然,这种被动的主体间性不是主动的主体间性的独立基础,而是从一开始就受到高级的、社会的自我共同体的作用和影响。因此,系统的主体间性理论正是建立在被动的主体间性与主动的主体间性之交互奠基的基础之上,而这在胡塞尔关于主动性和被动性之等级性的思想那里有其根据。山口一郎还具体地将被动综合划分成“天生的本欲意向性”“感知领域的原联想”“触发”“接受”“素朴的把握”“展显”(Explikatioion)七个层次。他认为,“天生的本欲意向性”是一种最原初的被动综合,亦即原触发的或原联想的被动综合,它处于现象学整个构造系统的最低层。通过对“天生的本欲意向性”的发生性分析,我们可以追溯到“前存在”和“作为前构造者的前主体性”。由此,我们不仅可以澄清个体主体性本身的起源,而且可以通过在这种原触发的或原联想的被动综合层次上所发生的联想—结对的综合澄清主体间的同源性(Gleiglichkeit)。在山口一郎看来,只有这种同源性才是胡塞尔整个主体间性理论建构的原根据。[14]
4。阿古雷论未分化的、非时间的开端
在《发生现象学与还原》中,阿古雷的研究论题旨在处理“通达还原的途径”的问题域。“现象学还原”在胡塞尔那里标识着超出生命和科学的自然实证领域的先验性转变方法,而其“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的理想正是建立在对此方法的思义之上。因为哲学的思义者借此方法才能获得绝对的确然性,亦即彻底排除所有的认识前提,从而达到绝对科学所要求的“无前提性”。因此,对此方法的思义标明了胡塞尔现象学的旨归:“由一种真正方法的力量而来的真正生成的真正开端(Anfang)。”(VII,142)阿古雷认为,尽管现象学还原的途径在胡塞尔那里不止一条,比如除了笛卡尔式的途径以外,还有心理学的途径、生活世界的途径等,但是,所有这些途径都包含这样一个基本思想:试图借助一种对经验着世界的意识的批判论证悬搁或还原的动机,悬搁或还原是作为其必然性结果而从这种批判中产生的。也就是说,所有的还原途径都必然以这种动机引发性的批判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