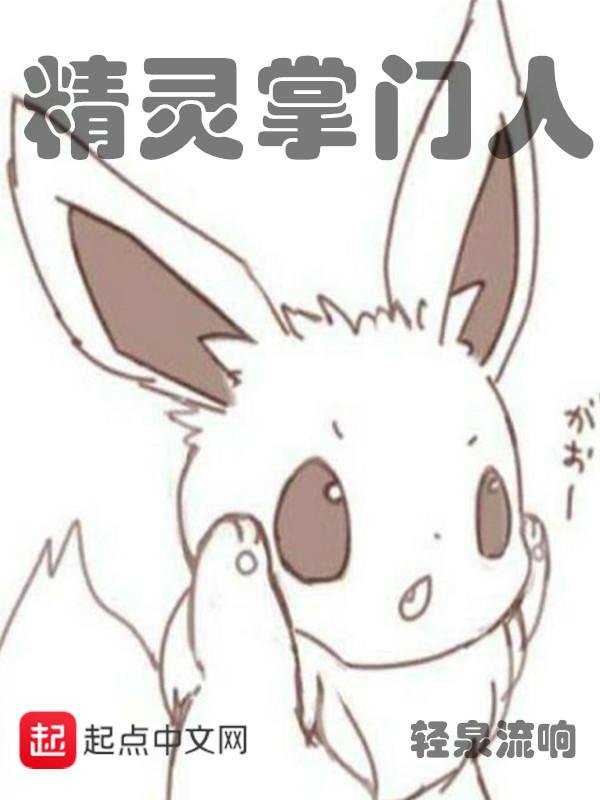奇书网>贞观悍师从教太子逆袭开始全本 > 第193章 太傅东宫不可无太傅(第3页)
第193章 太傅东宫不可无太傅(第3页)
最终,李君羡合上所有卷宗,长长吁出一口气。
他意识到,继续目前这种针对李逸尘个人的、浮于表面的监视,恐怕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他提起笔,在给皇帝的密奏草稿中,如实汇报了近期调查结果。
李逸尘其人家世清白,成长轨迹清晰,入东宫前期表现平庸,近一年来因太子涉足实务而得以展现才能。
于刑狱、文书管理等具体事务上确有聪慧过人之处,行事果决,渐得太子信重。
然,所有查证之事,皆在其职分与能力可解释范围之内。
并未发现其与疑似“高人”者有直接接触或传授高深学问之确凿证据。
两仪殿诛心之论前之独处,亦无实证表明其对太子有决定性影响。
他放下笔,知道这份奏报无法令皇帝完全满意,但这是他基于事实和逻辑所能得出的最负责任的结论。
他下令,对李逸尘的监视级别适当降低,转为常规关注,但调查并未终止,只是转入更耐心、也更茫然的等待。
李君羡知道,除非那个“高人”自己露出马脚。
或者太子身边发生更剧烈的、无法用常理解释的变动,否则,这条线索,很可能就此断在这里。
李君羡的密奏,最终被王德小心翼翼地呈到了李世民的御案上。
李世民挥退了所有侍从,独自在摇曳的烛光下,一字一句地仔细阅看。
他的眉头时而紧锁,时而微展。
奏报的内容详尽而客观,几乎无懈可击。
李逸尘的出身、履历、近期所为,都被梳理得条理分明。
一切都指向一个结论。
此子确有才干,尤其在实务与机变之上,堪称东宫属官中的佼佼者,太子对其信重,并非无因。
然而,所有线索到了“高人”这里,便戛然而止。
李君羡在奏报最后坦言,目前并未发现李逸尘与任何疑似“高人”者有确凿的、超越常规的接触。
李世民缓缓合上奏报,身体向后靠在宽大的御座椅背上,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
这叹息中,有几分释然,更多的却是难以排遣的失落与一丝隐隐的不甘。
他仿佛一拳打在了空处,蓄势待发的力量无处着落,这种空茫感让他极其不适。
难道真如李淳风所言,此等人物乃惊鸿一瞥,非人力可强求?
不甘心啊!
他李世民横扫天下,驾驭群臣,自认无不可掌控之人,无不可洞察之事。
如今却在一个藏头露尾之辈身上,接连受挫。
“罢了……”他喃喃自语。
“既是无迹可寻,强求亦是徒劳。或许,只能如李卿所言,从长计议,静待其变了。”
他的目光无意间扫过御案一角,那里摆放着几份关于已故郑国公魏征身后事宜的最终核定文书。
还有一件事情瞬间涌上心头。
在魏征病重之前,他并非没有动过让魏征兼任太子太傅的念头。
以魏征的刚直不阿、清望隆盛,以及对朝政得失的深刻洞察,正是匡正太子品行、辅佐其明了为君之道的不二人选。
他甚至已经在心里勾勒过如何与魏征深谈,将这副重担交付于他。
可如今,人死如灯灭,一切设想都成了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