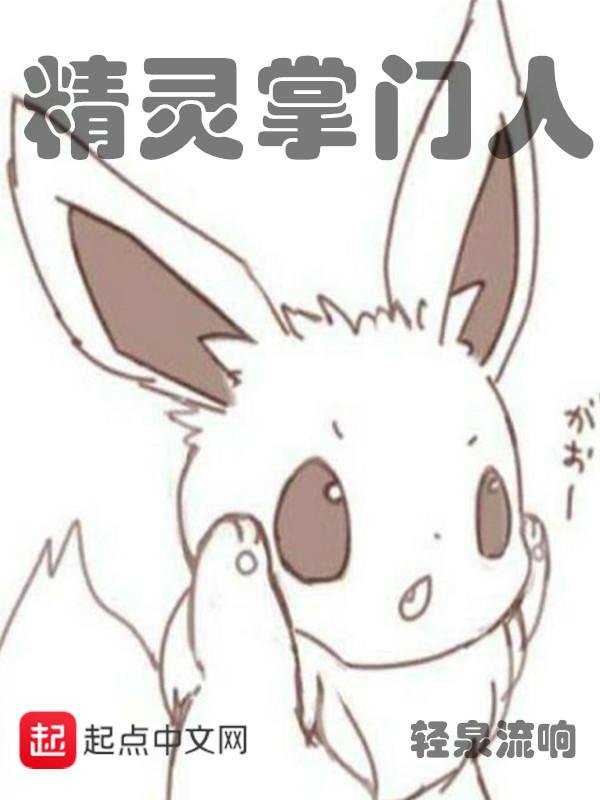奇书网>老庄人生智慧 > 004(第10页)
004(第10页)
孔子说:“他只求自由自在,忘心而忘形,忘形而忘情。在忘情的境界之中,看自己断了一只脚就像失落了一块泥土,超尘绝垢,大家都乐意跟从他。”
庄子讲的寓言故事的主角有三类人:
一类是圣贤神仙,如鸿蒙、黄帝、老子、孔子。这类人是庄子所说的道的传承者,比如广成子传道黄帝,老子传道孔子。
一类是做手工活的劳动者,如匠石、庖丁、灌圃老人。庄子曾为看林人(漆园吏),对同行的关注使他的知识里面充满泥土的智慧与木屑的芬芳。这类人是道的创造者,级别比前者还高。
一类就是残疾人,如本篇讲的王骀,及支离疏、申徒嘉等人。这类人另创一道,或说另显一道,显示了人真实的一面和唯一的出路,级别最高。
庄子如此关注残疾人,当然不是猎奇,而是有他深刻的思考。
一者,天生残疾者揭示了人与人命运的不同,这种先天的不同证明了世界是有多样性的,完美与残缺伴生,幸福与不幸同体。
手脚完好的人看见残肢断体者总是如此震撼,身体是人的全部,身体的先天损坏揭示了人类本身的缺陷。——人不可能完美,总有一两处重大缺陷困扰终生。
庄子曾借孔子之口说:“丘,天之戮民也。”“天之戮民”即上天所残害的人。庄子揭示:说到底,人是上天所生,上天生人又害人,人类头上的星空并非只是那么美丽。
庄子由此又推出:这个世界说到底是不适合人类的。《圣经》上说:“你们若不舍弃这个世界,断不会进天国。”意思同此。并且,庄子发现,这个世界正在生成,绝非成品,而最多是个半成品。
你看,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只是一个未完成之物,我们不可能依靠它真正完成我们的人生。
因此,应与世界共成长,而非借世界而成长。
庄子从残疾人身上还发现了另一个隐秘的宇宙:每个残疾人都不同,他的残疾本身却又似乎有规律可循。而上帝对他们残疾的补偿,又分外丰厚。
二者,后天残疾者是由社会与家庭造成。在庄子生活的年代,打仗就像吃饭,各国杀人者人为制造出了无数的残疾。战争最惨烈时,只有残疾人才能避免上战场,越是重伤,越是得福。
庄子这句话我曾引用在《太学赋》中,后来出诗集《寂》收入此赋时又将这句话删去了。在我,这话过火了。在庄子,这话还太轻。
庄子借孔子之口赞美王骀这个残疾人,用意何在?庄子是赞美王骀的心态好。管他残疾不残疾,反正我是个人。不但如此,世人视人为怪物,我视世人怪物都不如。
鲁有兀者王骀,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常季问于仲尼曰:“王骀,兀者也。从之游者,与夫子中分鲁。立不教,坐不议,虚而往,实而归。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
仲尼曰:“夫子,圣人也。丘也直后而未往耳!丘将以为师,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鲁国,丘将引天下而与从之!”
常季曰:“何谓也?”
仲尼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
庄子这个故事讲王骀为人通达,为当时所重,具有极大的亲和力。
通达之人豪爽,豪爽比智慧更能帮助人渡过困难,豪爽的人善于忘却不快。
这样,王骀看自己断了一只脚就像掉了一块土,又有何惜哉?
不知朋友们注意到没有,残疾人脸上多半带着微笑,并且做人做事神态自若,这是他们经历了一番死亡又战胜死亡后的不平凡的修为。
所谓正常人要向残疾人学习。
其实世上哪有正常人?人人都有病,人人都是“残疾”。不承认这一点就是自欺欺人。
上善若水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老子·八章》
最好的东西是水。水滋养万物,无私奉献而不争,别人都不喜欢的地方它也去,所以水已经接近于道了。
水是粮食的粮食。
五谷杂粮缺少水就不能生长,人同时不能缺少水与五谷杂粮,水对人有双重之恩。它就是我们的本能。
水是稀的,软的,无色透明的,一句话,水性温柔。光线直来直往,水比光更体贴。一个人站在阳光下还会形成阴影,一个人泡在水里则全身都充满温柔的呵护。
阳光浴不及海水浴,海水浴又不及清水浴。清水洗尘,清水出芙蓉,水让人清清爽爽。
水对人的日常生活是必需的,对人的精神生活更是必需。
老子主张“阴柔”,就是取象于水。
水是阴柔的,这种阴柔会聚集巨大能量。洪水也是阴柔的,但它同时也非常阳刚。
老子列举水的美德:一是滋养万物而无私心;二是别人不喜欢去的地方它也去。关于无私心的问题请参考上一章,此处让我们来看水是怎样“处众人之所恶”的。
大地表面凹凸不平,凸处多风比较干净,凹处空气流通不畅,渐渐会聚集为草木腐朽的场所,时间一久就会弥漫令人窒息的气味。水从高处往下流,流经凸处,冲洗之;流经凹处,还是冲洗之。这样泥沙俱下一路过来冲走了所有的脏东西。因为水是流动的,所以它本身永远清洁。万物受其恩赐,也变得清洁。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著名诗篇《菌梦湖岛》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