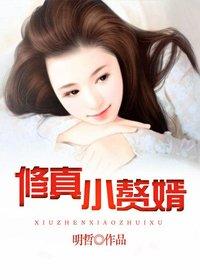奇书网>老庄人生智慧 > 004(第1页)
004(第1页)
004
化人又邀请周穆王同游,所到之处,抬头看不见日月,低头看不见江海。一片光打过来,又一片影子罩上来,周穆王一阵头晕目眩什么也看不见,内心迷乱,感到害怕,让化人带他回去。化人就抱着他回去了,周穆王见面前酒食未撤,一切照旧。
周穆王问:“刚才我从哪儿来的?”
左在的人说:“大王刚才在打盹。”
周穆王不禁怅然若失,三个月后才恢复正常,又去问化人。
化人说:“那是我陪大王神游啊,神游神游神游,神在游动,身子哪用得着?而且你看那次你住的那个地方,跟你住的宫殿有什么区别!那次你玩的那个地方,跟你平时玩的苑圃又有什么区别!大王你经常有空,请暂时就不要怀疑什么啦,只管跟我去,我的变化无穷无尽,不紧不慢之间你就看到了奇妙的事情,那岂能模仿!”
周穆王十分高兴。于是不理国事,不近女色,一个人肆意远游。他乘坐“八骏”拉的宝车,让造父为他驾车,随行的都是驾车高手。他们奔驰千里,来到巨人之国。巨人国王献给他天鹅血让他喝,用牛马流的汗水给他洗脚,又给他配备两名驾车人。周穆王喝完了天鹅血,又动身了,不知跑了多远,终于来到昆仑山。他就睡在昆仑山下,赤水河边。
第二天,周穆王爬上昆仑山,观看黄帝的宫殿,封为神宫,好让后人知道。周穆王就做客西王母的家中,二人会饮在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周穆王唱歌,周穆王也为她唱歌,歌声感人,歌词悲伤。
周穆王又往西行,去看太阳落下的地方,他一天就飞行一万里。周穆王就叹息说:“啊!我一个人没什么美德却如此行乐,后世的人想必会追问我的过错吧!”
周穆王差不多可以称得上是神人了,能享受身体带来的极限欢乐。但也不过一百年后就死了,世人以为他飞升了。
周穆王西游昆仑,约会西王母,爽!
这个“爽”是自己爽,并且是真的爽。周穆王从跟着“化人”神游,到自己真实地远游,他明白了一切必须从真的开始,又要实现真的目的。想得再美,无非意**。
意**并非**境界。
意**是**之殇。
你在网上交一百个网友,虚拟爱情一回又一回,情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哇,都是大美女,有什么意思?我建议你不如找一个身边的女孩更有意思。上网当然是假的,看书也是假的,庄子说书是古人糟粕,现在庄子也是古人了,他的书当然还是糟粕。但有的书糟粕之余,还是有点真东西,可以随便翻翻。我说“随便翻翻”,措辞是很考究的,指不可轻信任何书上的说法。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即此。
你比书更像一本书,你比网络更是网络。
你脚踏大地,胜似仰望天空。
周穆王在去昆仑山之前,昆仑山只是一座传说中的神山,等他亲自站在昆仑山上,才发现自己比传说更传说,因为一件事你亲身经历了才有资格说:“哇,真的很爽。”
于微妙处获利
视之不见名日夷,听之不闻名日希,搏之不得名日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
——《老子·十四章》
“夷”是消除、消失,“希”是寂静,“微”是微茫一片。这句话是说,想看却看不见的东西叫“消失”,想听却听不到的东西叫“寂静”,想捉却捉不到的东西叫“微茫”。这三样东西无法追问,所以把它们混同为一体。
老子此处说的“一”不是指一、二、三的一,而是指道。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而以为天下正。”说的就是道的神奇作用无所不在。
老子说的“非常道”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既表现为普遍存在,又表现为普遍消失。在普遍消失的过程中,事物会普遍产生巨大变化。这种巨大变化并不彰显,而是以微妙状态运行。这不是看得见的巨大,而是微妙的巨大。
万物都在普遍运行与普遍消失,独具慧心慧眼的人当于微妙处获利。
老子说“视之不见名日夷”,他看见了“没有”。
老了说“听之不闻名日希”,他听见了“寂静”。
老子说“搏之不得名日微”,他捉到了“微茫”。
老子说“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他不再追问第一起源,直接与道同一。
许由说老师做天子会天下大乱
尧的老师是许由,许由的老师为啮缺,啮缺的老师为王倪,王倪的老师为被衣。
尧问许由:“我想借王倪来邀请啮缺做天子,缺可以做天子吗?”
许由说:“危险,啮缺智慧超群,办事快捷机敏,天赋过人,但却爱用人为的心智去取代自然规律,他做天子必定凭借人为摒弃自然,尊崇才智而谋急用,必为琐事所役使,目不暇接地跟外物应接,他可做百姓的长官而不可做一国的君主,治理天下必定天下大乱。”
尧之师日许由,许由之师日啮缺,啮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尧问于许由曰:“啮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
许由曰:“殆哉,圾乎天下:啮缺之为人也,聪明睿知,给数以敏,其性过人,而又乃以人受天。被审乎禁过,而不知过之所由生。与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无天。夫何足以配天乎?治,乱之率也,北面之祸也,南面之赋也。”
庄子这个故事讲做人不要搞人,做事不要搞事,才能成。搞人者人必搞之,搞事者必会天下大乱。
许由说:“治,乱之率也”,很多事情表面被你收拾得可以,其实隐藏大祸根。大祸根的存在是因为有人包藏祸心,有人包藏祸心是因为你先搞事。你不先搞事,就没人能搞你。
借力不如卸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