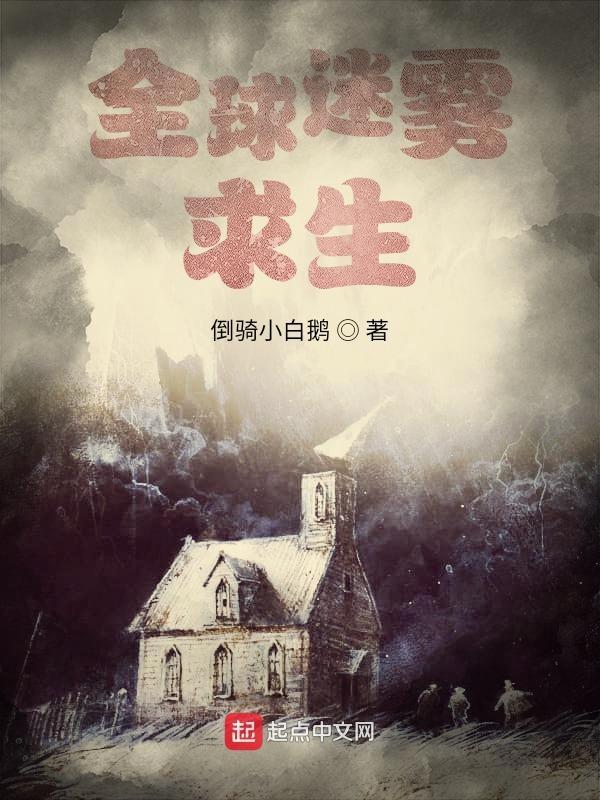奇书网>砚寒清诗号 > 薪火相传山河无恙(第1页)
薪火相传山河无恙(第1页)
鸣沙关的秋来得迅疾,一夜霜风过后,城外的胡杨林便染成了漫天金红。谢惊寒踏着晨霜登上城头时,恰逢一队新兵正在操练,整齐的呐喊声穿透薄雾,与远处互市的驼铃声交织在一起,成了北疆最安稳的韵律。他鬓边的白发已近半,眼角的皱纹被晨光刻得愈发清晰,唯有眼神依旧如寒锋般锐利,扫过城墙下的每一寸土地。
“将军,沈相的密函与物资一同到了。”秦风快步走来,手中捧着一个紫檀木匣,“这次送来的不仅有新药,还有沈相亲手校注的《孙子兵法》,说是给新兵们做教材。另外,户部拨的冬衣与粮草也已入库,比往年多了三成。”
谢惊寒接过木匣,指尖触到微凉的紫檀木,心中泛起暖意。打开匣子,除了密函与兵书,还有一个小巧的瓷瓶,瓶身上贴着纸条,是沈砚辞熟悉的字迹:“此乃润肺药膏,边关风沙大,每日涂抹,可护喉肺。新兵操练辛苦,勿要过于严苛,需劳逸结合。”
密函中的内容则多了几分凝重:“京城近日有流言,称北狄汗王拓跋宏染疾,其弟拓跋烈已暗中联络旧部,似有夺权之意。江南水患刚平,国库虽足,但需预留赈灾之资,边防物资暂难再加拨。你需密切关注北狄动向,同时安抚军中将士,尤其是老兵,近日有几人上书请求归乡,需妥善安置,勿寒了军心。”
谢惊寒将密函贴身收好,转头对秦风道:“传令下去,今日操练结束后,召集所有老兵到中军帐议事。另外,让医官将沈相送来的药膏分下去,每日操练后务必让将士们涂抹。”
“是!”秦风应道,犹豫了一下又道,“将军,那些老兵大多跟随您多年,从黑石峡打到鸣沙关,如今年纪大了,思乡心切也情有可原。只是他们一走,军中的骨干力量怕是会受影响。”
“我知道。”谢惊寒望着远方的胡杨林,语气沉缓,“他们为家国拼了半辈子,该享享太平了。归乡者,按最高规格发放抚恤金,再送些边关的特产,让他们风风光光回家;愿意留下的,编入教导队,负责训练新兵,待遇加倍。”
午时过后,中军帐内坐满了老兵。他们个个身上带着伤疤,有的断了胳膊,有的瘸了腿,却依旧坐得笔直,眼神中透着军人的刚毅。谢惊寒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心中百感交集:“兄弟们,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守了这么多年边关,辛苦了。如今太平了,想回家的,我绝不阻拦,朝廷的抚恤会一分不少;想留下的,我谢惊寒依旧与你们并肩。”
帐内一片寂静,过了许久,一名断了左臂的老兵站起身,声音沙哑却坚定:“将军,我们不走!跟着您,守着这鸣沙关,心里踏实。再说,这些新兵蛋子还没练出来,我们怎能放心离去?”
“对!我们不走!”老兵们纷纷附和,“只要将军还在,我们就还在!”
谢惊寒眼眶微热,抬手示意大家安静:“好!既然兄弟们愿意留下,那我们就一起守护这太平!从今日起,你们便是教导队的教官,把你们的本事都教给新兵,让他们成为新的边关柱石!”
老兵们齐声应和,声音震得帐顶的尘土簌簌落下。谢惊寒知道,这便是军人的传承,只要薪火不息,边防便永远固若金汤。
与此同时,京城的相府书房内,沈砚辞正对着一份奏折眉头紧锁。奏折是江南官员递来的,称水患过后,流民安置需要大量资金,请求削减边防开支,将部分军饷调拨给地方。沈砚辞放下奏折,指尖敲击着案几,心中了然——这又是江南士族在背后推动,他们只知地方疾苦,却不知边境的暗流涌动。
“大人,北狄传来消息,拓跋宏的病情加重,拓跋烈已掌控了北狄的部分兵权,近日频繁在边境调动兵力,还派人联络了漠北的几个小部落。”林墨轻声禀报。
沈砚辞眼神一沉:“看来,拓跋烈是要动手了。”他起身走到舆图前,指尖落在鸣沙关的位置,“谢将军那边,怕是又要面临考验了。”他转头对林墨道,“立刻拟旨,驳回江南官员的奏折,边防开支不仅不能减,还要再加拨两成,用于加固城防与更新军备。另外,派使者前往北狄,探望拓跋宏,同时密切关注拓跋烈的动向。”
“是。”林墨应道,又补充道,“大人,还有一件事,太子殿下近日多次提及,想亲自前往边关慰问将士,历练一番。”
沈砚辞眉头微蹙,太子年幼,性子急躁,从未经历过战火,此时前往边关,怕是会添乱。但他也知道,太子需要历练,才能将来扛起江山社稷的重任。“准了。”沈砚辞沉吟片刻道,“但必须派五千禁军护送,且不得干预军中事务,一切听从谢将军安排。另外,我亲自写一封信给谢将军,让他多费心。”
沈砚辞的书信很快送到了鸣沙关。谢惊寒拆开一看,除了告知太子要来的消息,还附了一张北狄的兵力部署图,上面用红笔圈出了拓跋烈的驻军位置。信末写道:“太子年幼,需多加照看,勿让他涉险。拓跋烈虽勇,却无谋略,只需严守边界,静观其变,待其内部生乱,便可不战而胜。我已令西域都护府暗中牵制,你无需担忧后方。”
谢惊寒看完书信,心中安定了不少。他立刻召集将领们议事,部署太子到来后的安保与边防事宜:“太子驾到,安保是重中之重,秦风,你率三千禁军负责护卫,不得有任何差池。赵毅,你率两万将士,加强边境的巡逻,若遇北狄士兵,只许防守,不许主动出击。”
“是!”将领们齐声应道。
三日后,太子的仪仗抵达鸣沙关。太子身着锦袍,意气风发,刚到关城,便迫不及待地想要登上城头,看看边境的景象。谢惊寒亲自陪同,耐心地为他讲解边关的防御工事与过往的战事。
“谢将军,如今北狄这般安分,为何还要保留这么多兵力?”太子好奇地问道。
谢惊寒指着远方的边境线,语气沉缓:“殿下,太平就像一层薄冰,看似坚固,实则脆弱。北狄的拓跋烈野心勃勃,一直在暗中积蓄力量,若我们放松警惕,削减兵力,他便会趁机南下,到时候,这太平日子便会化为泡影。这些将士,便是守护这层薄冰的基石。”
太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目光落在城墙上那些深嵌的箭头的,心中泛起一丝敬畏。
就在太子抵达鸣沙关的第三日,边境传来急报:拓跋烈率领三万骑兵,突袭了北狄汗王拓跋宏的营帐,夺取了汗位,随即下令,兵分三路,向鸣沙关进发!
“来得正好!”谢惊寒眼中闪过一丝锐利,“传我命令,秦风,你率五千将士,护送太子返回京城!赵毅,你率一万将士,坚守西城门!其余将士,随我登上城头,迎击敌军!”
“将军,我不走!”太子高声道,“我要留下来,与将士们一同守城!”
谢惊寒眉头一皱:“殿下,守城乃凶险之事,你身系国本,不可涉险!立刻返回京城,这是军令!”
太子见谢惊寒态度坚决,只得不甘地答应:“好吧!但谢将军一定要保重,我在京城等你凯旋的消息!”
送走太子后,谢惊寒立刻登上城头。北狄的骑兵已经出现在远方的地平线,黑压压的一片,如同潮水般向鸣沙关涌来。
“放箭!”谢惊寒一声令下,城墙上的箭矢如雨点般射下,北狄骑兵纷纷倒地。但拓跋烈的骑兵来势汹汹,很快便冲到了城下,云梯被架上城墙,士兵们疯狂地向上攀爬。
“扔滚石!倒火油!”谢惊寒高声喝道,巨大的滚石从城墙上滚落,火油坛被点燃后扔下去,瞬间燃起熊熊大火,将北狄士兵的冲锋路线变成了一片火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