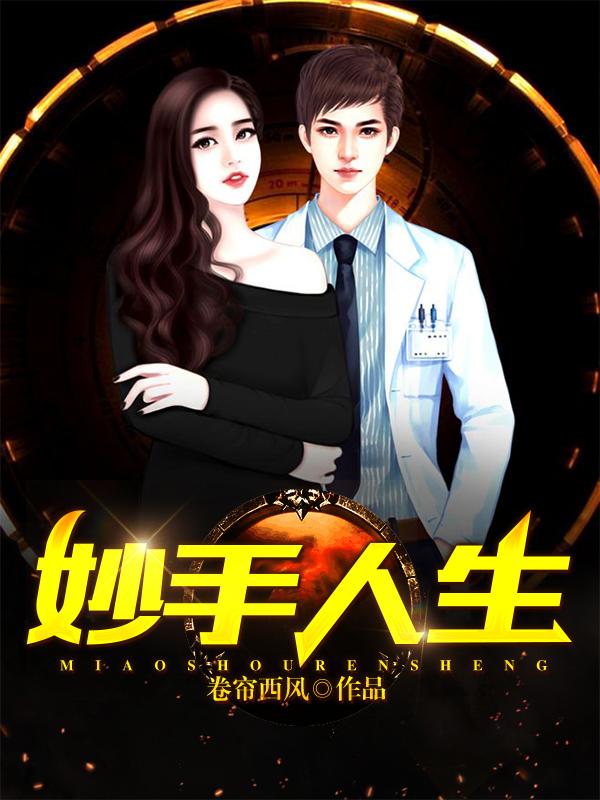奇书网>中外史学观点 > 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1(第1页)
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1(第1页)
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1]
一、为什么要提出“反思”的问题
提出中国史学上的“反思”问题,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偶然因素:从史学发展来说,也可以看作一个必然趋势。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次史学研讨会上,有青年朋友提出这样的论点:中国史学长于记述,是“记述史学”,而缺乏理论,甚至没有理论。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我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读研究生时,是攻读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因此难以接受这样的观点。如此发达的中国史学,怎么会没有理论呢?但是,要说中国史学有自己的理论,那么这个理论的内容是什么,有什么特点?这些,我在当时还不能做出具体的回答。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用“反思”这个思路来反映中国史学上的几次重要的进展,或许可以勾勒出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来,尤其是史学理论方面的发展规律。基于这些想法,我提出了中国史学上五次反思的见解。这就是我说的偶然机会的大致情况。
为什么说中国史学上的反思又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呢?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第一,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了一阵子,到了50年代就变得沉寂了。60年代初,在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鼓舞下,出现了再次活跃的势头,但不久“**”开始,又沉寂下去了。“**”结束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开始出现生机。可以说,几十年中,断断续续,时起时伏,人们在这个领域里,还没有充分的研究和足够的积累来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第二,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大量的西方史学的理论著作被引进国门,如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卡尔的《什么是历史?》、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等,受到中国史学界的热切关注。相比之下,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学在理论上似乎就显得“苍白”无力了。第三,人们在“熟读”西方史学的理论著作时,不由自主地以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的理论模式来看待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来衡量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元素。当然,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方法,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产生的,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是正确的。正是这几个方面原因所形成的“合力”,推动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探究,从而做出自己的说明。这些,就是史学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二、中国史学上五次反思的背景和特点
中国史学上的反思,是在中国史学有了很大发展和很多积累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的。两汉时期,司马迁和班固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当时复杂、动**的政治形势和门阀地主居于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史学出现了多途发展的局面,史书的内容更加丰富了,历史著作的数量和种类都大大增多了。到了唐初贞观年间,设馆修史又取得了重大成就,先后撰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晋书》,以及《南史》《北史》,当朝实录、国史也在撰述中,还有杂史、家传、传记、谱牒等。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史学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另一方面史学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教训和问题。这种客观存在,激发了史学家的思考,加之现实的历史撰述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如唐代史家刘知幾所说:“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2]刘知幾认为,当时史馆“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以至于把修史活动的种种障碍概括为“五不可”[3],这使史学家对于这种思考达到了必须做出总结和说明的程度。于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就落在了曾经在武则天、唐中宗时期担任史官的刘知幾身上。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的趋势来说,刘知幾是开中国史学反思之先河的史学家。
刘知幾对中国史学的反思,是中国史学上的第一次反思。这次反思的主要特点,是产生了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史通》这部书,对唐初以前的史学从历史编纂上做了全面的总结,涉及史学家的历史撰述态度和历史撰述方法的许多问题,既概括了成功的经验,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思路开阔、语言犀利,是《史通》的鲜明风格。
中国史学上的第二次反思出现于清代前期。其学术背景是,在刘知幾之后史学经历了中晚唐、两宋、辽金、元明和清代前期的发展,成果积累和思想积累更加丰富,提出的问题更加深刻,又有《史通》作为反思的前驱,于是出现了章学诚对史学的反思。这次反思的主要特点,是产生了一部有系统、有深度的史学理论著作《文史通义》。《文史通义》讨论文与史的理论问题,而以讨论史学的理论问题为主。这部著作继承了刘知幾的自觉反思的批判精神而又发展了这种精神,它主要是从史学家的历史撰述思想方面对以往史学做了总结,并着重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见解的认识,从而把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认识提高到理论认识的层面。可以认为,《文史通义》一书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所达到的高峰。
中国史学上的第三次反思出现在清代末年,其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是,清代后期从1840年开始,中国备受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到了20世纪初,更是出现了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与此同时,一方面是史学家们出于救亡图存的目的,加强了对边疆史地和外国史地的研究和撰述;另一方面是一批进步的思想家引进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作为改良政治的思想武器。这种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激发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审视和批判,于是出现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史界革命”的主张,形成了第三次反思。这次反思的主要特点,是产生了以梁启超所撰写的《新史学》为标志的“史界革命”的“宣言”。《新史学》以历史进化论为武器,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激烈的批评,提出革除“君史”、撰写“民史”的主张,强调历史撰述应写出人群进化的过程及其公理公例,否则不是好的史学家。以《新史学》为代表的史学思潮,在20世纪的前三四十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史学上的第四次反思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它同第三次反思有紧密的交叉,但它们在性质上却有明显的区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变动剧烈,历史步伐也大大加快了。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王朝统治的结束,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史学家们进一步开阔了视野,理论思考进一步加深,一部分史学家、理论家、社会活动家的世界观、历史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来思考历史问题和史学问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李守常(李大钊)于1924年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此书参考了当代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阐述了历史学的性质、历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以及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等重大问题,从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生、发展的基础,同时突出地反映了近代学科建设的自觉意识,成为中国史学走上科学发展道路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史学上的第五次反思出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政治形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意识形态领域则是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其时代特征。于是,在经历了“**”动乱之后,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从“万马齐喑”的状态一下子活跃起来,几乎每一个学科或学术领域都在思考自身的发展道路。一般来说,思考的核心问题有两个重点:一是“四人帮”对这个学科或学术领域的干扰和破坏,二是这个学科或学术领域在“**”前17年中的经验、教训。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重点,前者是对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的清算,后者主要是关于学术上的正确与偏颇的检讨。这样一个严肃的同时也是生动活泼的历史局面,是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因为它唤起了人们的自尊、真诚、信念和热情。中国史学上的第五次反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这次反思有几个特点。第一,它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可以看作学术群体的反思;第二,它以重新学习和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目标;第三,它要回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许多史学家如侯外庐、尹达、刘大年、白寿彝、尚钺等老一辈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次反思的重大意义,是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今史学多元发展的形势下,继续居于史学的主流地位,并创造出新的成就。
以上是讲中国史学上五次反思的梗概,下面我们着重讲这五次反思的标志性著作及其理论意义。
三、中国史学上五次反思的理论意义
中国史学上的这五次反思,都以其突出的理论成就,在中国史学发展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一)关于《史通》的理论成就
刘知幾《史通》一书是中国古代史学中第一部以史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理论著作。这部史学理论著作贯穿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应当被看作一部史学批评著作。《史通》前十卷为“内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着重阐述了有关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辑、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则,以及史学功用等,其中以批评纪传体史书的各种体例居多。后十篇为“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并略申作者对历史的见解。刘知幾撰《史通》的旨趣,是“商榷史篇”,“辨其指归”,而且“多讥往哲,喜述前非”。[4]他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的理论。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六点。
第一,关于史书内容的范围。《书事》篇引用荀悦“立典有五志”的论点,即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为史书内容的范围。又引用于宝对“五志”的阐释,即体国经野之言、用兵征伐之权、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文诰专对之辞、才力技艺殊异等。刘知幾认为:“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同时,他又认为,要使书事没有“遗恨”,还必须增加“三科”,即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五志”加上“三科”,“则史氏所载,庶几无缺”[5]。这里所说的史书内容范围的问题,实质上已触及史家主观意识如何更全面地反映客观历史的问题了。
第二,关于撰史原则。刘知幾认为,博闻、善择是撰史者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如《史通·采撰》篇一方面主张要慎于“史文有阙”的问题,一方面强调“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刘知幾肯定魏晋南北朝以来史籍繁富,皆“寸有所长,实广见闻”,但也产生了“苟出异端,虚益新事”的弊病。他告诫撰史之人:“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谜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杂述》篇还说:“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慎于采撰,根本的问题是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善于辨别真伪虚实的能力,这是刘知幾论撰史原则的核心。
第三,关于史书的体裁、体例。《史通》以精辟论述史书的体裁、体例而享有盛誉,《序例》篇说:“失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这是指史书体例本是史家反映历史见解的表现形式。刘知幾推崇《春秋》《左传》、范晔《后汉书》、萧子显《南齐书》的体例思想;而他本人的新贡献是提出了“诸史之作,不恒厥体”的理论,并通过《六家》《二体》《杂述》等篇,对史书体裁做了总体上的把握,并详尽地论述了纪传体史书的各种体例。
第四,关于史书的文字表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史通·叙事》篇较早从史学的审美意识提出了这个问题,刘知幾写道:“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又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他认为“简要”是“美”与“工”的基本要求,同时主张“用晦”,认为“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诲之道也”。他还提出史书文字表述应采用“当时口语”,“从实而书”,以不失“天然”。同时,他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体蒹赋颂,词类俳优”的文风,反对“文非文,史非史”的文字表述。
第五,关于史家作史的道德规范《直书》《曲笔》两篇提出了“直书”“曲笔”两个范畴,并做了理论上的说明,认为从本质上看,这是“君子之德”和“小人之道”在史学上的反映。从刘知幾所揭示出来的“直书”与“曲笔”对立的种种情况,说明它们的出现不仅有撰史者个人德行的迥异,也有社会的原因,如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对峙、等级的界限、民族的隔阂等。刘知幾认为,直书才有“实录”,曲笔导致“诬书”,它们的对立从根本上决定了史书的价值和命运。
第六,关于史学的功用。《史通》一书讲到史学功用的地方很多,如《直书》《曲笔》《自叙》《史官建置》等,而《辨职》篇尤为集中,提出了史学功用的三种情况:“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刘知幾对这三种情况的划分,明确地显示出他的史学价值观。更重要的是,他在《史官建置》篇中阐述了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道理:由于“史官不绝,竹帛长存”,人们才能了解历史,认识历史,看清善恶是非,才能“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内自省”,由此可知“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这就道出了史学功用之广泛的和重要的社会意义。
以上这几个方面,是从史学工作的内在逻辑联系分析了《史通》一书所提出来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尽管《史通》本身不是按照这个体系来编次的,但这个体系却包含在全书当中。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新阶段。同这个理论体系相表里的,是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说。他提出史才、史学、史识即“史才三长”这三个范畴,阐释了它们各自的内涵和相互间的联系,[6]是史学家自我意识的新发展、精神境界新的升华。从上引刘知幾强调“君子之德”来看,他的“史才三长”说是包含了为史之德的。从整体来看,刘知幾在史学理论发展上所达到的高度,的确是前无古人的,《史通》写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这在世界史学史上,也是无与伦比的。
(二)关于《文史通义》的理论成就
从理论上全面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的史家,是清代章学诚。他所著《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在史学理论上有重大建树,其中也有论及历史理论的名篇[7]。章学诚在史学理论方面的新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继承、发展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论点[8],这是继《隋书·经籍志》确立史学从经学中分离出来的经史分途格局之后,进而以史学来说明经书的新认识,进一步扩大和丰富了史学的内涵。第二,提出了“史法”和“史意”的区别,而重于“史意”的探索。他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9]简要地说,“史法”是探讨历史撰述的形式和内容,“史意”是探讨历史撰述的思想。刘、章的联系和区别,继承和发展,即在于此。章学诚用“不相入也”来表明二者的关系,显然是过于绝对了。第三,提出了“撰述”与“记注”的区别,以“圆神”“方智”为史学的两大宗门。他说:“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10]“记注”与“撰述”,亦可从“史法”与“史意”中得到说明。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的这一说法,是从历史的主体即人自身的自觉要求来看待史学的社会功用的,这就是:人们要总结历史经验即“欲往事之不忘”而必有“记注”,人们对未来的期待即“欲来者之兴起”而需要“撰述”,这是知识和思想的结合。这跟刘知幾讲史学的社会功用是从史学的主体即史官着眼,有所不同。第四,提出了历史编纂上“神奇”与“臭腐”相互转化、发展的辩证法则。他认为:“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他从“《尚书》园而神”一直讲到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出现,并说:“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11]他的这些论述,揭示了中国古代史书体裁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但这种发展变化也是同社会的要求和史家的创造分不开的。第五,总结了通史撰述的品类及其所具有的六便、二长、三弊,建立了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史编纂理论。[12]第六,提出了“史德—心术”论,发展了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说,把关于史家自身修养的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13]第七,提出了“临文必敬”“论古必恕”的文史批评的方法论原则。他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14]这是关于知人论世的精辟见解。第八,总结了史书表述在审美方面的理论,提出了“闳中肆外,言以声其心之所得”“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15]等文字表述的原则。第九,提倡“别识心裁”“独断之学”的继承、创新精神,强调在认识前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此谓之“心裁别识,家学具存”。[16]
章学诚的《校雠通义》是一部系统的历史文献学的理论著作,其中《原道》篇结合社会发展总结了历史文献发展的规律,《宗刘》以下诸篇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总结了古代历史文献的成就。
总的来看,章学诚在总结中国古代史学得失的过程中,继承、发展了前人的一些重要见解,其主旨多在于他说的“史意”,极具启发性,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高峰和终结的标志。
(三)关于梁启超《新史学》的理论成就
1902年,梁启超继上一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又在《新民丛报》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的构想,后者着力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这两篇文章,是近代史学家批判古代史学,为“新史学”开辟道路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