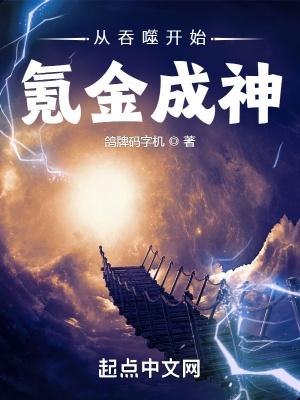奇书网>当代西方哲学家 > 论指称1(第2页)
论指称1(第2页)
(3)没有任何既是法国国王又不贤明的某物。
容易看出,罗素是如何作出这种分析的,以及这种分析又是如何使他能对我们开始时所提出的问题(即语句S在没有法国国王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是有意义的)作出回答的。显然,罗素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来作出这种分析的,即自问道:如果我们说凡是任何说出语句S的人都作出了一个真实论断,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并且,上述语句(1)—(3)的确描述了这种情形,它们至少是任何一个人通过说出语句S而作出一个真实论断的三个必要条件。这一点看来确实是相当明显的,我并不希望对此加以反驳。但是,正如我希望加以说明的那样,这种说法与下述这种说法完全不是一回事,即认为罗素对语句S的使用作出了正确的解释,这种说法甚至也完全不同于下述这种说法,即认为罗素作出了尽管还不完备、但就目前情况来说是正确的一种解释;并且,这种说法与下述这种说法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即认为,所提供的翻译模型,对于所有(或对于任何一个)以具有“如此这般”形式的词组起首的单称语句来说,都是正确的模型。
也易于看出,甚至在没有法国国王的情况下,这种分析如何使得罗素能够对于语句S何以是有意义的问题作出回答。这是由于,倘若罗素的这种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任何今天说出语句S的人都会同时对其中之一(即有一个法国国王)为假的三个命题作出断定;既然这三个命题的合取为假(因为其中之一为假),因而,语句“法国国王是贤明的”作为三个命题的一个整体就是一个有意义的假论断。因此,前面所说的那两种对虚存实体的错误论证没有一种适用于这样的论断。
二
为了证明罗素对于问题的解决是错误的,为了提出一个正确的解决办法,我现在打算作出某些区别,作为迈向上述目标的一步。为了这一目的,我在本节的其余部分要提到一种具有唯一指称用法的语词,我把它简称为“语词”;还要提到一种以上述那种语词起首的语句,我把它简称为“语句”。我将作出的那些区别有些粗率,并且,毋庸置疑,会出现一些有待改进的困难情况。但我认为,所作出的这些区别适用于我的目的。下述这些说法之间存在着区别:
(A1)语句(sentence),
(A2)语句的使用(use),
(A3)语句的表达(utterance),
并且,相应地,在下述这些说法之间也存在着区别:
(B1)语词(expression),
(B2)语词的使用,
(B3)语词的表达。
再考虑“法国国王是贤明的”这一语句。易于想象,这个语句可能是在进入了17世纪以后、继承了法国王位的各位君主当政期间的不同时间说出的;同样也易于想象,这个语句是在法国不存在君主制之后的时期说出的。要注意,我谈论在这一期间的不同时间说出“该语句”或“这个语句”,这一点是很自然的;或者换句话来说,谈论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场合说出的同一个语句,这是自然的和正确的。正是在谈论处于所有这些不同的场合所说出的同一个语句是正确的这样一种含义上,我打算使用(A1)“语句”这一表达式。可是,在这个语句的不同的使用场合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别。例如,如果一个人在路易十四当政时期说出这个语句,而另一个人在路易十五当政时期说出这个语句,那么,认为(假定)这两个人分别谈到不同的人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可以认为,第一个人在使用这个语句时作出了一个真论断,而第二个人在使用这同一个语句时作出了一个假论断。另一方面,如果这两个不同的人在路易十四当政时期同时说出这个语句(例如,一个人写出这个语句,另一个人讲出它),那么,认为(假定)他们两人都在谈论着同一个人会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且,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两人在使用这个语句时,必定是要么都作出了一个真论断,要么都作出了一个假论断。这就表明了我通过使用语句所意谓的东西。如果在说出这个语句的两个人中,一个人是在路易十五当政时期,另一个人是在路易十四当政时期说出这个语句,那么,每个人都对同一语句作了不同的使用;而在路易十四当政时期同时说出这个语句的人则对这同一语句作了相同的使用。[4]无论是在这个语句的情况下,还是在其他许多语句的情况下,显然,我们都不可能谈到语句本身的真或假,而只能谈到使用语句作了一个真论断或假论断,或者说(如果这种说法更可取的话)使用语句表示了一个真命题或假命题,并且,同样明显的是,我们不能说语句论述某一个特定的人物(因为,同一个语句在不同时间可以用来谈论完全不同的特定人物),而只能说对语句进行一种使用来谈论某个特定人物。最后,如果我说,尽管在路易十四当政时期同时说出这个语句的两个人对这个语句作了相同的使用,但他们还是对同一语句作出了两种不同的表达,那么,就会使我通过语句的表达所意谓的东西充分地清晰起来。
如果我们现在考虑的不是“法国国王是贤明的”这一整个语句,而只考虑它的一部分,即“法国国王”这一语句,那么,我们显然能在(1)语词、(2)语词的使用和(3)语词的表达这三者之间作出类似的(尽管不是等同的)区别。语句之间的这三种区别和语词之间的这三种区别是不等同的;既然,一般来说,只有语句能用来表述真命题或假命题,因而,我们显然不可能正确无误地谈到被用来表述一个真命题或假命题的“法国国王”这一语词;类似地,只有使用语句,而不是使用孤立的语词,你才能谈论某一个特定人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改换成这样的说法:在你使用语句谈论某个特定人物的过程中,你使用语词去提到(mentioo)某个特定人物。但是,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并在其他很多种情况下,正如不能说语句本身有什么真或假,语词(B1)本身也谈不上提到或指称什么东西。正如同一语句能用来作出具有不同真值的陈述,同一语词也能具有不同的指称使用。“提到”或“指称”并不是语词本身所做的事情,而是人们能够用语词去做的事情。提到某个东西或指称某个东西,是语词的使用的特征,正如“论述”某个东西与或真或假是语句的使用的特征。
一个与之不同的例子也许会有助于我们把这些区别搞得更清楚。考虑具有唯一指称用法的一个语词,即“我”这个语词的另一种情况;并考虑“我感到热”这一语句。这同一语句可以被无数的人所使用,但是,任何两个不同的人在逻辑上都不可能对这个语句做出相同的使用:或者说(如果这是更可取的说法的话)用它来表述相同的命题。“我”这个语词可能由(且仅仅由)无数人当中的任何一个正确地用来指称他本人。说出这一点也就是说出了关于“我”这个语词的事情:在某种含义上,也就是给出了这个语词的意义。这是关于语词本身所能说出的那种事情。但是,关于“我”这个语词本身,说它指称着某个特定人物却是毫无意义的。说它指称着某个特定人物这一点,仅仅是关于语词的某个特定使用所能说出的那种事情。
假设我用“类型”(type)这个字眼作为“语句或语词”的缩略语。那么,我并不是如同说“存在有船只,并且存在有鞋,并且存在有封蜡”那样在说:存在有语句和语词(类型),并且存在有它们的使用,并且存在有它们的表达。我是说,我们不可能就类型、类型的使用和类型的表达这三者说出同样的事情。而事实在于,我们的确在谈论类型;事实还在于,由于没有注意到,在我们关于这些类型本身所能说出的事情与我们仅仅关于类型的使用所能说出的事情之间存在着差别,因而就易于出现混淆。当我们正在谈论语句和语词的使用时,我们就易于想象我们正在谈论的是语句本身和语词本身。
造成这种混淆,这就是罗素所做的事情。一般来讲,正是在这方面,我不同意罗素的观点。意义(至少就一种重要的含义来说)是语句或语词的一种功能;而提到和指称,真或假则是语句的使用或语词的使用的功能。提出语词的意义(就我使用这个词的含义来说),就是为了把这个语词使用于指称或者提到一个特定对象或特定的人而提出一些一般的指导;提出语句的意义,就是为了把这个语句使用于构成某些真的或假的论断而提出一些一般的指导。这并未谈论语句的使用或语词的使用的任何特定场合。语词的意义不可能等同于该语词在某一特定场合下所指称的对象。语句的意义不可能等同于该语句在某一特定场合下所作出的论断。因为,谈论一个语词或语句的意义,不是谈论它在特定场合下的使用,而是谈论在所有场合下正确地把它用于指称或者断定某某事物时所遵循的那些规则、习惯和约定,因此,一个语句或语词是否有意义的问题,与在某一特定场合下所说出的该语句是否在那个场合下正被用来作出一个或真或假的论断的问题,或与该语词是否在那个特定场合下正被用来指称或提到某物的问题毫无关系。
罗素所犯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以为指称或提到(如果它们的确出现的话)必定是意义。他没有把B1和B2区别开来,而是在某一特定语境中把语词同它们的使用混淆起来了,把语词的意义同提到或指称混淆起来了。如果我谈论我的手帕,我或许能从我的口袋里掏出我正在指称的对象,但却不能从我的口袋里掏出“我的手帕”这个语词的意义。因为罗素把意义同指称混淆了,因此,他认为,如果存在着任何具有唯一指称用法的语词,这些语词是它们在表面上看来所是的东西(即逻辑主词),而不是伪装着的其他东西,那么,这些语词的意义就必定是这些语词被用来指称的特定对象。由此就产生了令人困惑的关于逻辑专名的神话。但是,如果有人问我“这个”(罗素为说明这种情况最喜欢用的一个词)这一语词的意义,我不会递给他我刚刚用该语词所指称的那个对象,我还会对他说,每当这个语词使用时,它的意义就会发生变化。我也不会递给他该语词曾用来或可能用来指称的所有对象。我会解释和举例说明支配该语词使用的那些约定,这正是提出了该语词的意义。它与提出(在“提出”的任一含义上)该语词所指称的对象完全不同,因为该语词本身并没有指称任何东西;尽管该语词在不同场合下能被用来指称无数的东西。事实上,在英语中,“意谓”(mean)这个词有这样的含义:在这种含义上,这个词的确接近于“表示(iioo)”,例如,当某人(不愉快地)说“我意谓的是你”时,或当我指点着说“那就是我所意谓的人”时。但是,我所意谓的人与我谈到这个人时所使用的语词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在“意谓”的这种特殊含义上,是人们在意谓,而不是语词在意谓。虽然人们使用语词去指称特定的事物,但是,一个语词的意义并不是该语词可以被正确地用来指称的一套事物或单个的事物:意义是为把语词使用于指称中的一套规则、习惯和约定。
在语句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甚至更明显。每个人都知道,“桌子上铺满了书”这个语句是有意义的,并且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含义是什么。但是,如果我问:“该语句是论述什么对象的?”那么,我就是在问一个荒谬的问题——一个关于该语句本身所不可能问到的、而仅仅关于该语句的某种使用才可能问到的问题。而在对该语句进行使用的情况下,该语句并没被用来谈论某个东西,它仅仅被当做一个例句。当知道语句的含义时,你也就知道了该语句是如何被正确地用来谈论事物的:因此,知道语句的意义与知道谈论某个东西的语句的任何特定使用毫无关系。同样,如果我问:“该语句是真还是假?”那么,我也是在问一个荒谬的问题,即使我补充说:“既然该语句是有意义的,因此它或是真的或是假的”,它仍然是荒谬的。这个问题之所以荒谬,是因为,相应于该语句本身并非论述(about)某个对象,它本身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当然,该语句是有意义的这个事实等同于下述事实,它能够被正确地用来谈论某物;在这样使用它时,某人会作出一个真论断或假论断。并且,我要进而指出,只有当使用语句的人的确在谈论某个东西时,语句才会被用来作出一个真论断或假论断。如果某人说出语句时并没谈论什么事物,那么,他对这个语句的使用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使用,而是一个虚假的使用或伪的使用:他既不是在作出一个真论断,也不是在作出一个假论断,尽管他也许认为他是在作出这样的论断。这就为正确地回答摹状词理论注定回答错了的难题指出了道路。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语句是否有意义的问题完全独立于关于该语句的特定使用所能提出的问题,即,它是真实的使用还是虚假的使用的问题,它是正被用来谈论某个东西,还是正被用来冒充做什么事或正被用作哲学中的例句。语句是否有意义的问题,也就是是否存在着这样的语言习惯、约定或规则使得语句在逻辑上能被用来谈论某个东西的问题;并且,这个问题也就因此完全独立于它是否在某个特定场合下正在被如此使用的问题。
三
再考虑“法国国王是贤明的”这个语句以及罗素关于这个语句所说的正确的话和不正确的话。
罗素关于这个语句所说的至少有两点是对的:
(1)第一点是:它是有意义的;如果现在有人要说出这个语句,那么,他就会说出一个有意义的语句。
(2)第二点是:当事实上在目前存在着一个且仅存在一个法国国王、并且他是贤明的时,现在说出这个语句的任何人才会作出一个真论断。
罗素关于这个语句说得不对的是什么呢?它们是:
(1)现在说出这个语句的任何人不是作出一个真论断就是作出一个假论断。
(2)他所正在断定的部分内容是,目前存在着一个且仅存在一个法国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