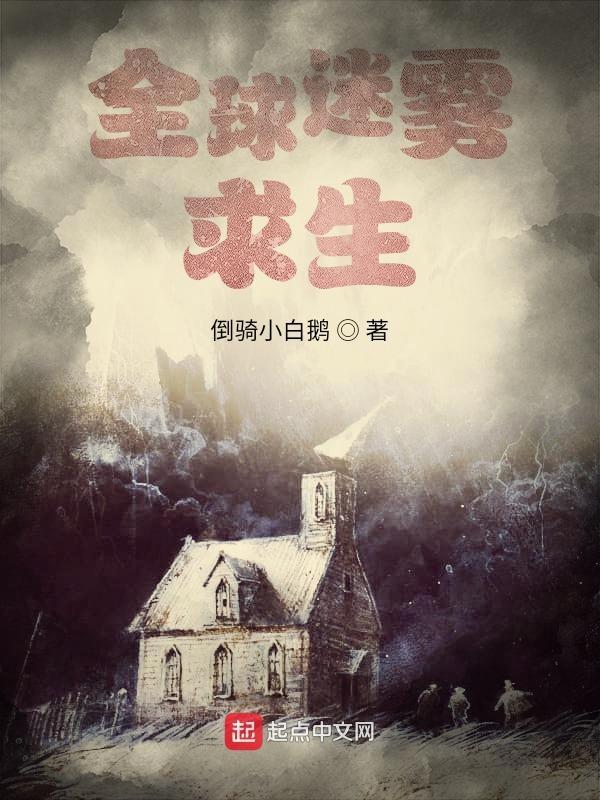奇书网>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 > 善的含义1(第2页)
善的含义1(第2页)
“它可能有益健康,不过它并不好。”
不过尼布甲尼撒将会不得不承认,从功能上说它是好食物;他没有给予的乃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称赞。
然而,我想要提防一种解释,这种解释会使前面提出的定义更加含糊。我用“需要”所指的不仅仅是“标准”或者甚至是“评价的标准”。在这里引入评价的标准将使分析太过曲折从而无法得到阐明,并且单纯参照标准将会忽略一些非常根本的东西。我们可以称某人是一个典型的令人讨厌的人;因而他必定是满足所探讨的标准的人——即令人讨厌的人的标准——不过一个“好的令人讨厌的人”则让人很难理解。我认为,“善”总是包含有对关切、需求等这样一些东西的关涉,我希望“需要”在这个意义上被解读,而不是被单调地几乎等同于“标准”。
有人或许会争论说,存在着这样一些使用,在其中不包含任何像关切这样的东西,在这里某个东西被称作它这一类里边善的东西,在这里“善的”等价于“典型的”。我们以此方式当然可以理解“一个好的鹦鹉螺化石”或者“一个好的日冕”。不过这里无疑依然存在着所探讨的关切;对一个想要知道、想要向别人显示一个鹦鹉螺化石、一个日冕是什么样子的人来说,或者对于一个想要为了以后类似的使用而在博物馆收藏鹦鹉螺化石、拍照记录日冕的人来说,这些是好的样本;如果我们设想某个人就像其他搜集名人一样到处搜集的令人讨厌的人,那么“一个好的令人厌恶的人”就变得基本上可以理解了。“一个好的藏匿”有时候就被作为一个处于此关联中的例子;不过在这里毫无疑问存在着对欲求或者关切的一个指涉,而它们是谁的关切,则被故意地模糊掉了。
二、道德语境中的“善”
如果沿着这些要点的东西是对“善”的一般含义的一个正确解释,那么它基本上没有限制这个词的可能的伦理运用(当然,存在着不止一种伦理运用。“善”可以在范围广泛的各种论题——结果、事态、大众、品格或者特性、行为、选择、生活方式——的道德语境中被表述。在更加技术性的哲学著作中我们发现康德的“善的意志”、亚里士多德的“对人而言的善”、柏拉图的“善”或者“善的相”)。假设甚至在道德语境中“善”也依然具有它的一般含义,它依然刻画了某个东西能够满足所探讨的那类需要、关切或者需求,那么,从言说者的观点或其他(一些?所有?)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需要(等等)是否得到了满足,指涉是否以某种方式涉及每个人的全部关切,所探讨的关切是否如同在功能性的使用或者作为定语的使用中那样以某种方式被形容词“善”明确地或间接地修饰的那个名词决定了,这些依然是不确定的。不过虽然一般的含义使所有这些可能性都尚未确定,但它也使一个更进一步的可能性没有确定,我认为伦理使用很可能特别地示范了这个可能性。使用客观道德价值这个概念的人将假设,存在着一些需要,它们就在那里,就在事物的本质之中,它们不是任何个人或者人群,甚至也不是上帝的需要。因而,成为道德上善的东西就将是成为能够满足这些内在需要的东西。当西季威克把“一个客观地善的东西”等同于“从普遍的观点看是善的东西”的时候,他几乎要把握到这个观念了。当康德通过把善的意志的“尊严”(Würde)与“价值”(Preis)相对照来刻画它的内在的善的时候,他注意到的不只是这一点,还有其他两点。他认为,一个相对于某个主观的要求是善的价值在下述方面也是相对的,一个东西的价值可以和其他东西的价值相比较,可以等于或者超出其他东西的价值;但是尊严在与这些形成对比的两个意义上是绝对的:它是一个不可比较的价值,也是一个内在的价值。不过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我在第一章称作的依赖方向的颠倒:什么具有尊严,这并不仅仅因需要,甚至是普遍的需要而发生变化。所探讨的需要对具有尊严的东西,即善的意志自身来说也是内在的。法律的制定基于各种需要,它确定了所有(其他的?)道德价值:它就是需要。不过我认为,善也是如此,善也被看作是在回应各种需要;所以或许我们应该说,善被看作是各种需要的来源,它也要满足这些需要。这些观念非常令人费解,或许不能完全地前后一致,然而我认为康德是在努力说出潜伏在日常道德思想中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在建构一个哲学的幻想。
根据所有这一切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摩尔的开放问题论证的力量。我们可以说,这个论证利用了概念的不确定性,使我用“所探讨的那类需要”这个短语试图指出的东西成为“善”的含义的一部分。有时候这些需要可能相关于比如说A的愉悦。但是如果我们问,“虽然x有益于A的愉悦,但它是善的么?”就通过问这个问题,我们表明我们在把其他一些需要纳入视野。类似地,通过问“我同意x符合上帝的意图,但是它是善的么?”与我们问“……它是善的么”相关的那些需要将不是x已经被承认为能够满足的那些需要。黑尔曾经认为,摩尔的论证依赖于一个可靠的基础,摩尔自己并没有清楚地理解它:如果善等同于任何具体的特性集合,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因为一个东西具有那些特性而称赞它。确实如此;不过虽然这个对我们来说依然不确定的称赞可能是我曾经称作的自我中心的称赞,但它并不是必须如此:它可以相关于其他各种各样的需要,只要它们不同于其满足已经被包括进事物的特性(事物就是由于这些特性才被称赞的)之中的那些需要。开放问题论证实际上可以转过来反对根据自我中心的称赞对“善”做出的一个定义:我从我自己的观点真诚地称赞一个东西,与此同时,我依然可以使下述进一步的问题有意义,即它是否真的是善的。根据称赞对善做出的一个定义(它可能与这个论证相违背)必须要包含在我们的定义中通过“所探讨的那类需要(等等)”所指明的某种弹性。
有可能看起来客观的价值单独地就会与开放问题论证相违背:大全的观点将混合所有的需要,从而对于从这一观点看是善的东西,我们再也不能问它是否满足了某种需要。不过这是一个徒劳的希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同时满足所有的需要、关切和需求以及类似的东西;不可能存在一个无所不包的观点。局部的邪恶是普遍的善[7]这个表面上令人鼓舞的格言提示了一个不那么令人鼓舞的反思,即普遍的善可能不过是局部的邪恶。
因此,摩尔认为“善”甚至在道德语境中也是不可定义的,或者说它代表了一种不可分析的性质,他这么想是错误的。我们这种定义也把善重新确立为一个纯粹是描述性含义的语词了么?自我中心的称赞或许会被称作并非纯粹描述性的,因为它里边的一个根本性的要素就是言说者对需要的暗中认可——不论这些需要是否明确——被称赞的事物据说可以满足这些需要。不过,它部分地也是描述性的,这在于它既声称事物具有内在的特性(不论这些特性是什么),这些特性使得此事物能够满足这些需要(不论这些需要是什么),(因此)它也声称事物与那些需要具有这种关系。我们在宽泛意义上可以称为称赞的其他事物则是纯粹描述性的:例如与功能性名词相联结的“善”的使用。指向一个假定客观的道德价值的“善”的使用则更加棘手。一方面,它指向存在着这些内在需要以及这个事物可以满足它们这些所谓的确凿事实;另一方面,正因为这是内在地被需要的,所以“从大全的观点看来的善”,它就是这样的这个陈述,也是规定性的——不过不是主观地规定的;它不具有自我中心性,至少它在不纯粹是描述性术语的最明显的例子中是不明确的。但是从我们的定义的确可以推导出,对“善”的使用存在着某种描述性的约束;一个东西要被称作善的,它就必须与像关切这样的东西具有某种满足关系。但是“像关切这样的东西”,或者它们可能的对象,在逻辑上不能够反过来被限制。
然而,从这些描述性含义的要素远远不能推导出下述结论,即“善”就意味着使某个东西成为善的那些特殊的性质。把这些甚至当作它的含义的一部分,例如,当“善”被运用于一把餐刀的时候说“善的”甚至部分地意味着是“锋利的”,这么做将会是一个错误。没有必要说,当“善”的运用从餐刀转到垫子时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的含义,这正如当“大”的运用从跳蚤转到大象时其含义并没有变化,或者当“我”或“这里”被不同的言说者使用时其含义也没有改变。“大”绝不意味着“比一毫米长”;而“这里”也绝不意味着“约翰·麦凯旁边”:这些绝非哪怕是它们含义的一部分,虽然它们是可以从它们在某些运用中所具有的含义那里推导出来的特性。
不过下面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在第一章中被称作“道德怀疑主义”或“主观主义”的东西,对客观道德价值的拒斥,经常被与关于伦理术语之含义的非认知、非描述的观点联系起来,虽然正如我已经论证过的,它并不需要任何这样的观点。所以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善”可以被表明毕竟具有一个描述性的含义,那么客观的价值也会得到恢复。然而,正如已经被我们的解释揭示出来的,这些描述含义的要素并没有这样的倾向,这将是很明显的。的确,“善”的一般含义为这个词可以被用来在道德语境中关涉到假定的内在需要留下了可能;不过它同样地也为道德语境中的“善”可以被用于自我中心的称赞留下了可能。这个词的一般含义在这两个相互对立的观点中是中性的。不过进一步来说,即使我下面的想法是正确的,即主要的伦理使用的确指向假定的内在需要,由此也不能推导出来存在着客观的价值,它只能推导出来道德思想在传统上通常——我已经提出,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理解的——包含了一个客观性的主张。我已经指出对“善”的使用的一个描述性约束,一个东西要成为善的,它就必须与像关切这样的东西相关;不过即使有比这个严格的约束,也没有什么东西会推导出客观的价值。存在着诸如“勇敢”之类的词,它们具有相当确定的描述性含义,不过它们通常也具有自我中心的称赞的一种传统的以言行事的语力:一个人自己如果不认可对一种品格或行为称许性的评价,他就几乎不能够称这个人或这个行为是勇敢的。但由此不能推导出勇气具有客观的价值;能够推导出的只是,对它的称许性的评价被很好地确定了,以至于它已经被吸收进了日常的语言习惯之中了。
我总结如下,对“善”的含义我们可以给出一个解释,这个解释把“善”的伦理使用关联到其他语境中的使用,把在相互对立的哲学理论中被分别强调的不同方面整合到一起。不过对含义的这一研究的结论主要是否定性的。“善”的一般含义自身并没有确定这个语词是如何被运用于伦理学的,并且,不论是这个一般的含义还是任何特殊的伦理含义都没有对实质性的道德问题给出什么解答。
(丁三东译)
[1]选自麦凯:《伦理学——发明对与错》,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2]开放问题论证,是摩尔在其《伦理学原理》中提出的对“自然主义谬误”的主要反驳论证。考虑一个特殊的自然主义主张,“X是善的”等同于“X是令人愉悦的”。如果这个主张是正确的,那么“令人愉悦的是善的”这个判断就等同于“令人愉悦的是令人愉悦的”。然而,当一个人表达前一个主张的时候,他想说的肯定不止后面这个同语反复。所以,即使我们确定某个东西是我们所欲求的、是令我们愉悦的,但它是否是善的,这依然尚未确定。——译注
[3]彼得·吉奇(PeterGeach,1916—2013),英国哲学家、神学家,分析托马斯主义的奠基者,其研究领域包括哲学史、逻辑哲学、神学,著有《心智行为》(1971)、《证明和一般性》(1968)、《逻辑问题》(1980)等。——译注
[4]麦凯举的这个例子并不是非常清楚。一个好的网球选手当然可以不是一个健谈的人。但是麦凯把“一个人既是网球选手又是健谈者的人”作为推理的前提条件。然而“健谈者”(aversationalist)通常已经包含了“善于谈话”(goodatversation)。所以结论当然可以说“这个人同时也是一个健谈者”;只不过这个结论不是通过他提出的测试方式推出的,而是诉诸“健谈者”这个词的通常含义。我们可以改进这个例子,使之更加清楚:一个既是网球选手又是州长的人可以是一个好的网球选手,但却不是一个好的州长。——译注
[5]比利·简·金是美国著名的网球选手,她曾经获得20次温布尔顿网球赛冠军、4次美国网球公开赛冠军。——译注
[6]尼布甲尼撒(Nebuezzar,约公元前630—前561)是古代巴比伦王国的国王,他曾经征服了犹太国,攻陷耶路撒冷并将全城的人虏往巴比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之囚”。他还建造了举世闻名的巴比伦空中花园。——译注
[7]这句话出自英国18世纪的著名诗人蒲伯的诗歌《论人》(EssayonMan)。——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