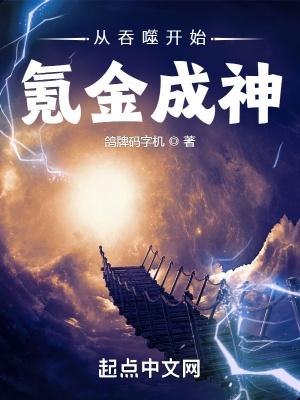奇书网>柳如是别传哪个出版社的好 > 第五章 复明运动05(第4页)
第五章 复明运动05(第4页)
寅恪案:渔洋初以诗贽于牧斋,乃在顺治十八年。故牧斋书有“八十老叟”之语。此时距郑延平率师入长江失败后不久,牧斋实参预大木此举。《白门秋柳》一题,钱、柳俱涉嫌疑,自不欲和韵,否则《秋柳》原诗即使为人攫去,亦可重抄传寄。其答渔洋之言,不过推托之辞耳。至河东君是否真如牧斋所谓“当家老姥”“十指如锥”“吟红咏絮”“邈若隔生”,亦殊有疑问。盖此时固不免多少为家务所干扰,但以当日士大夫之生活状况言,绝下致无挥毫作字之余暇,然则所谓“白家老媪,刺促爨下”,仍是婉言辞谢,借以免却外间之招摇而已。呜呼!当河东君赋《金明池·咏寒柳》词时,谢象三目之为“白氏女郎”。当王贻上请其和《秋柳》诗时,牧斋目之为“白氏老媪”。二十余年间,人事之变迁如此。牧斋诗云:“杨柳风流烟草在,杜鹃春恨夕阳知。”(见《有学集》三《夏五诗集·留题湖舫二首》之二。第四章已引。)渔洋山人虽非旧朝遗老,然亦生于明季。钱、柳不肯和《秋柳》诗之微意,或能有所感悟欤?
夫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迁,据《有学集》十《红豆诗二集·后秋兴八首·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其五云:“水击风抟山外山,前期语尽一杯间。”(并见遵王注本《投笔集》。)当时牧斋迫于不得已而往北京,但河东君独留南中,仅逾一岁,即顺治三年秋,牧斋遂返故里。可知钱、柳临别时必有预约。两人以后复明之志愿,即决定于离筵之际矣。丁亥春,黄毓祺之案,牧斋实预其事,距前此白门分手时,亦不过一年有半也。
黄毓祺案牧斋虽得苟免,然复明之志仍不因此而挫折。今就牧斋作品中所能窥见者,即游说马进宝反清一事。(寅恪案:马氏于顺治十四年九月清廷诏改其名为“逢知”。见《清史列传》八十《马逢知传》。)关于牧斋本身之活动,兹可不详引。但涉及河东君者,则备论述之,以明本文宾主轻重之旨也。
今检《瞿忠宣公集》五《留守封事类》“奏为天意扶明可必,人心思汉方殷,谨据各路蜡书,具述情形,仰慰圣怀。更祈迅示方略,早成中兴伟业事”略云:
臣子壬午举人元锡,因臣孙于去腊离家,未知其到粤消息,遣家僮胡科探视。于〔永历三年己丑〕七月十五日自家起程,今月十六日抵臣桂林公署,赍带臣同邑旧礼臣钱谦益寄臣手书一通,累数百言,绝不道及寒温家常字句,惟有忠驱义感溢于楮墨之间。盖谦益身在〔虏〕中,未尝须臾不念本朝,而规画形势,了如指掌,绰有成算。据言:“难得而易失者时也。计定而集事者局也。人之当局,如弈棋然。楸枰小技,可以喻大。在今日有全著,有要著,有急著。善弈者,视势之所急而善救之。今之急著,即要著也。今之要著,即全著也。(寅恪案:顾苓《塔影园集》一《东涧遗老钱公别传》云:“以隐语作楸枰三局,寄广西留守太保瞿公。”今《有学集》中,固多观棋之作,可称隐语,然与此书之明显陈述者,绝不相类。《投笔集·后秋兴之六》第四首云:“腐儒未谙楸枰谱,三局深惭廑帝思。”及《后秋兴之十二》第三首云“廿年薪胆心犹在,三局楸枰算已违。”牧斋诗语即指此致稼轩书言。岂云美虽间接获知其事,而未亲见原书,遂致有此误会耶?至其列此事于黄案之前,其时间先后之讹舛,更不待辨矣。)夫天下要害必争之地不过数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长淮汴京,莫非都会,则宜移楚南诸勋重兵,全力以恢荆襄。上扼汉沔,下撼武昌。大江以南,在吾指顾之间。江南既定,财赋渐充,根本已固,然后移荆汴之锋,扫清河朔。其次所谓要著者,两粤东有庾关之固,此有洞庭之险。道通滇黔,壤邻巴蜀。方今吴三桂休兵汉中,三川各郡数年来非熊(指王应熊)在彼,联络布置,声势大振。宜以重兵径由遵义入川。三川既定,上可以控扼关陇,不可以掇拾荆襄。倘以刍言为迂而无当,今惟急著是问。夫弈棋至于急著,则苟可以救败者,无所不用。迩者燕京特遣恭顺、致顺、怀顺三〔逆?〕进取两粤。(寅恪案:《清史列传》七八《尚可喜传》略云:“崇德元年四月封智顺王。顺治三年八月同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征湖南。”牧斋书中“智顺”作“致顺”,乃音近笔误。原阙一字,今以意补为“逆”字。盖此三人者,在清为顺,在明为逆也。)因怀顺至吉安忽然缢死,故三路之师未即渡洞庭,过庾岭。然其势终不可遏,其期谅不甚远。岂非两粤最急时乎?至彼中现在楚南之劲〔敌〕,惟辰常马蛟麟为最。传闻此举将以蛟麟为先锋。幸蛟麟久有反正之心,与江浙〔虏?〕提镇张天禄、田雄、马进宝卜从善辈,皆平昔关通密约,各怀观望。此真为楚则楚胜,而为汉则汉胜也。蛟麟倘果翻然乐为我用,则王师亟先北下洞庭。但得一入长江,将处处必多响集。我得以完固根本,养精蓄锐,恢楚恢江,克复京阙。若谦益视息余生,奄奄垂毙,惟忍死盼望銮舆拜见孝陵之后,槃水加剑,席稿自裁等语。臣反覆披阅,虽谦益远隔万里,而彼身为异域之臣,犹知眷恋本朝,早夜筹维,思一得以图报效,岂非上苍悔祸,默牖其衷,亦以见天下人心未尽澌灭,真祖宗三百年恩养之报。臣敢不据实奏闻,伏祈皇上留意详阅,特赐鉴裁。臣缮疏方毕,适原任川湖督臣万年策自平溪卫取路黎靖来至桂林。具述虏镇马回子驻兵常德,实有反正之心。回子即名蛟麟者也。以情事度之,钱谦益楸枰三局揣摩之语,确相吻合,似非无据。岂非楚南拨云见日之时,而中兴之一大机会耶?
据此牧斋《致稼轩书》作于顺治六年己丑之秋。其中已言及马进宝。故次年庚寅即有往金华游说马氏之事。更可注意者,即说马之举实与黄梨洲有关。黄宗羲《思旧录》“钱谦益”条(此条第四章已引,兹为便利论述,故重录之。)云:
一夜余将睡,公提灯至榻前,袖七金赠余曰,此内人(自注:“即柳夫人”)意也。盖恐余之不来耳。是年(指顺治七年庚寅),十月绛云楼毁,是余之无读书缘也。
《鲒埼亭集》一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略云:
公既自桑海中来,杜门匿景,东迁西徙,靡有宁居。又有上变于大帅者,以公为首,而公犹挟帛书,欲招婺中镇将以南援。
黄炳垕编《黄梨洲先生年谱》中“顺治七年庚寅”条云:
三月,公至常熟,馆钱氏绛云楼下,因得尽翻其书籍。
寅恪案:太冲三月至常熟,牧斋五月往金华。然则受之此次游说马进宝,实梨洲所促成无疑。观河东君特殷勤款待黄氏如此,则河东君之参预劝马反清之政治活动,尤可证明也。
又金氏《牧斋年谱》“〔顺治八年〕辛卯”条云:
为黄晦木〔宗炎〕作书绍介见马进宝于金华。(原注:“尺牍”)
金氏未言出于《尺牍》何通,但检《牧斋尺牍(中)·致□□□》略云:
余姚黄晦木奉访,裁数行附候,计已达铃阁矣。友人陈崑良赴温处万道尊之约,取道金华,慨慕龙门,愿一投分。介恃道谊之雅,辄为绍介。晦木知必荷眄睐,先为遥谢。
寅恪案:此札乃致马进宝者。细玩其语气,介绍晦木与介绍崑良,时间相距至近,且足知两人俱是初次介绍。今检《浙江通志》一二一《职官表》“分巡温处道”栏云:
陈圣治,辽东锦州人。顺治十年任。
万代尚,辽东铁岭人。顺治十四年任。
孟泰,辽东辽阳人。贡士。顺治十六年任。
及《清史列传》八十《马逢知传》略云:
〔顺治〕三年,从端亲王博洛南征,克金华,即令镇守。六年命加都督佥事,授金华总兵,管辖金衢严处四府。七年九月,奏言臣家口九十余人,从征时即领家丁三十名星赴浙东,此外俱在旗下,距金华四千余里,关山迢递,不无内顾之忧。恳准搬取。下部知之。十三年迁苏松常镇提督。
并《有学集》七《高会堂诗集》有:
丙申重九海上作。
一题及《高会堂酒阑杂咏序》末署:
〔顺治十三年〕丙申阳月十有一日书于青浦舟中。
故综合推计牧斋之介绍晦木见马进宝于金华,实在顺治十三年丙申秋季以前,马氏尚未离金华赴松江之时。至《浙江通志》列万代尚之任温处台道,始于顺治十四年者,不过因排次便利,只书年而不书月。否则,绝无元旦上任除夕解职之理也。
嗟君万里赴行都。桂岭云深入望迂。岂意张公双剑去,却令伍子一箫孤。粤西驻辇当通塞,湖北扬旌定有无。分手三年鸿雁断,如余今日正穷途。
可见陈氏同是当时参预复明运动之人。牧斋介绍之于马进宝,必非寻常干进以求衣食者之比。惜光绪修《常昭合志稿》三一《义行门·陈璧传》仅云:
陈璧,字崑良。崇祯末尝三上书论事。不报。归隐。
寥寥数语,殊为简略。今读闇公此诗,则陈氏平生志事更可证知矣。
兹仅录牧斋作品中,庚寅夏往返金华,游说马进宝之作品,并略加释证于下。《有学集》三《庚寅夏五集序》云:
岁庚寅之五月,访伏波将军于婺州。以初一日渡罗刹江,自睦之婺,憩于杭。往返将匝月,漫兴口占,得七言长句三十余首,题之曰《夏五集》。《春秋》书“夏五”,传疑也。疑之而曰“夏五”,不成乎其为月也。不成乎其为月,则亦不成乎其为诗。系诗于夏五,所以成乎其为疑也。《易》曰:“或之者,疑之也。”作诗者,其有忧患乎?
寅恪案:此《夏五集》可称为第一次游说马进宝反清复明之专集。河东君参预此活动,尤为显著。读者应特加注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