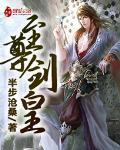奇书网>柳如是别传在线阅读 > 第五章 复明运动02(第5页)
第五章 复明运动02(第5页)
海虞钱牧斋名谦益,中万历庚戌探花,官至少宗伯,历泰昌、天启、崇祯、弘光五朝矣。乙酉岁,北兵入南都,率先归附,代为招抚江南,自谓清朝大功臣也。然臣节有亏,人自心鄙之。虽召至燕京,任为内院,未几即令驰驿归,盖外之也。四月朔,忽缇骑至苏猝逮云。
钱牧斋有妾柳氏,宠嬖非常。人意其或以颜貌,或以技能擅长耳。乃丁亥牧老被逮,柳氏即束装挈重贿北上,先入燕京,行赂于权要,曲为斡旋。然后钱老徐到,竟得释放,生还里门。始知此妇人有才智,故缓急有赖,庶几女流之侠,又不当以闺阃细谨律之矣。
〔黄毓祺〕将起义,遣徐摩往常熟钱谦益处提银五千,用巡抚印。摩又与徽州江某善。江嗜赌而贪利,素与大清兵往还。知毓祺事,谓摩返必挟重资,发之可得厚利。及至常熟,钱谦益心知事不密,必败,遂却之。摩持空函还,江某诣营告变,遂执毓祺及薛生一门(寅恪案:“薛生”指薛继周之第四子),解于南京部院,悉杀之。钱谦益以答书左袒得免。然已用贿三十万矣。
之类,皆未明当日事实所致。叶氏之书,大抵依时日先后排列,但“钱牧斋有妾柳氏”条,乃闻牧斋脱祸以后,因补记于“海虞钱牧斋名谦益”条相近处,盖以同述一事故也。所可注意者,其记牧斋被逮至苏,在丁亥四月朔,与洪亨九原揭所引吴胜兆供词及牧斋自记丁亥三月晦日在家忽被急征者相合。常熟距苏州甚近,叶氏于四月朔闻讯,遂笔录之耳。天寥与牧斋之关系,迥非谢象三之比,然其记牧斋被逮事,亦在顺治四年丁亥,殊有参考之价值。至于所言河东君挈重贿北上先入燕京、牧斋徐到一节,乃得之辗转传闻,可不置辩。叶氏言“重贿”,计氏言“用贿三十万”,皆未悉牧斋当日经济情况者之揣测。兹略微载记,以证牧斋此时实不能付出如此巨大数量之金钱,而河东君之能利用人情,足使牧斋脱祸,其才智尤不可及也。关于牧斋经济情况之记载,虽颇不少,但一人一家之贫富,亦有改变,故与黄毓祺案发生之时间相距前后久远者,可不征引。前论河东君患病,经江德璋治愈,牧斋以玉杯赠江为谢,因述及顺治二年乙酉清兵破明南都,牧斋奉献豫亲王多铎之礼物独薄一事,据此得知牧斋当时经济情况实非丰裕。盖值斯求合苟免之际,若家有财货,而下献纳,非独己身不应出此,亦恐他人未必能容许也。南都迎降之年,下距黄毓祺案发生之岁,时间甚近,故牧斋必无重资厚贿以脱祸之理。今存《牧斋尺牍》,其中诉穷告贷之书札不少,大抵距黄案时间颇远,以非切当之资料,不多引。唯与毛子晋四十六首,其第三十九通云:
狱事牵连,实为家兄所困。顷曾专信相闻,而反倩笔于下走者,老颠倔强,耻以残生为乞丐耳。未审亦能悉此意否也?归期不远,嘉平初,定可握手。仲冬四日。
检《有学集》一七《赖古堂文选序》云:“己丑之春予释南囚归里。”可证牧斋于顺治六年己丑春间,被释归常熟。此札末署“仲冬四日”,即顺治五年戊子十一月初四日。“嘉平初,定可握手”者,谓戊子年十二月初,可还家与子晋相见。牧斋作此札,尚在黄案未了结之时。然则叶、计两氏所言之非信史,更可见矣。
明末苏松常镇之士大夫,多置田产,以供其生活之费用。清室因郑成功舟师入长江之役,江南上大夫多响应者,发起奏销案以资镇压。观孟心史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奏销案》一文,可概见也。复检《牧斋尺牍(中)·与□□□》云:
双白来,得手教,谆谆如面谈。更辱垂念,家门骨肉道义,情见乎词,可胜感佩。近日一二枭獍,蜚语计穷,创为一说,谓寒家户田欠几万金,将有不测之祸。又托言出自县令之言,簧鼓远近。试一问之,户有许多田?田有许多粮。若欲盈欠万之额,须先还我逾万之田而后可。小人嚼舌,不顾事理,一至于此。此言必有闻于左右者,亦付之一笑可也。海晏河清,杜门高枕,却苦脚气缠绵,步履艰涩。此天公妒其安闲,以小疾相折抵也。
寅恪案:此札虽不知致谁者,但据“家门骨肉”之语,知其人为牧斋同族。“双白”者,指王廷璧,见《明诗综》八十上等。牧斋之免于奏销案之牵累,当别有其他原因,然其田产无论有无,纵或有之,亦微不足道,观此札可以证知。牧斋既不依田产收入为生,则其家计所赖,唯有卖文一途。《河东君殉家难事实·孝女揭》略云:
我母柳氏,系本朝秘书院学士我父牧斋公之侧室。吾父归田之后,卖文为活。茕茕女子,蓄积几何。
此虽指牧斋于顺治三年丙戌秋由北京还常熟以后事,但黄案之发生即在此年之后。此数年间,牧斋遭际困顿,自不能置田产。由是言之,牧斋丙戌后之家计,亦与其前此者无异,皆恃卖文维持。赵管妻之语,固指丙戌以后,实可兼概丙戌以前也。今所见资料,足资证明此点者殊多,不须广引。考牧斋为王弇州后文坛最负盛名之人(见黄梨洲《思旧录》“钱谦益”条),李北海“干谒走其门,碑版照四裔”(见《杜工部集》七《八哀诗》之五及《旧唐书》一九十中《文苑传·李邕传》),韩昌黎谀墓之金(见《新唐书》七六《韩愈传附刘叉传》)。其故事可举以相比也。复检《牧斋尺牍》中《与王兆吉五通》,其第五通云:
生平有二债,一文债,一钱债。钱尚有一二老苍头理直,至文债,则一生自作之孽也。承委《南轩世祠记》,因一冬文字宿逋未清,俟逼除时,当不复云祝相公不在家也。一笑!
同书同卷《与遵王三十通》,其第五通云:
岁行尽矣,有两穷为苦。手穷欠钱债多,腹穷欠文债多。手穷尚可延挨,东涂西抹。腹穷不可撑补,为之奈何?甫老寿文,前与其使者以望日为期,正是祝相公又不在家时候也。一笑!
关于牧斋与介子是否如马国柱所谓“素不相识”之问题,兹检《牧斋尺牍(中)·与木陈和尚(寅恪案:木陈即道忞)二通》,其第二通云:
《密云尊者塔铭》,十五年前已诺江上黄介子之请矣。重以尊命,何敢固辞。第以此等文字,关系人天眼目,岂可取次命笔。年来粗涉教乘,近代语录,都未省记。须以三冬岁余,细加检点,然后可下笔具稿。谨与晓上座面订,以明年浴佛日为期,尔时或得围绕猊座,觌面商榷,庶可于法门稍道一线,亦可以慰吾亡友于寂光中也。
其第一通略云:
丧乱残生,学殖荒落,恭承嘉命,令补造《密云老人塔铭》,以偿十五年旧逋。每一下笔,辄为战掉。次后著语,颇为老人施十重步障。窃自谓心平如地,口平如水,任彼百舌澜翻,千喙剥啄,亦可以譬诸一吷,付之一笑。
及《有学集》三六《天童密云禅师悟公塔铭》略云:
崇祯十四年辛巳,上以天步未夷,物多疵厉,命国戚田弘遇,捧御香,祈福补陀大士还,赍紫衣赐天童悟和尚。弘遇斋祓将事,请悟和尚升座说法,祝延圣寿。还朝具奏,上大嘉悦,俞其请。诏所司议修成祖文皇帝所建南京大报恩寺。命悟为住持,领其事。弘遇衔命敦趣,以老病固辞。逾年而示寂。又二年甲申,国有大故,龙驭上宾。越十有五年戊戌(即顺治十五年),嗣法弟子道忞具行状、年谱,申请谦益,俾为塔土之铭。师讳圆悟,号密云。嘉靖戊寅岁,生常州宜兴,姓蒋氏。示微疾,趺坐频申而逝,崇祯十五年壬午七月七日也。世寿七十七,僧夏四十四。明年癸未,弟子建塔天童,迎全身窆幼智庵之右陇。师剃度弟子三百余人。王臣国士参请皈依者,又不胜数。偕忞公二通辈结集语录书问,标揭眼目者,江阴黄毓祺介子也。师既殁,介子裁书介天童上座某属余为塔铭。遭世变,不果作,而介子殉义以死。又十年矣,余为此文,郑重载笔,平心直书,誓不敢党枯仇朽,欺诬法门,用以副忞公之请,且慰介子于九原也。
则牧斋与介子为旧友,此三文乃是铁证。马国柱奏谓钱、黄素不相识,公牍文字自来多非事实,即此可见。牧斋作《密云塔铭》时,在郑延平将率舟师入长江之前夕。岂牧斋预料国姓此举可以成功,遂亦反其往日畏葸之态度,而昌言不讳其与介子之关系耶?又《圆悟塔铭》涉及田弘遇补陀进香事,颇饶兴趣,读者可取前述江南名姝被劫及避祸事参阅也。
夫起西为常熟人,又是牧斋旧友黄介子之高弟。牧斋垂死时,梨洲至虞山视牧斋疾,即寓起西家(见后引梨洲《思旧录》“钱谦益”条)。则起西自与牧斋不能无关涉,可以推知。首告之盛名儒逃不赴质,恐是河东君间接所指使。殆取崇祯时告讦牧斋之张汉儒故事以恐吓之也。至介子之能在狱中从容自尽,疑亦与河东君之策略有关,因借此可以死无对证,免致牵累牧斋。其以介子病死为言者,则可不追究监守之狱吏耳。黄案得如此了结,河东君之才智绝伦,诚足令人惊服。所可注意者,牧斋不付五千金与徐摩,遂因此脱祸。鄙意牧斋当时实亦同情于介子之举动,但其不付款者,盖由家素不丰无以筹办巨额也。故就此点观之,亦可证知牧斋经济之情况矣。
关于牧斋狱中寄河东君诗,第三章论卧子《长相思(七古)》,已引王应奎《柳南随笔》涉及牧斋此诗序“弟”与“妻”之问题,可不复赘。惟牧斋此诗,虽有遵王之注,然亦未能尽窥其师之微旨。故重录此诗序,并六首全文,分别笺释之。其他典故,读者自当更取遵王原注并观也。
《有学集》一《秋槐诗·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其序云:
丁亥三月晦日,晨兴礼佛,忽被急征。银铛拖曳,命在漏刻。河东夫人沉疴卧蓐,蹶然而起,冒死从行,誓上书代死,否则从死。慷慨首涂,无刺刺可怜之语。余亦赖以自壮焉。狱急时,次东坡御史台寄妻诗,以当诀别。狱中遏纸笔,临风暗诵,饮泣而已。生还之后,寻绎遗忘,尚存六章,值君三十设帨之辰,长筵初启,引满放歌,以博如皋之一笑。并以传视同声,求属和焉。
寅恪案:娄东无名氏《研堂见闻杂录》云:“牧斋就逮时〔柳夫人〕能戎装变服,挟一骑护之。”某氏所记河东君事,多杂采他书,实无价值。其言河东君戎装挟一骑护牧斋,则绝无根据,不过牵混河东君作“昭君出塞装”之传说而来耳。此事前已辨之矣。至“无刺刺怜之语”,乃用韩退之《送殷侑员外使回鹘序》中:
今人适数百里,出门惘惘,有离别可怜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宁顾婢子语,刺刺不能休。
之文(见《五百家注韩昌黎先生文集》二一)。遵王注中未及,特标出之,以便读者,并足见牧斋之文,无一字无来处也。又“余亦赖以自壮焉”之语,与第一首诗“恸哭临江无壮子”句,亦有相互关系。余见下论。
抑有可附论者,即关于河东君生年月日之问题。当牧斋顺治四年丁亥赋此六诗时,河东君应如牧斋之言,确为三十岁。此点并据康熙三年甲辰河东君示其女赵管妻遗嘱所言“我来汝家二十五年”(参第四章论《寒夕文宴》诗节),及顾苓《河东君传》所载“定情之夕,在辛巳六月七日,君年二十四矣”等资料,推计符合。或谓牧斋于丁亥三月晦日在常熟被急征,至南京下狱,历四十日出狱,即牧斋此题序所谓“生还”。若依此计算,其出狱当在五月间。然则河东君之生辰应在五月矣。鄙意牧斋所谓“生还之后,值君三十设帨之辰”,其时限虽不能距五月太远,但亦难决其必在五月,是以或说亦未谛也。至牧斋序文所以引“贾大夫”之烂熟典故者(详见第四章论牧斋《庚辰冬日同如是泛舟再赠》诗“争得三年才一笑”句所引),固借此明著其对河东君救护之恩情,更别具不便告人之深旨。盖明南都倾覆,在乙酉五月。自乙酉五月至丁亥五月,亦可视为三年。在此三年间,河东君“不言不笑”,所以表示其不忘故国旧都之哀痛。遵王注已引《左氏传》以释此古典,然恐未必通晓其师微意所在。故不可据牧斋之饰辞,以定河东君之生辰实在五月也。唯有可笑者,第四章论牧斋《〔庚辰〕冬日同如是泛舟有赠》诗引江熙《扫轨闲谈》,谓牧斋“黑而髯,貌似钟馗”可知牧斋有贾大夫之恶。至牧斋之才,在河东君心目中,除“邺下逸才,江左罕俪”之陈卧子外,“南宫主人”尚有可取之处(见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牍》第二五通及第三十通)。宜其能博如皋之一笑也。
朔气阴森夏亦凄,穹庐四盖觉天低。青春望断催归鸟,黑狱声沈报晓鸡。恸哭临江无壮子,徒行赴难有贤妻。重围不禁还乡梦,却过淮东又浙西。
寅恪案:第一句“朔气”盖谓建州本在北方。“夏亦凄”者,言其残酷也。韩退之《赠刘师服》诗云:“夏半阴气始,淅然云景秋。蝉声入客耳,惊起不可留。”(见《五百家注昌黎先生集》五)牧斋以丁亥三月晦日在常熟被急征,至南京下狱时,当在四月初旬。历四十日出狱,已在五月。五月为仲夏,与韩诗“夏半”之语适切。或云牧斋下狱在夏季,似与韩诗“云景秋”之“秋”不合。鄙意骆宾王《在狱咏蝉》诗“西陆蝉声唱”句(见《全唐诗》第二函骆宾王三),虽是秋季所作,但诗题有“狱中”之语,牧斋遂因韩诗“蝉声入客耳”句联想及之。观牧斋此诗第四句“声沉”之语,与骆氏此诗“风多响易沉”句相应合,可以证知。不必拘执韩、骆诗中“云景秋”及“西陆”之辞为疑也。第二句遵王注本作“穹庐”,并引《史记·匈奴传》以释之。甚是。盖牧斋用“穹庐”之辞,以指建州为胡虏。其作“穹苍”者,乃后来所讳改也。第三句遵王注引韩退之《游城南》诗中《赠同游(五绝)》释之。亦是。但《五百家注昌黎先生诗集》九此诗注略云:
牧斋丁亥四月正在金陵狱中,故以青春望断“不如归去”为言,其意更出韩诗外矣。第四句言建州之统治中国,如双王之主宰泥犁,即所谓“暗无天日”者。关于第二联之解释,甚有问题。《柳南随笔》一(参《东皋杂钞》三及《牧斋遗事》“牧翁仕本朝”条)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