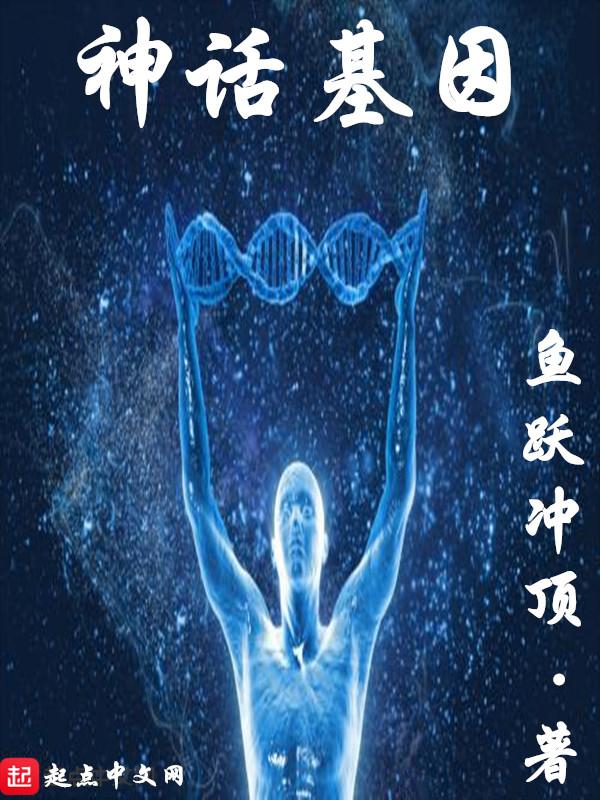奇书网>夜巡的作者是谁 > 五(第2页)
五(第2页)
他慢慢立起身,摇摇摆摆朝他卧室走进去,关上了门。
一个白净净、眼睛细长长的老太朝我一笑:“你叫什么?驾牛?这名字真有田园气息。你别生气,刚才那老头,生下来就那吃相,别理他就好。”
一个戴红框眼镜的胖老太斜我一眼:“要在一号楼混饭吃,眼睛看清楚,嘴巴要把得稳!”
我用眼睛找抹布,希望马上可以把周围的一切用水擦一遍。我看过沙发边的角落,又看那些小圆桌子,再去看电视机下面柜子。都没有抹布。
“我跟你讲话呢!”胖老太用圆鼓鼓的手指捅我一下,“先知道一下楼里情况,对你有好处!”
我把眼光转回来,定在胖老太鼻尖上。她眼珠在淡黄镜片后很恼怒地瞪我,像我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
“告诉你,楼上和楼下可不是一伙儿的。”她说。
“是的。你看过电影不?”细长眼老太凑过来,笑着告诉我,“楼下喜欢的事情,楼上就反对!”
“你得告诉他为什么!”胖老太抢说,“我们的养老金是辛辛苦苦一辈子不吃不喝攒下来的。下面那伙人的钱来路不明。外头混不下去,跑里头来欺负我们。”
“一样住着一号楼,”细眼睛老太说,“凭什么吃比我们多吃,喝比我们多喝?我们吃的东西恐怕是他们吃剩下的!”
“这要看你良心了!”两个老太都用手指头指我。她们的手指很烦人,指着指着就落到我心口,戳在那里不动了。
我想到那只方头猴,想知道这些老太为啥围着他转。问题卡在喉咙口,问不出来。
我下楼去找抹布扫帚,看见廖老头朝我招手,我走过去,听他吩咐。
“小伙子很好!长得很精神!”廖老头站起来,走开了。我见他走进自己房间,关上了门。
另一个和气的小老头向我送来一串千变万化的笑,像用不停的笑容讲话。我惊奇地看他的白头发和皱纹,无论是头发还是皱纹,在他身上都软软的,一点不让人难受。他说:“小伙子,初来乍到,坐下来谈谈心呀?”
老头老太太呜呜地点头,好像他们一齐邀请我。
我放下抹布扫帚,听他们要吩咐我什么。
“我们是一群老人,现在体弱多病,需要年轻人照顾。不过,我们曾为社会做过贡献!不说我们,就说说廖局长。廖局长多年来担任文化工作,他把一辈子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文明建设上。我们的城市如今花好月圆,怎么离得开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呢?”白头发老头说到这儿,被那鹅蛋面孔小眼睛的老太太用一只白胖手拍断了。
“小孩子听不懂你文绉绉的。”老太太扭头对我说,“别信楼上那些小市民嚼舌头,廖老退下来是局级干部,对他保留些尊敬是应该的。请问楼上那些小市民,他们一辈子为社会做过什么?只知道索取!”
“告诉你吧!”她耐心等我慢慢看她眼睛了才说,“楼上那个方头家伙道德品质是有问题的,我看过他档案!”
我不知道老太太为什么激动,又为什么得意洋洋。她看过方头老汉的裆啊?!我觉得好笑。
过妈妈关照过我,差不多十点光景,要把一号楼每个人的点菜单收集来,送交她本人。早上她已来过,把今天厨师愿意做的三种花式写在一楼和二楼楼梯口小黑板上。老头老太们要做的,是把自己挑好的菜式写到点菜单上,填上自己名字。
我拿着一楼填好的点菜单到二楼去收二楼的,楼梯扶手上不知给谁蹭了一大块污斑,我把点菜单放沙发上,找了抹布来擦干净,又洗抹布,晾起来。
十点整我把点菜单送给过妈妈,她问:“今天到这会儿了,一号楼还没吵起来?让你去一号楼,的确有点意思!”她一伸手,我工作服胸兜里多了堆热腾腾的鹌鹑蛋。
过妈妈和我一起推保温车,把菜和饭送一号楼。二号楼、三号楼和四号楼的老头老太互相搀扶着,正赶往食堂去吃午饭,一轮发红的日头晒得人额头发烫。
“有钱人坐在**吃饭。”一个老头看看我们,哼一声。
“还不用亲自上厕所。”另一个老头笑呵呵,“有人递扁马桶,替你擦屁股!”
这群老家伙满怀恶意地看着我,看着过妈妈。
过妈妈看看他们,笑着挥手:“去去去!别一个个红口白牙!收掉你们电炉子是为你们好!成天偷吃,小心烧了房子,把自己烧成点心!”
“就是怕我们烧了房子呗!”一个老太婆咕哝,“说为我们好,假仁假义!”
进了一号楼,我独个儿卖力气。过妈妈省了心,只念念菜单,告诉我什么餐盘端给什么人。老头老太个个浑身通泰,坐下来吃午饭,一桌还给上一瓶红酒。
过妈妈很满意我,凑我耳朵说:“给你留了一大块走油肉,不是给你午饭吃,也不是晚饭吃,给你带回房间,半夜吃!”
我满心欢喜。半夜一块肥腻的走油肉,绝对是我走出大山的彩头!
廖老头忽然不高兴了,他那帮手下七手八脚喊过妈妈:“上错菜了!廖局说过多少次他不能吃辣椒?”
过妈妈翻出廖老头的点菜单,上面涂掉了一个菜名,重新写上了“辣椒炒干丝”。
“这是怎么一回事?”老家伙们吹胡子瞪眼望着我。
我把菜抬到二楼。过妈妈分菜,我看见方头猴笑得差点气绝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