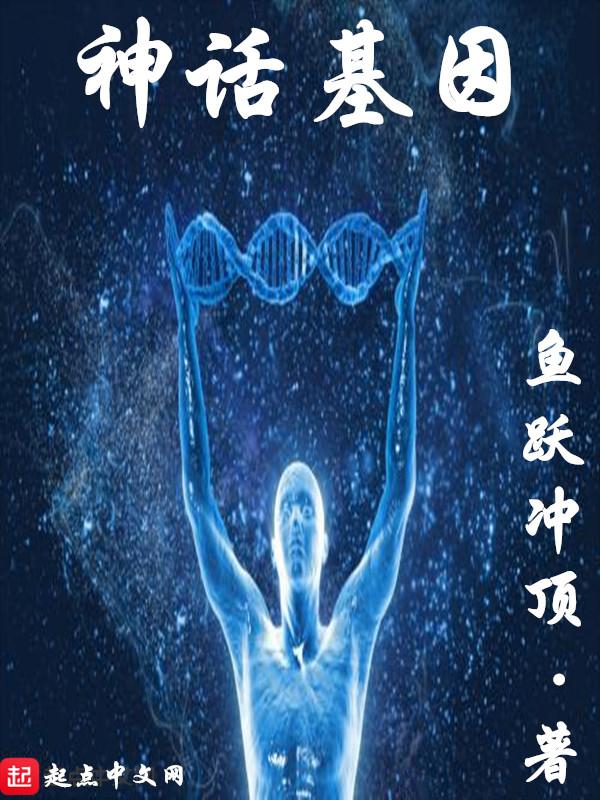奇书网>本草春秋是什么 > 禹余粮(第2页)
禹余粮(第2页)
后人提起那次治水,描述都很简单,说大禹的父亲鲧只会堵,结果连有能够无限生长的神土息壤帮忙也是不成,只好换了大禹来,用疏导的方法十三年后终于大功告成。如此而已。
果真如此简单吗?或者换句话说,有着多年治水经验的鲧,思维竟会如此僵化机械吗?
水利是一项专门技术,自古便是专家的活计。西汉末年,黄河频决,水患严重,汉哀帝下诏“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一个专家,贾让,应诏上书,提出了著名的治河三策。上策是不与水争地,而是顺水之势改河道,转移挡着水流的民众,避高趋下,决口放河入海;中策是开渠引水,达到分洪、灌溉和水运等目的;下策才是“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对堤防修修补补。他认为,如用上策,虽然一时损失很大,却能一劳永逸,“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而中策可以“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如用了下策,那便永远“劳费无已,数逢其害”,再没个出头之日。
后世对此三策评论不一,虽然大部分人都认为贾让说得很有道理,可谁也不敢轻易尝试他的上策。当时便有人反驳贾让,说如用了他的上策,结局将不敢想象:“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
谁都知道,顺着水势因势利导,四两拨千斤,是最简单也是最明智的做法。而堵,却是最愚笨最危险的。贾让用了个比喻,他说“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水如果只靠着堵,就好像想叫小孩子不哭就塞住他的嘴,如果不马上停止,“其死可立而待也”。
但谁都得正视水路上那亿亿万万的“城郭田庐冢墓”!有几人、几个王朝,能做出如此大的决心,能承受如此大的牺牲呢?
想保住所有的局部利益,结局却往往是失去更多的利益,这个问题谁都看得到,但谁也没办法。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众诸侯会于葵丘,一大议题便是想解决各国自修水利、不计邻国安危的弊政。会上倒是立了盟誓,可盟誓自盟誓,会后各国仍自行其是。直到真正统一的秦汉帝国建立,才又一次在全局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亘古难题。
可还是没有谁敢放手让江河自由而下,一路浩**奔流。
所以在黄河面前,几千年几乎全赖着一条下策在苦苦支撑,堤坝随着淤泥水势上升,直到彻底被勒成了一条高高在上的悬河。
当时这个难题一定也摆在鲧的面前,甚至,他面临的困难更加难以克服。或者说,鲧没有魄力牺牲眼前赖以为生的宝贵土地;或者说,他的下游部落,也一样舍不得神圣的田园,绝不肯为鲧治下的洪水让出一条正路,并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包括战争。
很少有人懂得以舍求得,尤其在疆域上。
正是土地捆住了鲧的手脚。所以鲧便只好手忙脚乱地用堵的方法,用土围子战战兢兢地守着那一块块长满了庄稼的田地,见招拆招,狼狈地与洪水缠斗,终有一日,堤防塌了。
禹的伟大,正是在于他看出了父亲做法的无奈和无效。在父亲的灵位前,他发誓,要接过这副世上再无人能承受的重担,并将用他的法子,完成这项大业。
终于,他成功了。
禹的成功与其说是由于他的辛劳坚韧,也许不如说更多的是凭借他的魄力和铁腕。可能,治水过程中,对天下部族的协调、安置,甚至用残酷的武力强制推行,与他的凿山开河同样重要。《韩非子》中有一句话,“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提到居然有民众公然阻碍治水,也透露了禹的对手不仅仅是大自然。
从父亲坟前启程的那天,禹便有了一张设想中可以让所有人都安居乐业的天下规划蓝图。
这张在禹手里实现了的蓝图,便是我们的“九州”。后世所有的宏功伟业、征战阴谋,轰轰烈烈也好、回肠**气也好、阴险残酷也好,都在这个禹为我们开创的舞台上一幕幕上演。
以禹为代表的先人,为我们从凶险的自然手里夺回了土地。应该说,站在自然(也就是古人所谓的天地)的对立面,争取生存权利的努力,从人类诞生以来就没有片刻停止过。当年女娲的补天工程其实也包括了治水:补天,不正是为了止住天漏,不再下雨吗?黄帝时,大战蚩尤,请旱魃来对付蚩尤的风雨浓雾,也可以看成是与自然灾害抗争。然而,直到禹的出现,或者说人类发展到禹的时代,才使我们看到这种抗争真正有了现实可行性。补天,让天不再下雨,只能是美好的童话;用旱魃的旱灾来对付涝灾,寄希望于老天三百六十度急转性子,也只是可怜的哀告祈祷,无论你有多虔诚,还是得听天由命。
如此艰辛,终于在大地上又一次站稳了脚,当然要更加珍惜。于是,从此,天人之间的争斗隐到幕后进行,另一场也从来没有停息过的争夺成了这个舞台上的重头戏:那就是人类自己对土地的争夺。
也许刚放下铲斧的大禹没喘几口气便投入了这场战争。从当年神农伐补遂到黄帝伐逐鹿擒蚩尤,到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现在该由禹伐共工、有扈氏了。
战争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从这片土地上驱逐妨碍耕作的捣乱分子,这种观念是十分明显的。如儒典里时不时提到的“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投畀豺虎”,明明白白地说了:要把捣乱分子摒弃到遥远的四边,放逐到沼泽森林等蛮荒之地,与野兽为伍!
这些战争的性质和后世历代王朝都得谨慎地抵御游牧民族的骚扰一样,目的都是为了守护这块世代传承的大地、田园。
这种对田园的依赖和守护,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遗传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恋土情结。都说中国人安土重迁,迫不得已背井离乡,都要凄凄惨惨地挖一捧故乡的土,精心包好,随身带了方才一步三回头地上路。从此无论漂泊到哪里,想家时取土来看了,放在鼻端嗅嗅,晶莹的泪花中便似乎又袅袅升起了童年的炊烟。
这种感情往往是方舟上诺亚的后人所难以理解的。永远不肯下船的海盗就是他们很著名的一支后代。
这种感情,已经渗透到了我国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中。如儒家推崇的君子,就应该是像大地般广博沉稳宽厚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自然,传统医学也被深深烙上了这个印记。
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一是五行学说,就是用五行来概括说明人体各脏器的功能。中医认为,人体有两个基础是最重要的、是根本:一个是先天之本,肾;另一个是后天之本,脾。一个人健康与否,与这两者关系最大。虽然先天之本,也就是天生体质是极为要紧的,但更关键却还得是脾。有句老话,先天不足后天可补,指的就是即使天生体质虚弱,如果经过合理的调养,也是一样能够强壮起来的。假如自恃父母所赐的本钱硬,起居无节胡乱挥霍,忽视养生,那么这人的寿命往往还不如一个先天不足的长——不是有句俗话,破鼓倒经敲吗?
肾,五行属水;脾属土。肾,主一身之水,输布调节全身水液;而脾,消化吸收饮食精华的同时,运化水液、统摄全身之血。一切水湿之疾,都与脾功能失调有关,“诸湿肿满,皆属于脾”。
水,是先天的,我们无法选择;而土,却是后天可以改造的根本。所以土是根本中的根本。后世医家有一支便专门发挥此理,全力培土,被称为“补脾派”。
这个建立在保土疏导上的中医理论,正是在人体内部进行的治水方针——诸湿肿满,不正是发生在人体内部的洪涝灾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