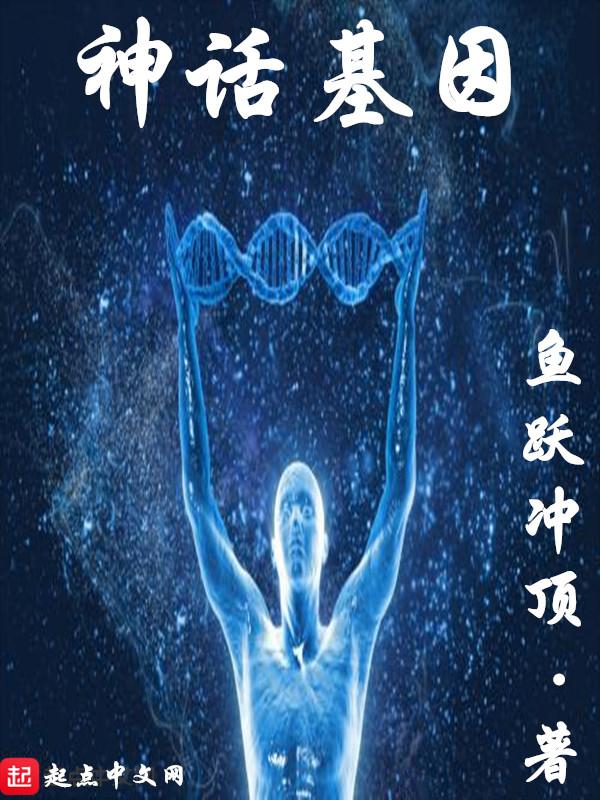奇书网>本草春秋是什么 > 禹余粮(第1页)
禹余粮(第1页)
禹余粮
——守土与治水
隔行如隔山。药书的文字半文不白,四气五味寒热归经,生涩拗口,竟似满篇隐语黑话,往往令外人云遮雾罩,头痛不已。
但读药书也有窍门。正如画龙点睛,其实一味药的功效,仅凭药名也可揣摩出几分。比如叫泻叶,自然能泻下通便;称首乌,无疑能补肝肾乌须发;夜交藤可改善失眠;决明子、夜明砂能清热明目;益母草必是妇科良药;续断、骨碎补应该主治跌打损伤;伸筋草、千年健,想来长于祛风湿、强筋骨……
禹余粮呢?
初学者乍一看到这个名称,第一反应大都会将这药归纳为收敛固涩一派,专门用来治理人体内的水液失调,如泄泻痢疾之类。
八九不离十。教科书上的禹余粮,指的是种叫作褐铁矿的天然矿石,能涩肠止血,用于久泻久痢、妇人崩漏带下。不过,本草典籍中,此名之下还另有一种药,是植物,叫土茯苓,却是青霉素发明之前治疗梅毒的主药。这其实有些诡异,毕竟梅毒这风流病是明代才传入我国的,和大禹八百竿子打不到一起,怎么也得了这个名目呢?
但如若再仔细一看,土茯苓还有另一个作用:解毒除湿利关节,可用于风湿筋骨挛痛、疖疮痈肿等,此时便恍然大悟,这就又和禹挂上钩了。
剥离了神秘面纱的大禹,可能是有风湿痛的。后世道人斋醮做法时诡异的步法,称为禹步,被附会成创自大禹,其实这反而透露了大禹可能并没有多大神通,只是个凡人,所以终于得了风湿——长年水中作业的人不可避免的职业病。这在古籍中也有记载,如先秦《尸子》云:“(禹)生偏枯之疾,步不相过,人曰禹步。”走路后腿跟不上前腿,拖着一瘸一拐,正是严重关节炎的症状。
但无论矿物的禹余粮还是植物的禹余粮,药名的来历却如出一辙,都说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吃饭时或是来不及或是一时吃不完,留了下来,便化成了这一种药。
如此上古神物自然应有几分神秘。确切的收涩疗效外,多有医家称此石久服能不饥,轻身延年;令人多力气、耐寒暑,负担远行,身轻不疲——
就像那时大禹风尘仆仆奔波治水那样。
有学者认为,远古神话传说的女娲补天也好、大禹治水也好,其实都是用洪水隐喻着一个作为原始人最可怕而又必须经历的劫难:生育时的生死危机,血崩或是难产。
这个说法如果联系禹余粮的功效——可用于妇人崩漏带下——似乎倒也能说得更圆。然而不管如何牵连论证,这个现实是不容抹煞的:我们的这个星球上,在人类的初年,确实发生过一场可怕的全球性大洪水。
证据是我们自己的古籍上比比皆是的记载,如《孟子》“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之类;还有考古学家气象学家地质学家生物学家的研究,说大约多少多少万年前,地球气候变暖冰川消融导致洪灾云云;更有力的证据是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在原始神话中都提到了人类初生之时经历过一次濒临全体灭绝的大洪灾。
这次洪灾甚至写入了《圣经》,那就是著名的诺亚方舟的传说。
尽管各个民族信奉的神灵不同,洪水传说却都大同小异,都是硕果仅存的善人靠着对神灵的虔诚得了启示,准备好大船或是有神龟相救,漂浮了若干天,等到浩劫过去后,重新开始生活。
而我们的传说却是大禹治水。
这传说相比漂流逃难多了一种悲壮,多了一份主动,但也总能给人一个疑问:
我们的先民难道不能也像其他民族一样,躲上一艘船,避开洪峰,等着上天息怒吗?何必要一代代苦苦在泥泞中挣命呢?
应该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的先民已经离不开这片土地。
或者说,世界上其他民族对土地的留恋,都没有我们的先民那么强烈。《圣经·创世纪》有段话,应该能揭示一二。上帝在降下洪灾之前,规定了诺亚能带上一起逃难的物种,“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于是“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地到诺亚那里,进入方舟”。查遍此节,可有一词一句提到另外一类生物的种子:庄稼?
很明显,当时的希伯来人,主要还靠游牧为生,他们可以离开一处已经不适宜生存的环境,去寻找另一处;而我们的先民,大洪水来临时却已经进入了农耕文明——有了田地,有了家,还能轻易抛弃家园远走他乡吗?
大禹时期华夏民族已经进入农耕文明,这是学者们早已证明了的。当然,还有一个简单而有力的佐证:教人学会耕作的神农,早于大禹很多代。
其实农耕相比游牧、狩猎,要辛苦得多。著名历史学者美国人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引用另一学者的话说:“大量的资料表明,狩猎、采集者不仅有充足的实物,还享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事实上,比现代工人、农民、甚至考古学教授所享有的还要多得多。”
辛苦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选择农耕,便意味着从此被牢牢束缚在这片土地上,失去了狩猎、采集的灵活与潇洒,即使与游牧相比,也失去了不少的剽悍和迅疾——禹和他们的祖先,为何选择了这条艰辛的道路呢?
很简单,农业,只有农业,才能提供大量稳定可靠的食物,才能更有效地壮大部族。农业出现之前,人类对付无常自然的办法只有一个:根据生存条件自我调节人口,类似于后世的量入为出。而调节的办法却是残忍的堕胎、停止哺育或者杀死新生儿。农业的意义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话说,是“农业革命导致了又一次人**炸”。他算了一笔账,人类逐渐进入农业文明后,“一定地区的食物供应量比过去更多更可靠”,所以,距今10000年至2000年的8000年中,人口总数从532万剧增到13300万,与之前100万年中的人口增长数比,约增长25倍。
所以进入农耕,绝对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我们庆幸我们有那么适合农业的气候,我们感激出现过神农等一些伟大的观察思考者,我们自豪我们曾经遥遥领先——但,进步也要付出代价:我们这片古老的大地,面对洪水时,要保卫的已经不再只是一条条生命,还有那富饶的田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