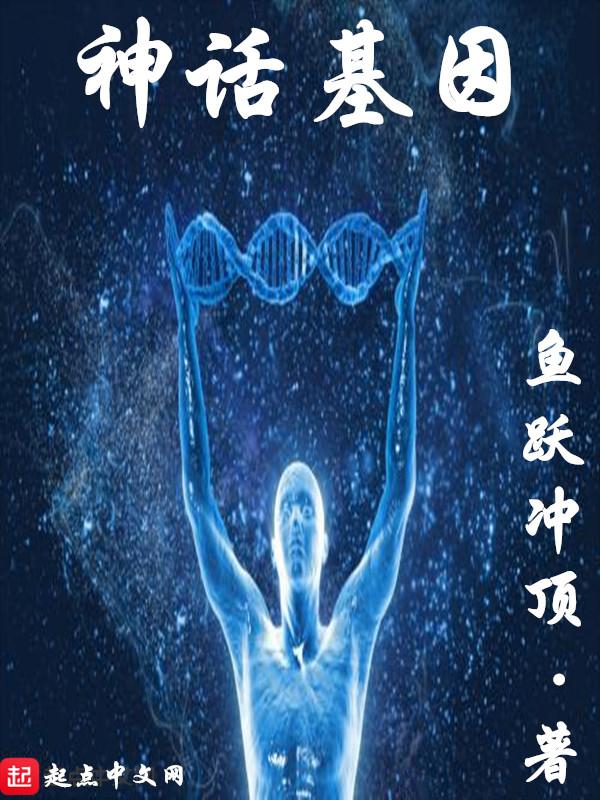奇书网>四合院开局认亲傻柱 > 第38章 移情別恋韦东毅要把李秀芝领回家(第1页)
第38章 移情別恋韦东毅要把李秀芝领回家(第1页)
韦东毅停稳吉普车,带著几分钓鱼未竟全功的遗憾,拎著沉甸甸的鱼桶,右手提著那根祖传的、此刻显得格外沉重的紫竹钓竿,嘴里哼著不成调的小曲,慢悠悠地往四合院走。
刚跨进垂门,迎面就撞上了下班回来的三大爷阎埠贵。
“哟,东毅,今儿个这么早就收杆了?”阎埠贵推了推眼镜,目光精准地落在韦东毅手里那个显得比往常“轻飘”不少的鱼桶上,语气带著惯有的算计式关切,“这……收穫瞧著可有点稀鬆啊?”
韦东毅脚步一顿,没好气地把鱼桶往地上一放,抬脚展示那只被河水泡过、鞋帮还破了个大口子的布鞋:“別提了三大爷!今儿点儿背,撞上条大鲤鱼!估摸著少说也有二十斤开外!那劲儿大的,差点把我拖河里去打窝!您瞅瞅我这鞋,赔大发了!最后……唉,线切了!”
他一脸肉痛地摇头,仿佛那跑掉的不是鱼,而是白的银子。
阎埠贵盯著那只破洞布鞋,一个没忍住,“噗嗤”乐出了声。
意识到不妥,他赶紧绷住脸,摆出一副感同身受的惋惜表情,咂著嘴:“哎呦喂!那可是太可惜了!这么大一条鱼,卖给轧钢厂食堂可值不少钱!真是亏大了,亏大了!”那语气里,遗憾有之,但更多是掩不住的幸灾乐祸。
韦东毅懒得跟他磨牙,扯了扯嘴角,拎起鱼桶鱼竿,留下一句“可不是嘛”,便径直朝中院走去。
水池边上不见秦淮茹洗东西的场景。
路过贾家时,他眼角余光扫过那扇在夏日午后依旧紧闭的房门,心头掠过一丝冷笑。
看来刚才那番“掏心掏肺”的威胁,效果拔群。
秦淮茹是真被戳中七寸,老实缩回去了。
这感觉……让那条跑掉的鱼王带来的鬱闷都消散了几分——果然,让討厌的人不痛快,自己就痛快了!
……
翌日清晨,易家。
韦东毅难得地站在梳妆柜前仔细捯飭了一番。
崭新的白衬衫熨得笔挺,深蓝色的工装裤稜角分明,脚上蹬著一双擦得鋥亮的棕色小牛皮鞋——这在六十年代初可是稀罕物。
他甚至还特地把头髮洗得清爽蓬鬆,整个人显得精神奕奕,容光焕发。
“东毅今天可真精神!”一大妈围著韦东毅转了两圈,笑得合不拢嘴,眼里满是骄傲。
今天可是韦东毅转正成为国家正式干部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意义非凡。
在她看来,这比过年还值得重视。
在易中海和一大妈欣慰的目光中,韦东毅发动了吉普车。
副驾坐著易中海,后座则“顺理成章”地塞进了二大爷刘海中。
这胖子昨晚下班瞧见吉普车停在胡同口,就一直在易家门口“无意”地徘徊,那点蹭车的心思昭然若揭。
韦东毅懒得为这点小事计较,索性做个顺水人情。
车子驶入轧钢厂,停在后勤部楼下。
走进採购三科办公室,迎接韦东毅的是一张张热情洋溢的笑脸。
“恭喜啊东毅!正式干部了!”
“韦干事,以后多多关照!”
“东毅兄弟,转正大喜!”
同事们纷纷道贺。韦东毅笑容满面地一一回应,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掏出几大把包装鲜艷的硬——这是一大妈特意准备的喜。
“同喜同喜!来来来,吃!沾沾喜气!”他大方地分发著,办公室里顿时充满了喜庆的甜味和欢声笑语。
刚坐下泡好一杯热茶,同事们就呼啦围了上来。
话题自然离不开他上周那趟“传奇”的塘沽之行。
“东毅,快说说,海边啥样?真像书上写的那么蓝?”
“听说你弄了一车海鲜回来?都有啥稀罕玩意儿?”
“那渔村的人真拿鲍鱼当饭吃?”
韦东毅绘声绘色地讲起渔村的见闻、咸腥的海风、退潮的滩涂,还有那朴实热情的渔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