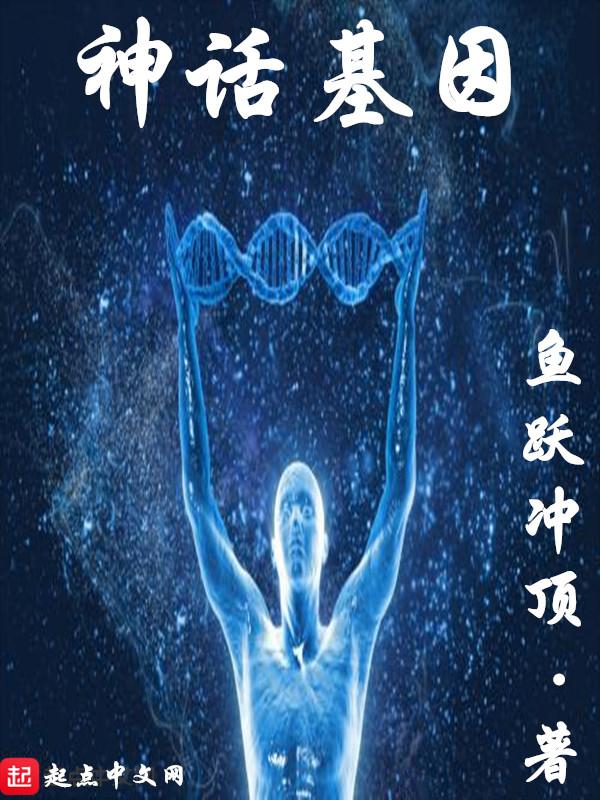奇书网>被迫复出后我笑了 > 第44章(第2页)
第44章(第2页)
有人进来扶了虞然一把,虞然冲了下脸,总算缓过来。
对方车有保险,撞到许木容后第一时间把人送到医院,也表示了会赔偿医药费。
虞然清了清嗓子,对许木容逆行跟他表示了歉意,三言两语地和解后,对方离开了。
病房里只剩下许木容和虞然。
虞然捂着痛得要裂开一样的脑袋,在头发里摸到一个鼓包,好在没有流血。
“撞哪了?”许木容手上打着点滴,仍然从床上起来,要去看虞然的伤。
虞然清楚地看到了,许木容看向他关切的眼神里,原来有这么明显的死灰。
原来许木容准备着一死了之,已经准备了十年。
虞然反手扶住许木容的胳膊,把她扶回病床上。
这次意外地没有发生意外,下次是什么时候。
是不是他一个没看住,许木容转头就会再去寻个意外。
虞然深喘几下,在病床边蹲下,从口袋里把那叠意外险保单掏出来时,手指还有些抖。
他当着许木容的面把保单打开,拿出手机拨打上面的客服电话。
在他跟客服说出终止参保时,许木容的脸色终于崩塌,她伸手要去抢虞然的手机,去夺虞然手里的保单。
但快五十岁的许木容怎么可能抢得过比她高了一头的虞然。
虞然轻而易举地躲开并按住她,打完一个电话,又翻开下一张,继续打电话退保。
发现自己根本阻止不了虞然,许木容面如死灰地停下挣扎,眼泪不断涌着落,渐渐地哭出声。
虞然漠视她的哭声,甚至一直保持礼貌客气的声调,一一地跟保险公司确认退保。
直到打完最后一个电话,虞然按着膝盖站起来。
他缓缓搂了下许木容,微颤着温声说,“妈,别再做傻事了,已经没用了。”
一向温婉柔弱的许木容,尽管绝望崩溃,情绪也只是像撕开了个细细的口子,哭声一直低低缓缓的。
但一个人撑着扛着,压抑了十几年的情绪,像是从这个小口子,一时半会难以倾泄。
许木容哭了很久,她坐在病床上,从下午到晚上眼泪一直没有停过。
虞然没有劝她不哭,也没有逼问她,除了中途出去买晚餐外,他就静静地在一旁陪着她。
其实从看到那封遗书开始,虞然都是想不通的。
就算鹏城生活成本确实高一些,但他可以不用每个季度都换最新款的运动鞋;可以不用参加那些需要额外负担费用的研学活动;可以不用每个节日都要收到充满仪式感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