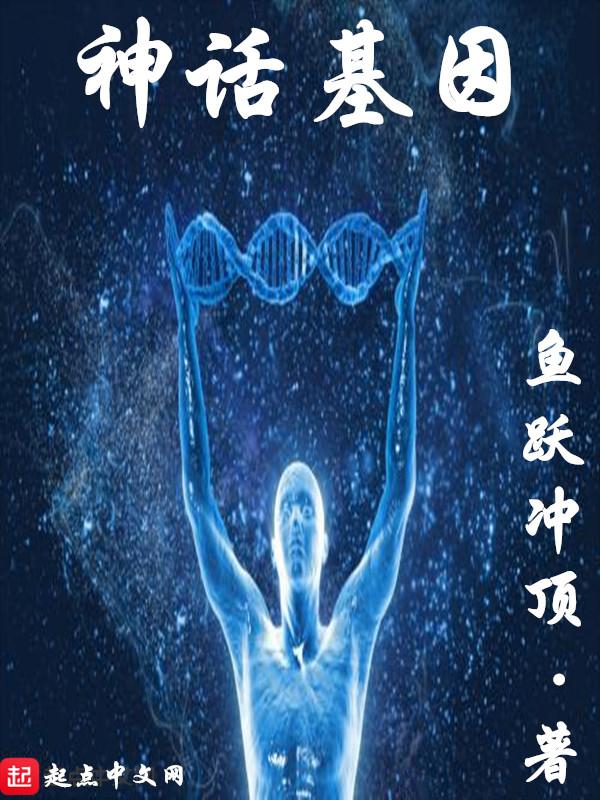奇书网>朕要在线阅读 > 第二百四十五章 诊所(第1页)
第二百四十五章 诊所(第1页)
社区诊所的灯光白得晃眼。
顾云舟低著头,活像个被班主任揪到办公室罚站的小学生。
面前,还是那位熟人赵医生。
赵医生推了推老镜,看看手里的病歷,又看看床上掛著水的萧青鸞,最后把目光投向了顾云舟。
“又是你们俩。”
顾云舟的头埋得更低了。
“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赵医生痛心疾首,“到底是怎么回事?上次来,小姑娘营养不良。这次倒好,直接给我整了个重度营养不良加脱水,高烧快四十度了!”
“再晚来半小时,人就得休克了!你知不知道!”
顾云舟嘴唇动了动,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知道个屁。
他只知道在物流园里跟传送带死磕,把自己累成狗,以为这样就能把脑子里的事儿都给忘了。
结果家里这位倒好,直接玩了个更大的。
“吵架归吵架,怎么能不吃饭呢?”赵医生嘆了口气,“小伙子,你也是,看著挺老实一人,怎么能让女朋友饿成这样?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
顾云舟:“……”
我不是,我没有,別瞎说。
他想解释,说冰箱里一半是她自己买的菜,说她压根就没动过。
可这话怎么说得出口。
难道跟医生说,我们俩在玩一种很新的冷战,她用绝食来对我进行精神攻击,我用搬砖来对自己进行物理超度?
医生听了怕不是直接掏出手机打给精神病院。
算了。
毁灭吧。
他默默地听著,把所有训斥都咽进了肚子里。
行吧。
我全责。
病房里很安静,只有输液瓶里药水滴落的轻响。
萧青鸞躺在床上,烧得通红的小脸在苍白的枕头上显得格外脆弱。
顾云舟坐在床边,像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
他先是伸手,把被子的一角掖得严严实实。
嗯,不能漏风。
然后他拧开温水瓶,倒了点水在盆里,仔仔细细地把毛巾浸湿,再拧乾。
温度得刚刚好。
他把毛巾叠成方块,轻轻敷在萧青鸞的额头上。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熟练得让他自己都感到害怕。
我上辈子难道是个金牌护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