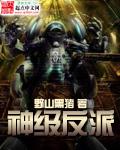奇书网>清末新政创办的学堂 > 四排满演说(第1页)
四排满演说(第1页)
四、排满演说
1903年旧历元旦的东京清国留学生会馆排满演说,是具有一定政治影响的事件,曾在留日学界和国内引起不小的反响,预示着革命热潮即将来临。但目前史学界关于此事引以为据的两条主要资料,即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和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的有关记载,却有不少失实之处。两人所记如下:
壬寅、癸卯间,东京学生杂志风起,高谈民族主义,倡言革命,而讳言排满。先生(即孙中山)忧之,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匣剑帏灯之宣传无益也。”召成禺及马君武赴横滨曰:“吾朋侪中有勇气毅力,莫如两子,余非依违两可,即临阵脱逃者。民族革命,要在排满,舍排满而言民族,其能唤起国内人民之清醒乎?今有一机会,元旦留学生团体,欢迎振贝子,公使蔡钧、监督汪大燮皆在,开演说会。禺生与君武,能提出排满二字,以救中国,大放其辞,自能震动清廷,风靡全国。禺生楚人,君武原籍湖北蒲圻,彼亦楚人也。身家性命功名富贵之徒,不足与言亡秦之事矣。”元旦日,莅留学生会馆,首由马君武登台演说排满,声泪俱下,予继之。当日全国通电,皆言刘成禺,而不言马君武,故予一人获罪。[1]
癸卯元旦,各省学生在骏河台留学生会馆举行新正团拜礼,到者千余人。清公使蔡钧亦到。时有广西人马君武、湖北人刘成禺先后演说满洲吞灭中国之历史,主张非排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不足以救中国。慷慨激昂,满座鼓掌。满宗室长福起而驳之,为众呵斥而止。事后刘成禺因此被开去成城学校学籍,不许入士官学校。长福由蔡均力保,得充横滨领事。[2]
这两条记载,乍一看言之凿凿,仔细推敲,参诸其他史料,则难以奉为信史。
1。演说时间及与会人数。冯、刘二人称演说发生于癸卯元旦,即1903年1月29日。近年出版的有关著作均沿用此说。但当时出版的《选报》第51期所发详细报道《满洲留学生风潮》记载:“新正初二日,东京留学生会馆大集同学,兼请国人到馆演说。”据此,则演说的具体日期是1903年1月30日。《选报》的主持者与留日学界关系密切,并在东京设有访事人,而且该文系辑录《苏报》等各日报的报道而成,内容多为来自东京的现场消息,并非捕风捉影的传闻,因此可靠性较高。当时有些报道标以“元旦会馆演说”,应系泛指。
至于与会人数,冯自由说有一千余人,而《选报》记为五六百人。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中的题名录统计,当时中国留日学生总数为642人,[3]除去未到会者,估计有600人与会,《选报》的报道是准确的。
2。演说者。据冯、刘二人回忆,当日演说排满者为刘成禺、马君武两人。然而根据当时的报道,发表排满演说者只有马君武一人。《选报》所载《满洲留学生风潮》一文,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大会的过程:
时有广西马某在座,众首推之。马登坛力数满人今昔之残暴,窃位之可恶,误国之可恨,应如何仇视,如何看待。座中除三十余名满人外,约有五六百人皆鼓掌。逾刻满人互相语曰:“宁送朋友,不与家奴,诚吾人待汉奴不易之策也。”马退而湘人樊锥继之,言:“中国患在外而不在内,满虽外族,仍为黄种,不宜同种相仇,与人以鹬蚌之利。”满堂寂然无和之者。最后则汪大燮续演,略谓:“诸君皆在学年,正宜肄力于学界。语曰:思不出其位。吾敢以为诸君劝云。”
据此,这次大会共有3人演说,即马君武、樊锥、汪大燮。后两人的演说,目的在于直接或间接反对马君武的观点。此外,《黄帝魂》一书中的《满学生与汉学生》也说:“元旦学生会馆演说,有某生者,主张排满”;陈天华的《狮子吼》描写道:“留学生在日本,有一个会馆,每年开大会两次。有一回当开大会之时,一人在演台上,公然演说排满的话,此时恃着人众,鼓掌快意。”[4]可见当天演说排满的只有马君武一人。马虽与梁启超及《新民丛报》关系十分密切,却怀抱革命宗旨。他利用时机鼓吹排满,是十分自然的事。其演说的具体内容为:
一若满之为满,为今天下所当共排。其意盖谓满人之饮食宫室何所取资,曰惟汉人是赖。满人之衣服男女何所取资,亦曰惟汉人是赖。汉人日竭其出作入息、胼手胝足之勤劳,以供给此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之辈,于心已不能平,况又削汉膏腴以保彼晏游之地,割汉行省以赎彼根本之区,今又以三十九年之摊还四百余兆之赔款,斫骨削肉,饮血啜脂,福则惟满独优,祸则惟汉独受,天下事之至不平者无过于此,盖欲不排乌得而不排!间尝反复其旨,大抵亦本自由平权等说而来。[5]
至于刘成禺,则没有在会场上演说排满,而是乘势响应,“在《湖北学生界》畅说人种,与元旦议论颇多疑似,故亦为满学生所忌”[6]。刘成禺的文章题为《历史广义·内篇》,连载于《湖北学生界》第1、3期上,其中第1章即为《人种》。该文称“秦汉以后之历史,真可谓世界上空前绝后一部大奴隶史也”,“南北朝辽金元诸史,所述某帝天性仁厚重儒术,某帝英武过人,勘定大敌,宣扬赞叹,几有认外种人为吾之祖若宗者。无怪乎奴隶根性养之数千年,而流毒孔长也”。文章表面虽然主要针对列强,但隐含排满倾向,甚至对保皇派的拥帝也隐加批评,认为:“无论他种人有华盛顿之君,有极自由之政,终不让彼窃我公产,侵我民权,污秽我人种的历史上之人物也。”[7]
由于马、刘两人同时在不同场合发表过排满言论或文章,又出现于同一报道之中,容易令人混淆。1903年《汇报》的一篇论说已将演说者误记为刘成禺,孙中山在《革命原起》中也只提及刘成禺的名字。后来刘自觉不妥,撰文为马君武表功,然而有意无意间又把自己加了进去,结果刘、马之误部分得到纠正,演说者却由一人增为两人,真是越理越乱了。另据1903年7月6日章炳麟《狱中答新闻报》,邹容“元旦演说,已大倡排满主义”[8]。但当时章并不在日本,事后传闻,不足为据。
与此有关的问题,是对马君武、刘成禺两人的处理。刘成禺自称:“练兵处奏清廷,廷寄不准学陆军入士官学校,抄籍武昌家产,逐出东京。后由汪大燮赔款六千元赴美,与学生会馆干事订立条约,刘成禺一人不入士官,易自费生二十人学陆军,方声焘等皆条约所交换。办理此案,则蔡锷、蒋百里、胡文澜诸人也。”[9]参照其他资料,亦属夸张之词。首先,刘成禺并未立即离开日本,拒俄运动兴起时,他参加了5月成立的学生军和军国民教育会,后又往来于上海、东京间,直到1904年5月以后,才应聘前往旧金山任《大同日报》主笔。
其次,清政府并无以刘成禺交换20名自费生学陆军之举。据报载:“东京成城学校卒业生湖北刘君成禺为满洲同学所持,不许入联队进士官学校。”“日人以信用支那政府为外交主义,亦允其请,故刘君竟无可设法。”[10]部分满族学生还策动当局,不准保送汉族学生学习陆军,“今汉学生不能入陆军学校,方信此事非讹传。湖南提督之子亦不得入陆军学校。今应有二十余人由成城学校卒业升入联队者,学生中纷纷传说,谓监督得有政府电谕,不许保送汉学生入陆军学校”[11]。在控制留日学生学习军事的问题上,清政府已多次与留学生发生冲突,这次同样激化矛盾。汉族学生闻讯,“全体哗然,各开同乡会以牟救济”[12],“东京满汉冲突甚为剧烈”[13]。在留学生的坚决斗争下,清政府不得不遵守1902年7月成城学校入学冲突后达成的协议,继续保送汉族学生。
再次,清政府处理的重点是马君武,对刘成禺则只是不准其升入联队。当时马君武有意转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某某两生并胁学生监督汪大燮,使不许送主张排满之某生入成城学校”[14]。元旦演说事令汪大燮十分恼怒,指马君武“昌言无忌,性气尤劣,正思有以治之而无术”,暗中指使汪康年“设法令其母一控,由江南咨敝处押遣回国”。但又担心马君武与日本华族女学校校长下田歌子有交,“设办不得手,反致生事”,嘱咐汪康年“需告知日本领事转达日外部,至以为要”。并再三叮嘱:“如办马事,能觅一湘人与午帅(即魏光焘)处通气,方能顺手。第一不可泄漏,第二要使日本人不生阻力,第三要办得神速。”[15]
不过,此事办起来颇多窒碍,不易措手,汪大燮又转而试图化解矛盾。不久,他函告汪康年:“马君武其人通英法文,笔下亦颇好,故前劝其赴欧美学,居然劝动。现已于前月下浣动身,大约日内可到上海矣。既离日本,前说即可不必,恐上海一有风声,反迫其东来,转多事也。此间事亦非用威所能行,寄居人国,凡一切押解驱逐之说,皆不能行,所谓无恩可怀,无危可畏,是以无法无天如此。细察情形,即国家能用一二人,亦尚无益。缘其滋闹之人,必不可用,亦自知必不见用,其喜事仍如故也。深思之真无善法耳。”[16]
作为留日学生的主管,汪大燮煞费苦心地对付一介书生,不仅表明清政府对留日学界日益增长的潜在威胁感到忧心忡忡,而且显示他何等重视马君武演说其人其事的影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马、刘两人在此事件中角色地位的差异。刘成禺书多有不实之词,此亦一例。
3。演说的策动者。刘成禺称这次演说的策动者是孙中山,并详细引述了孙中山向他和马君武面授机宜的谈话内容。可是,唯其情节愈详则漏洞愈多。孙中山是1902年12月初离开日本经香港转赴河内的,[17]此时距癸卯元旦尚有近两个月的时间,孙中山布置得如此周详,本身已属可疑。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元旦团拜演说已成通例,可以预先计及,清贝子载振去日本一事,却无论如何是孙中山当时不可能得知的。
1902—1903年间,载振曾两度去日本,第一次是1902年9月,为处理成城学校入学事件,调解留学生与公使蔡钧的冲突。他于9月5日在骏河台留学生会馆召集成城、弘文、同文、清华、高等商业等校和帝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400余人,鼓吹了一番所谓“爱国”观。9月24日回国。第二次去日本,是在1903年4月底至5月底。此番东渡,是为了参加日本在大阪举行的劝业博览会,并未与东京留学生会面。孙中山既不可能在1902年12月上旬就得知载振的行止,而载振也不可能出席1903年1月30日的东京留学生新春团拜。此外,东京留学生杂志风起的情况,出现于1903年年初,孙中山不会在1902年就对其中弱点进行针砭。可见这次演说虽然很可能受孙中山的思想影响,但直接策动者却不是孙本人。
4。演说的反对者。冯自由《革命逸史》及其他一些记载称,当马君武演说之际,满族学生长福从座位上跳出来大肆反对,并因此得到清政府的青睐,事后由蔡钧保荐,当了横滨领事。《苏报》报道却说:“今年元旦留学生会馆演说时,有满人长福闻而鼓掌。某满人怒之以目,迨回寓时将责福曰:‘彼毁我满人,汝何鼓掌耶?’某曰:‘吾未闻其有毁我满人之语也。其所言善,吾安得不鼓掌?’”[18]据此,长福非但没有跳出来反对排满演说,而且是满族学生中唯一与汉族学生一齐鼓掌表示赞同的人。两种记载,截然相反,一个是面目可憎的跳梁小丑,另一个却是凛凛正气的进步学生,究竟哪一个是历史上真实的长福?
从各方面材料看,冯自由笔下的长福是被扭曲了的形象或张冠李戴。长福,字寿卿,清朝宗室,正红旗人。从1893年起以工部员外郎任记名外务部章京。1901年11月1日,他与25名满族学生东渡日本,进入弘文学院警务科,并担任学长。[19]留学前长福的思想状况,据他本人说,为官数年,昏昏扰扰,“甲午之役,渐知自愧,戊戌之变,寻知自强,至庚子之变,发奋投袂,游学东瀛”[20]。留学期间,他广泛阅读各种日译泰西新书,潜心研究日本近代政治制度,对日本官制及一切法度,知之甚详。[21]
1902至1903年间,各省留日学生纷纷发表劝同乡父老送子弟游学书,长福也慨然挥毫,撰写发表了长篇《劝游学书》,呼吁八旗青年子弟东渡扶桑,为国求学。文章劈头一句:“呜呼!我中国今日几不国矣!”接着历述鸦片战争以来种种列强野蛮侵略和清政府丧权辱国的惨痛事实,指出甲午战后列强掀起瓜分狂潮,使中国“门户尽失,无险可据,而列国惟以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公例,日寻竞争。我不筹防止之术,则举凡利权胥归乌有”。对于八国联军烧杀掳掠的骇人暴行,长福尤感痛心疾首,同时清醒地指出,列强所以没有瓜分中国,“非我有所恃,亦非彼有所不能也。盖以列强势均力敌,莫敢先发我”。提出中国必须矫正墨守成规、无爱国心及缺乏公德等三大弊端。他指责“吾国守数千年之旧学,于人群之关系无所发明”,主张讲求合群之义务,生团结之力,起进取之念,“推一己之利益而利益吾群”。作为一名北方士人,他对开埠通商后沿江沿海读西书,讲西学,以俾实用的情形表示赞赏,而批评直隶“读书之士则鲜知时务”,府县地方更“狃于守旧迂习”,只知排外仇教,“而不知别求自强之道,以立于列强竞争之世”。认为庚子拳变“有仇教之心,无克敌之术,其志固可嘉,而其愚则可悯已”。主张“经此大创,受此大辱,当如何卧薪尝胆以图报复,当如何呼号奋发以图自强”。
长福不仅具有当时一般进步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与救国切望,作为一名满族学生,他还对十八省同胞怀有深切的内疚与自责。他痛斥当此亡国惨祸临头之际,满人依然歌舞升平,昏庸误国,“愧我直奉八旗之人,犹复醉饱酣歌,安于扑塞固陋,而不知可危孰甚哉!”辛丑和局虽成,“重以赔款四百余兆,负债五十年。虽各省为我分负之,而我直奉八旗之人,问心能不耻乎?”为此,他呼吁八旗子弟源源赴东,“考求各种专门学术,迨至卒业回华,各就所长,施诸行事”,使“民德日进,民智日开,民力日厚”,这样才不致“无以对各省之为我同负巨款”,而“我直奉庶不为十八省同胞所见弃也!”[22]这封呼吁书洋洋数千言,饱含痛楚、悔恨与愤懑,爱国救亡**,跳跃于字里行间,比之于其他各省留学生所著劝游学书,独具特色。无怪乎《汇报》发表专文对此评论道:“宗室长福劝八旗子弟游学一书,觉其脑筋为独灵,其目的为最准,其思潮与心血尤为极膨胀而极热诚。然后叹八旗中莫谓无人,固自有识时务之俊杰在也。”[23]后来他还与一批开明旗人在京师创设北京进化阅报处,助人看报,并设讲报机构。
长福的政治倾向还不止于此,出于爱国救亡的动机,他甚至对排满革命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与支持。长福回国后,1903年6月3日,曾与外务部同僚孙宝瑄等人置酒纵谈。席间他说:“今日之游学日本者,多主张革命排满,或立会或演说。吾虽满人,决不斥以为非,引以为忧。”这与他在元旦大会上的表现正相吻合。所以孙宝瑄闻听之下,不禁赞叹长福“人极开敏,其脑中已灌注无限新理想”[24]。孙曾任中国议会干事,是官场士林中的新派人物,如果长福顽固守旧,不会得到他如此赞赏推许。
长福的激进倾向在行动上也有一定的表现。1903年5月,他和另外3位满族学生一起,毅然参加了革命色彩较强的爱国团体东京军国民教育会。该组织的13名干部中有8名是革命团体青年会的成员,而且刘成禺也是会员。如果长福在3个月前刚刚扮演了一个反对革命,人人唾弃的丑角,恐怕就未必会加入,也未必会被允许加入这个组织。
冯自由说长福因反对排满演说有功,由蔡钧力保,当上了清政府驻横滨的领事,则更是无稽之谈。长福的确在日本任过领事,但既非蔡钧保举,也不是在横滨,更不是由于反对排满演说而换取的赏赐。事实是,1903年5月中下旬,长福由日本启程归国,[25]在外务部任候补主事。1904年8月26日,横滨正领事请假销差,驻日公使杨枢以“横滨一埠,最称繁杂,侨寓该埠之华商多系广东人,商情颇难接洽。现值考察商务,呈报商部之际,该埠领事更须慎加遴选,以期得力”为由,举荐原神户正领事吴仲懿(广东人)调补横滨正领事,而让长福接任较次要的神户正领事一职。[26]蔡钧早已于1903年10月15日离任,此事与他毫无关系。[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