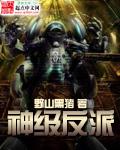奇书网>世事苍茫意思 > 关于老年的笔记之二(第1页)
关于老年的笔记之二(第1页)
关于“老年”的笔记之二
前面的一篇收在了《窗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一集中,一个小友读了,说是有点恐怖,何以将“老年”这题目作成了这样子!或许我那时还不够老。但“老年”本是生命中的一段,与其他任何一段一样理应受到关注。而我自己,则是到了身边的亲人渐渐老去,故去,才体验了发生在这生命途程中的温暖与严酷,且由己及人,想到了与“老年”有关的种种。
近读《顾颉刚日记》,其中有“老的定义”,包括如下几条:“一、身体各部分功能衰退。二、无抵抗气候变化的力量。三、不可能紧张地参加社会活动。”接下来说,“此必到了老年才会深切地感到,年轻人及中年人均无法领会”。以上文字写于1964年,那年顾氏71岁,所写均为他的经验之谈,“过来人”的切身体验。由顾氏晚年的日记看,他对于自己身体状况的关注,较吴宓更甚,尤以睡眠、排便为大端,几乎逐日记录。看起来失眠与肠胃疾患像是他的一大负担。吴宓的晚年日记,则几乎逐日地记自己的吃喝拉撒,种种病痛、不适。我猜想吴、顾日记中的如上内容,一定令年轻人难以卒读的吧。
顾氏多病,日记中反复诉说“老年之苦”。去世前一年的10月29日,在日记中说:“近日天气,忽阴忽阳,殆所谓‘满城风雨近重阳’者。此在年轻时读之,固觉其美,而今日则为胆战心惊矣。老人处境,真不能自己掌握矣。”实则顾氏的老年并不枯槁。顾为苏州人,或许得自早年的陶冶,日记中的顾颉刚,爱花成癖。1964年5月5日:“怀念江南之春,不胜神往。”“藤萝花近日大开,朗润园中不愁寂寞矣。”5月10日:“近日园中盛开者为刺梅之黄花,藤萝之紫花,濛濛扑面者为柳絮。”5月18日:“近日校园中仅有刺梅及洋槐花未残耳。绿肥红瘦,又是一番景象。”5月19日:“始闻布谷鸟声,委婉可听。此鸟所鸣,苏州有‘家家布谷’、‘家中叫化’两说,徐州有‘烧香摆供’一说,此城中所不闻。洋槐花落,镜春园中殆如以氍毹铺地,使人足底芬芳。”1965年4月19日记往北海“饱看春色”,说自己“最爱者碧桃,为其丽而端。其次丁香,为其芳而淡。又次则海棠,为其艳而不俗。若榆叶梅,则过于艳冶,品不高,花已萎而不落,又使人生憔悴之感也”。同年5月7日观赏景山之牡丹,说:“举凡姚黄、魏紫、宋白、王红诸名种皆备,置身其间,浓香馥郁,洵可爱也。”你应当想到,那已经是“文革”前夜。到风暴将至的1966年的4月3日,顾氏在香山路上,还欣欣然地看“白者李,赤者桃,淡红者杏,吐露在松柏间”。同月12日,因“花事正浓”,“徘徊不忍去”,陶醉在香山的花海中。当着饱受冲击之后,1971年环境稍宽松,就期待着公园开放,使自己得以“徘徊于林石间”(8月23日。以上引文均见《顾颉刚日记》第十、第十一卷)。顾颉刚不如吴宓的健饭,食欲旺盛,对寻常美食津津乐道;也不像吴的随遇而安,对“待遇”多有不满,却酷爱花木,对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纤敏的感受,于此更有文人习性。他们也就各有自己的排解方式,多少避免了被不健康的情绪所伤害。
由日记看,梁漱溟对公园作为环境情有独钟,且足甚健,京城各大公园似无所不至,散步,习拳,与友人聚谈,饮茶,用餐,兴致盎然。因了情趣,这老人会不惮烦地寻觅某种食物,无论水果还是京城小吃(比如面茶)——是并不奢侈的享受(梁氏日记见《梁漱溟全集》第八卷)。
顾颉刚、吴宓“文革”中的遭遇,因日记书信的面世已广为人知。但若仅由老人生存状况着眼,你不妨承认,无论吴、顾这样的知名人士,还是你我普通知识人,较之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中的老人,已经算得上幸运了。曾经有剪报的习惯,至今也偶尔一剪的,就有如下剪得的片段。
《南方周末》1998年7月6日署名陈冀的文章,同年《文摘报》以《七旬老妇经营**业只为棺材本》为题有如下摘录:
四川省安县破获的一起建国以来最大的容留妇女卖**嫖娼案,已查实的76起个案发生在秀水镇鸡市街小巷里一间没有窗户、设备简陋的十平米大小屋子里。76岁的房主张秀贞,把它经营成了一个**窝。
每当暗娼带着客人来到,风烛残年的老妇人就颤颤地用唯一的磁杯泡上茶,放在靠床的小方桌上,然后坐到门口望风。之后,她会收到嫖客2元、3元、5元不等的“床铺费”。一年里,12名暗娼在这里接客76次,张秀贞收入大约292元。
…………
秀水派出所审查一名嫖宿人员时牵出了张秀贞。警方从张家墙角的米坛子里搜出了她292元赃款。
在提审室里,老妇人担心那292元钱要被没收竟大哭起来:“那是我的棺材本啊!”
张秀贞一生未曾生育,儿子是丈夫的,因为家境贫寒做上门女婿去了外乡。五年前,张秀贞的老伴过世时儿子回过一次家。丧事办完,儿子拉走了张秀贞放在床下的三根圆木,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张秀贞从此落下一个心病,棺材就是她一生努力的回报,死后一口好棺材,几乎就是一生善终的全部保证了。然而她最终没能要回那三根圆木。
我未核对原文,不知上述摘录能否反映该文的原貌。我得承认,这故事让我感到的不是嫌恶,而是无边的荒凉。上述报道中老人处境的绝望,使得人们面对容留卖**嫖娼这样的罪恶,也不免心情复杂。
2001年第2期的《法制与新闻》所刊《“孤儿寡母村”见闻》(作者山晓),记述了一位乡村母亲的故事。那是鄂西北大山深处的竹山县。当年这个贫困县的农民与城镇居民往往到河北、河南、陕西的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私营小矿窑挣血汗钱,且往往一个村子、一个家族集体出动,一旦发生矿难,对于相关家庭以至村落,就是灭顶之灾。这个名叫李玉兰的老人,在矿难中失去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婿。
这日,漫天的雪花伴随着落叶在大山中飞舞,李玉兰老人独自背着一个背篓在公路边守候着。嘴里念叨着:没啦,都没啦……
矿难后女儿、儿媳不堪重负,相继出走,儿媳还带走了唯一的孙子。
两位老人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他俩常常在黑夜里哭喊道:吃人的矿窑啊,现在日子咋办啦……白天,他们常会神经失常般地到几公里外的公路边,望着一趟趟班车来来往往,希望总有一天奇迹会出现……
我没有读到过较之这篇更令人沉痛的关于“矿难之后”的报道。这一对老人在他们的衰暮之年所承受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它彻底地摧毁了他们残余的生活。人生至痛,无过于老年丧子,且失去了仅有的生活保障与生存的理由。对于这样的绝境,很难想象当时的地方当局能够施救。
近年来发生的矿难中,有精神失常的母亲拨通了井下早已身亡的儿子的手机,欣喜若狂,一次次地拨打,直至将电耗尽的故事。在“孤儿寡母村”之后的变化,是倘无瞒报,死者的亲属可以指望稍高的赔付,但又有什么能消除丧子之痛?
《南方周末》2003年8月7日第31版《唐全顺赌球案调查》(作者为《南方周末》驻沪记者刘建平、实习生朱红军),记述了一位曾较有名气的足球运动员,1988年全国甲级足球联赛的最佳射手,因赌球而进班房的故事。看来赌球由来已久,不知何以拖到了近期才被“引爆”。这篇报道令我不能忘的,却是赌球案衍生的次要情节,一个插曲,即犯案球员的老母亲的故事。该文说,那位老母亲久已见不到儿子,在上海杨浦区棚户区的生活极其拮据。据记者所见,这位老人“住在一间旧房内,床板上铺了一张补了又补的凉席。上海正值酷暑,记者坐着尚且汗如雨下,而老人的家中,既没有一台电风扇,也看不见一样电器”。“邻居们主动地跑过来,他们抓起一瓶没有标签的腐乳告诉记者,这就是老人每日三餐的下饭菜。为了省米,老人三餐喝粥,为了节省一点煤气,不等粥煮开,就将锅端下来,靠着余热将米涨开。”“有人传过话来,唐全顺还要为赌球罚款2000元。老人为此夜夜痛哭,不知该到哪里找这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