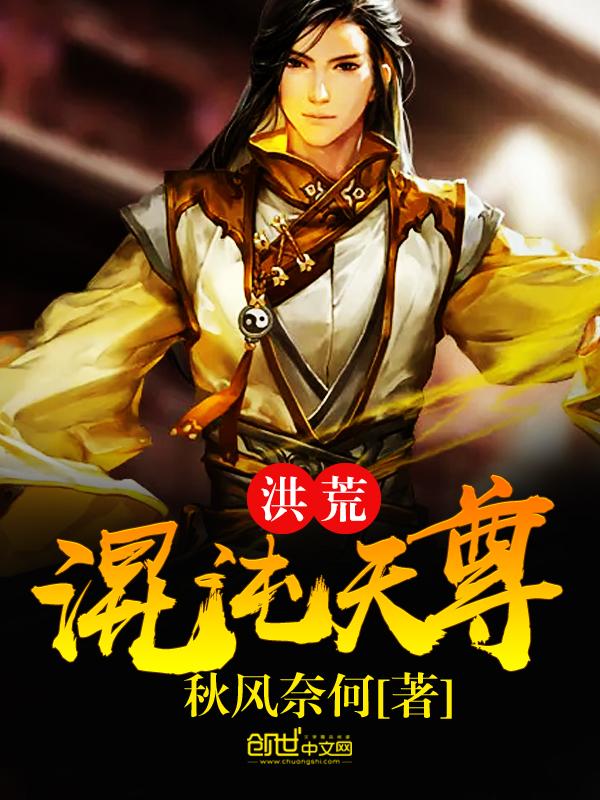奇书网>旧制度与大革命视频 > 托克维尔和旧制度(第1页)
托克维尔和旧制度(第1页)
托克维尔和旧制度
弗朗索瓦·孚雷
【编者按】弗朗索瓦·孚雷(Fra,1927—1997)是法国革命传统史学修正派的领军人物。他倾向于把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意识形态的而非社会经济的演变,因此他十分重视托克维尔关于“旧制度”这个词的意义解析。他认为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它解释了为什么“旧制度”会引起那么强烈的仇恨,以至于法国革命者要用一场“大革命”来与之彻底决裂,而这种史无前例的决裂信念本身,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实际上也是“旧制度”自己锻造出来的。
在这篇文章里我想再次谈谈一本书,这本书曾深深启发过我和许多历史学家,它就是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1]托克维尔试图在此书中理解“旧制度”这个词的意义,而这个词当初是一个民族为否定它的过去而发明出来的。他希望了解这个词所描绘的究竟是怎样一种社会和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是何时和怎样发生的,以及这种制度为什么在续存了好几个世纪之后会如此突然地崩溃,以至于人们总会嘲讽地加以回顾。托克维尔对旧制度的研究直到今天还在引起我们的关注,还在促使我们对他提出的问题做出新的解释。我这篇文章就是为此而写的,首先让我来简要谈谈这部书本身的历史。
在20年的时间里托克维尔写过两部有关法国旧制度的历史作品,第一部写于1836年,那是应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之邀为《伦敦和威斯敏斯特评论》写的一篇长文;第二部便是他在1856年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名为《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两部作品因时代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第一部是在七月王朝初年写就的,当时法国大革命的目标似乎已经实现。第二部写在路易·拿破仑政变(1852年12月2日)之后,目的是想解释这样一个问题:革命为什么会在1848年重现而其结局却又和第一次一样是拿破仑独裁。
这两部作品的内在差异是非常显眼的。在1836年的文章里,托克维尔没有区分1789年革命的远因和近因的年代上的差异,而且他谈大革命的原因结果的方式也和后来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托克维尔在1836年的文章里没有对“革命”这个词本身和法国大革命的现象做任何探究。当时,他只是把大革命看作已经在全欧发生的一场运动的突然加速。法国人只是以一种快捷而彻底的方式终结了贵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状态,而这种社会状态的终结早已是欧洲各民族内在的发展定势了。所以法国人的历史,无论其多么具有革命性,也只是新在“形式上和发展上,[而]非在原则上和内容上。由革命产生的一切,没有革命无疑也会出现;革命只是一种暴烈而快速的程序,它帮助政治状态适应社会状态,帮助事实适应观念,帮助法律适应习俗。”[2]这实际上是在重复基佐1820至1821年间在索邦讲课时所说的这样一句话:“被称作革命的那种动**,与其说是某种刚开始的事情的征象,远不如说是对那种已经发生了的事情的宣告。”[3]
但在1856年,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从1789年法国人提出要完成的事情和他们实际做到的事情之间的比较开始的。他们曾热切地要和他们的过去决裂,但他们实际上已经把旧制度的习俗和观念重新赋予了新世界。这正是为什么解释法国人的革命对于这位历史学家来说是那样的困难:他不仅必须弄懂一个民族何以会产生彻底砸烂旧世界、一切从头开始的观念,而且还必须搞清楚这种观念是怎样马上就在习惯的重压下被埋葬的。托克维尔琢磨出一个办法,那就是在大革命进程内部划分出两个阶段。
托克维尔的出发点,是那种被同时代人看作法国大革命的崭新、非同寻常、无法理解、令人厌恶同时又令人着迷的特征的东西。这种特征并非一开始就很清楚,但它很快就成了包括埃德蒙·伯克和约瑟夫·德·迈斯特在内所有最富有洞察力的观察家们的共同印象,他们都为这种突如其来而且世所仅见的景象而惊讶莫名。然而托克维尔却提出了自己的异议:大革命最终还是恢复了宗教,并借由对社会平等概念的高扬而创造出了那么伟大的力量,以至于它的敌人都要跟着效仿。大革命能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新鲜感,而其结果又是那样不出所料——何来这种强烈的反差?无非是因为在这个打断时间进程的事件背后,隐藏着一种时间上的连续性。这个悖论,在托氏此书第一编的第一、第二章里有一个初步的勾勒,接下来的三章文字便是对它的深度阐述。这说明托氏在描述大革命的各种因素方面是下了许多功夫的。
大革命之新,究竟新在何处?新在革命者希望按照某种宗教革命的方式把它搞成一种“普济主义的”革命,即使它只是一种社会的和政治的事件。托克维尔想到了基督教,想到了基督教以普济主义诉求击败古代各城邦所有地方教派的斗争方式。他把民主的理想和基督教理想做了对比,目的不是要将前者归结为后者,而是要确认大革命被注满了宗教性的魔力。18世纪末的法国人立志再造人性,其实就是想在此岸实现基督教徒想在彼岸实现的梦想。他们诱出的希望和煽起的**,都和宗教世界的希望和**非常相似,即使向这种希望和**开放的只有一个政治空间。这样他们就发明了“一种新宗教”,即革命政治宗教。循着米什莱[他的《法国革命史》(1847—1853)托氏一定读过,尽管从未引用过]的叙述,托克维尔发现1789年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旨在煽动民众参与政治的宣传活动。言其“新型”,不是说这种活动在早期的宗教运动中没有先例,只是说这种活动的成效长期低迷,“直到中世纪中期”都从未能成功,实际上一直滞留于圣经也就是宗教里。说的也是,早期宗教运动的人气,岂能与法国大革命在18世纪末的人气相比。所以,1789年革命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解释为什么一般公众那么容易接受它的普济主义信条。
像米什莱一样,托克维尔也注意到了这种信仰非同寻常的新颖性,以及它是怎样产生强大的影响。但和这位共和派历史学家不同,托氏还看到了这种信仰的怪异性。他感到这是一种看上去像宗教实质上却是政治的东西。它表达的是一种对人性的信念然而却又只体现在一个民族的范围之内。它在未来会是一种普遍的信仰然而却又和一个国家的历史连在一起。这种矛盾使革命者们确信必须彻底否定过去,必须密切监视那条区分过去和他们所期望的目标的界限,必须证实他们创始新社会的权利。如此说来,革命既身陷历史的囹圄又是必欲推翻历史的运动。托克维尔这样写道:“在1789年,法国人做出了任何其他民族都未做过的巨大努力,要把他们的命运切作两段,要在他们的过去和他们所期望的未来之间划一条鸿沟。”[4]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他们会把他们的过去看作一种与他们的未来对立的世界,并不遗余力地要“对自己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彻底告别他们的历史——这历史现在被他们称作“旧制度”,它代表着革命决裂的另一边。
现在托氏要探究的,正是这个另一边或“旧制度”,因为他感到其中包含有许多有关革命信念的奇奇怪怪的东西。在这种探究中,托氏又拾起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支配他去美国旅行的诸多思想中的这样一个思想:美国的民主因其没有一个“旧制度”要战胜或要推翻而没有革命性,而法国的民主则只有在推翻了贵族的社会统治之后才能建立起来。实际上美国人没有必要成为民主派,因为他们一经定居到那片将成为他们的共和国的土地上,他们就已经是民主派了。他们用跨过大西洋的方式和过去实行了决裂。所以,所谓18世纪末的美国革命只是对他们的立国状态的一种重新确认,切断和英王朝的关系只是对他们的自由经验和平等主义社会条件的一种具象化。美国的建立的确标志着一个新民族的诞生,而这个新民族是由一群自由联合的公民自主创建的。但美国公民们没有必要否定他们的过去,没有必要驱除他们的历史,没有必要来一场革命决裂。
而同一时代的法国人则确信他们必须反美国人之道而行:为了在自然权利的原则上建立他们的民族,他们必须弃绝他们的传统、忘记他们的记忆。在托氏看来,正是这种对过去的精神和政治条件的弃绝,造成了法国的革命化,使法国出现了一场和过去的激进决裂,出现了一个民族集体地嫌恶他们自己的历史的景象。就是在这里,托氏看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抽象的”和哲学的本质。大革命不只是要依靠一些哲学原则来解决一场政治危机,它还启动了一种可怕的否定性努力——旨在抛弃他们的过去的一种绝望的,而且是在劫难逃的努力。这种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或者说,对旧制度的仇恨是怎样由旧制度本身生成的?
这个问题又将托克维尔带回到法国式民主和美国式民主之间的差异上,他的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说盎格鲁—美利坚的社会状态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话(因为它既是晚近的,又是直接建立在社会平等的原则之上的),法国的情况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法国的社会状态历史悠久,又是由君主制形塑而成,而且法国人在革命时期还曾努力去根除过它,同时对自己进行洗心革面的改造。换言之,托氏力图把革命思想的力量和脆弱性这两个方面都弄清楚。革命思想虽有一种堪比基督教的普济主义魅力,但也有其脆弱的一面。和宗教不同,革命的唯一裁判者是历史,即使它是从推翻这个民族的过去开始的。无论革命像宗教信仰一样对人们的头脑施加过多大的影响,它的行动总是发生在尘世的,是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的。托氏此书第一编的最后两章主要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托克维尔认为,所有历史时代的终结,主要都是因为信誉的缺失,而不是因为自身的老朽。只要看看近代欧洲人们对“封建的”和“哥特式的”习俗残余的嘲讽态度,就不难理解这些残余在消失之前曾怎样声名狼藉。当社会顶层出现求新的狂热,而这种狂热又渐渐弥漫到社会各阶层的时候,当人们对于习俗的记忆在衰退的时候,对这些习俗的提及就会引起越来越多的轻蔑。正是在这里出现了该书的一个主要思想:封建主义的残余越是重要,对这种残余激起的仇恨就会越是强烈。
和从封建结构里成功地生长出了现代性的英国不同,18世纪欧洲的其他地方不同程度地呈现着一种共同的格局。那里中世纪的习俗到处都在消亡,到处都在丧失信誉,偶然还会被人们置若罔闻,而这种态度都已经扩散到了民间。法国大革命着手加以根除的,正是这种正在消亡而且在当时许多人的心目中已经死亡的习俗。但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因为这些习俗渗透在社会和政府的方方面面,对于它们的根除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场革命。即使出现了一种新近统一起来的平等主义的社会秩序,这种激进的根除运动也只是废除了一个正在自我消失的世界。如此说来,大革命乃是那种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平等借以在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其绝对统治权的运动的法国版。大革命的发生并非偶然,或者说并非不可预料,它其实是一个持续了两个世纪的历史进程的终结。如果大革命没能发生,旧制度也会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一点一点地消亡,而不是在1789年毕其功于一役地被彻底摧毁。托克维尔相信这个论点足以驳斥伯克有关大革命是对“欧洲古老的普通法”的一种令人痛惜的破坏的谴责,因为伯克没有看到旧秩序哪儿都在消亡,包括在英国。
所以托氏此书的最后一编所讨论的问题,并非大革命为什么只是完成了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而是大革命究竟是怎样完成这个过程的。大革命的命运与民主神秘莫测的兴起息息相关,而按照托克维尔的看法,关于这种民主的兴起,我们不可能探知它的原因,只能知道它的结果。法国民主兴起的新颖性甚至独特性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案例。那种激进的、伴随着一种终极判决的清洗,以及那种决裂旧世界的毫不妥协的**,只能在发生于这些情况之前的历史过程中才能找到解释。历史断裂的观念,作为一种集体的想象,只能是一种更早的退化过程的产物。但是革命者对旧制度的强烈憎恶,把这个退化过程弄得模糊不清了。他们因为想摧毁它,于是就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大革命是在它之前发生的历史过程的产物。
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个可怕的、50年后还在制约着法国人的思维方式的法国事件,必须透过一个披露了它的绝对独特性的双重谜语来理解。这种从头开始再造人类社会的想法在欧洲一个最古老的民族中究竟是怎样和出于什么缘故产生的?这种明显不靠谱的观念何以会被人们当成真理并受到那样热切的追捧或那样强烈的憎恶?法国人给其历史增添了一种宗教的特点:这种打断时间链条的想法他们是在哪里提出来的?他们为什么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普济主义的民族?这组问题又将我们带回到了那个神秘的、在自我否定中展现的历史观念上。
大革命对过去的否定这个当时的人们就感觉强烈并且在谈论的事实,掩盖了事情的另一个侧面,而大革命就是通过这个侧面来完成这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进行的工作的。这种“完成工作”的观点,对于基佐的大革命解释,对于米什莱关于大革命是正义对于专制统治和基督教教条的最后胜利的思想,都具有核心的意义。对于托氏的解释来说也同样如此[5]。托氏告诉我们,要是我们撇开大革命的精神不谈只看它的实际结果,我们就会看到它并不是它自命的那种东西:它的“创新性比人们一般所说的要少得多”。[6]它只是粗暴地结果了一个快要消失的东西。即使它令当时的人们感到惊讶,它也至多只是一场早就开始了的并导致了旧社会大厦全面崩溃的演变过程的最后一场戏。这种演变过程欧洲几乎到处可见,但唯有法国是以老民族签署新民约这种非同寻常的场面来结束它的。由此可知,大革命的全部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分析旧社会历史的特点和旧社会在法国消失方式的特点来解决的,大革命的原因就隐藏在两者之间的关系中。这样我们就回到了托克维尔那个最早的、把他带到美国的思想:如果民主的进程不是人类可以设想的,至少它的发生方式和后果是可以研究、可以理解甚至是可以操控的——最后一点,《论美国的民主》的这位作者或许已承认在法国是不可能做到的了,但这也更坚定了他要对这个问题加以解释的决心。
为了弄清楚托克维尔是怎样解释社会平等在法国的出现这个问题的,我们先来看看他的旧制度分析的一个根本性的方面,即那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市民社会”的东西和实行行政集权的王朝的关系。《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第二编前几章描述了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随后诸章(八至十二章)则探讨了这种中央集权对社会造成的后果,那是从这两个主要结果谈起的:其一是一种让人们彼此相似的倾向,其二是令人们相互分离的种种情绪的强化。一方面法国人变得越来越相似,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日益分裂成一个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小团体,即一个个以排他的感情死死守住它们之间的边界的微型社团,而由于这种社团的新生性或脆弱性,这种排他的感情还变得越来越强烈。1789年革命,在著名的8月4日之夜将这些微型团体彻底粉碎,从而暴露出它们所隐藏的东西:一个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更具有同质性的社会形态。
这种同质性或相似性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之间,而且表现在省与省之间。王朝通过适用于整个王国的国王立法,逐渐消除了各省之间的差异,实现了法国的国家统一。到18世纪末,那种由国王敕令和改革派思想所培育起来的统一精神,已经为法国社会所普遍接受。
同质性的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日益相似。深知农民已自我构成一个庞大的阶级,托克维尔这里谈的不是全体法国人民,而只是上流社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这里考虑的是贵族和富裕资产阶级——这种资产阶级虽因没有“贵族身份”而仍被隔离在贵族圈子之外,但他们终究正在变得跟贵族越来越相似。
何以贵族会越来越穷而资产阶级会越来越富,托克维尔认为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一个演化进程的结果。这种演化是以最大的一部分地产转入资产阶级和农民之手告终的。由于缺乏维持和强化其特权的手段,贵族失去了(或售出了)他们土地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以至于他们都没有了统治的习惯和精神”。[7]托克维尔指的可能是,贵族被王权剥夺了政治特权之后就和土地——他们的力量和财富的基础——自我疏远了。贵族最富裕的部分由于对农民不再有用,加上为国王的权力所吸引,他们就进了城,过起了跟资产阶级一样的生活。最贫穷的贵族则卖掉了土地,尤其是那些不再带有对当地居民的统治权的土地,仅靠一些残存的领主权利和地租生活。这样贵族就既失去了财富又失去了权力,或者说既失去了权力又失去了财富,而从中获利的则是比典型贵族富有许多倍的资产阶级。
所以,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曾有过一个长期的平等化运动。那是一种经济上的平等化,而隐于其后的是另一种更具有本质性的平等化。由于贵族被剥夺了拥有领地的排他性权利,在国王政府眼里他们就和资产阶级不再有别了。贵族和资产阶级都已臣服于国王政府。权力被从社会里剥离出来之后,便外在于社会了,落到了国王和政府的手里。让贵族与权力和土地分离的结果,便是一个不同于以威胁性姿态凌驾于其上的政治领域的市民社会的创生。而且,这种分离还引起了条件的平等,因为它根除了那种把政治权力和世袭社会身份联系在一起的贵族原则。结果,人人在国王面前都成了臣民。日益发展的财富平等化其实只是政治从属化的结果而已。
英国历史的情况则完全相反。托克维尔继续将英国历史同法国历史进行比照,即使这种比照会导致他修正他20年前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的观点。他的这部伟大的处女作主要是在法国和美国之间、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之间作比较。法国和美国是两个民主国家,尽管情况非常不同但都属于同一个平等社会家族。而英国则仍是一个贵族国家。然而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美国的例证几乎消失了,从斯塔尔夫人和基佐那里借鉴来的英法历史比较成为关注的中心,因为英国的特点是保持着君主制下的贵族制,而法国的贵族制原则却在君主制下遭到了破坏并消失了。
托克维尔在下一章里分析了这一情况的原因。严格说来,英国贵族已经不是贵族了,就是说英国贵族不再是那种由法律樊篱保护着它的入口的种姓了,而主要只是一个被历史学家们称作乡绅的社会群体,是一个富裕的、拥有地方权力的土地所有者阶级。这个阶级是一种原初贵族命运的体现,这种贵族命运让新家族在老家族的遗存周围聚集起来,以同时享有其土地收入和与之相联系并受习惯法保护的政治权利。在英国,时代变迁联系着现在和过去;在法国,时代变迁则起着一种分离性的作用:它把王朝跟托举过自己、自己也长期植根于其中的社会分离开,还把贵族跟土地和封建政治特权分离开。于是就发生了一种双重的社会同质化过程,社会在其间一方面构成一个直面“抽象”国家的整体,另一方面又由被国家剥夺了政治自由的个人所组成,而这些个人在财富上尤其在土地财富上还是比较平等的。